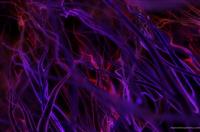2005年,一闪而过,像一场无趣的电影,情节一点一点地发展,却忘记了以怎样的方式填补每一天,忘记了怎样欢笑,怎样哭泣。有时会试图回忆,更多的时候,想忘记那种平淡寡味的感觉。
2005年第一场春雨来得特别早,平时不怎么联系的一个初中同学,很突兀地给我打电话,说,她要结婚了。仍记得雨水潺潺的那天,我坐在她的婚宴上,突然就看见了对面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微黑皮肤,眉清目秀,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显然他也是认识我的。婚宴好似同学聚会,一桌子十一个人,闹哄哄的,大家各说各的,却听不清都说了些什么。
有人突然大声对这他喊:宏,最近在哪儿发财呢?突然就想起了他的名字,林家宏,初中邻班的同学。曾经,动不动就站在我班级的门口对我大喊:小不点儿,借我英语书用用,我忘带了。小不点儿,我没带圆规,把你的借给我。借来借去,彼此越来越熟悉。初中三年,他整整陪伴了我三年,曾经每天同路放学回家,曾经一起走着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曾经一起吃小卖部的海带丝咸菜头…
中考时,他说:小不点儿,我们一起考市一中,可好?我点头。
太小的年龄,我们只是父母手中的一枚棋子,前面的路岂是我们说了算的?于是,各奔东西。
从此失去联系,隔了十年,再次相逢,欲语还休。
中间,好友燕子打来电话,她已在我家等我回来。我挂掉电话,起身离开热闹的人群,只一瞬间,我忽然想起对面坐的他,我还没有同他说一句话,可,已同新娘告别,又怎好意思再返回去?算了吧,十年的光阴。彼此怀念过去的纯真,却只能相忘于江湖。
烈日炎炎的夏,有同事把她表姐的弟弟认识给我,不好回绝,于是,素面朝天接受任务。如此盛大的相亲场面,同事坐在我旁边,其次是她表姐,姐夫,姐姐的三岁的孩子,表姐的弟弟,表姐的母亲。TMD,你们这么多人合伙一起对付我一弱不禁风的小女子,我才不干。中间,联通发来不足五元的催费短信,我不好意思地欠起身说:真抱歉啊,我妈找我有事,我必须得回家看看。咱们改天再聊吧。
习惯了上网,看到有他在线,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海阔天空的聊,没有中心,没有任何目的。我说生活过的太平淡了,真想捡到一大笔钱,去周游世界,花光所有的钱再回来过穷光蛋的日子我就知足了。他说:你的理想是纯粹的,可惜出发点不对头,哪个神经病把钱丢到大马路上让你捡啊?不如去买彩票,中个500万什么的,也算光彩。
于是,充满希望地去买双色球。趿拉着拖鞋,混迹于无数充满金钱幻想的老爷们儿中间,研究每一期中奖号码走势。那段时间对数字及其敏感,但,除了我的发财梦想日益膨胀外,我一无所获。
金秋十月,连工作都变得乏味。头儿在会上说:市教育局要派三名青年教师去阿拉善盟支教一年。我回到家,从床底下翻看初中的地理书上画的中国地图,发现他们说的那个寸草不生的地方长满了大片大片的沙漠,顿时我的眼前一片灿烂光辉,三毛故事里浪漫的撒哈拉也不过如此吧。看多了志愿者义务支教的故事,经常会被感动,也只有在那种清贫且纯粹的环境里,我们才可以体会到教书是作为一种事业而存在的。
次日,信誓旦旦地去校长办公室报名,校长请示局里的有关人员,对方竟说,名额已满。做了一晚崇高的撒哈拉之梦就这么轻易破灭了。
事后,同事说,你还是太小,什么都不懂,这种事能留给你吗?有多少人走后门抢这个美差呢,不到一年,回来后就涨工资啊,提干什么的,支教只不过是中间要走的一个过程罢了。
连这么崇高的事情也能沾染上腐败的气息?这世上还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
周日的时候,找个心腹,去肯德基要杯温热的澄汁,看着透明的玻璃窗外,黄花满地堆积,
整个秋季,我们一起落寞的数着零零散散的黄叶走过。
冬天,所有的人都变得缩手缩脚,学校开始放假。
一个人窝在家里冬眠。看片子,看小说。
凯歌导演的《无极》票房一涨再涨,美丽至极的画面,尤其是满神在江面上飘来飘去的那一瞬间,一直以为是动漫做出的逼真效果,事后才知道是陈导他老婆以真乱假,陈红的魅力就在于此吧。视觉还算及格,但听觉上就忒糟糕了,港日韩三地明星操着不纯正的普通话一本正经地背台词,也就刘烨说话能听懂吧,但,他统共也没说两句,真个无聊之极的片子。
《断臂山》里两个搞同性恋的西部牛仔在一起深情相拥的场面怎么看都让人恶心,是不是所有获大奖的片子都有一种变态的美?
外面开始下雪,我把手机放在耳朵旁边,开始混混噩噩地睡觉。手机是我和外界联系的唯一工具,可,我还是希望,就这样安静地一直睡者,希望睁开眼,就可以看到春暖花开。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睡眠,过了秋分又冬日,收拾书箱好过年。
终于等到过年,我的2005及其烦躁的从我身边走过,我却忘记了,那是一个怎样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