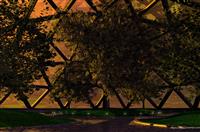妈妈是家里的洁净急先锋,无论是看得见的门窗桌椅,还是看不见的犄角旮旯,都在她的管辖范围。仿佛武林高手飞天遁地,清理那些在我和爸爸看来根本没有必要打扫的地方。
“这个地方别扫了,不安全。”看着她爬高上低,实在不放心。
“看看,还是儿子心疼我。”妈妈回头望着爸爸。然后得意的说:“那你来,你个子高,方便。”
“我……”接过抹布,从围观者变成参与者,爸爸一旁窃喜。
在妈妈眼里,我和爸爸是家里仅次于细菌的脏、乱、差环境制造者,经常被她数落。其实,我和爸爸并不脏,只是在卫生观方面,有细微的差别。
“大面儿过得去就行,弄那么干净,跟酒店一样,一点不亲切。”这种观点如果放在现在,应该称为佛系。
从小到大,家里的任何东西都是一尘不染。灶台、地板、桌子、柜子……只要能擦的,无论人家愿不愿意,都用抹布摩擦摩擦。怕她累,只好帮着干。谁知,这么暖心的行为,竟为我俩招来了新的槽点。
事情是这样的。
拖地,是家里最常见的清洁项目。相对于那些难清理的边边角角,拖地有大片空地可供发挥,难度系数较低。正因为此,这成了我和爸爸的必争之地,赢的无需爬高上低,输的需要龇牙咧嘴。
“先扫再拖,干净。”在打扫卫生方面,妈妈是有天赋的。除了能出色完成自己的工作,还能有效的监督。“噢,我扫。”在妈妈炙热的注视下,我终于完成了拖地的第一步,包括地板砖与地板砖中间的缝隙都没有放过。
“多冲冲水,拖的干净。”为了不浪费宝贵的水资源,我据理力争。妈妈想了想,认为有道理,转身出去了。正当我准备开始时,她将一只空桶放在我面前,示意水不要浪费,可以冲厕所。“噢,我冲。”
“拖把弄的干点,别滴水。”妈妈再次就拖地发出了第三次指令,我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我连拖地都不会?”正准备上前理论,突然看到歪着身子,龇牙咧嘴的爸爸,很显然,窗子的设计不符合人体工程学。
“要什么自行车,赶紧的吧。”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场景。
拖地是迅速的,一方面身强力壮,一方面建筑面积有限。看来,贫穷也没什么不好,除了限制想象力,也能带来不小的好处。
“拖把涮了吗?”
“涮了。”
“好,等干了再拖一遍。”
“我……”
活儿是自己选的,活儿是自己选的。默念一百遍,挤干多余的水分。爸爸端着瓜子,等待妈妈的验收,微笑的眼睛仿佛在说:“臭小子,知道为啥不选拖地了吧。”
第二遍很快,因为干净的地板摩擦系数很低,毫不费力。打开电视机,屏幕反射在窗明几净的玻璃上,一同在玻璃上的,还有爸爸扭曲的身影。“不合格,你看看这里有水印儿,还有那儿……”
我和爸爸面面相觑,盘算着下回干点省劲儿的活儿。当然,这只是千百次大扫除的缩影,我和爸爸也尝遍了所有工种,无一例外的不省心,全返工。
“你俩就是给日本人干活儿的,出工不出力。”我和爸爸无法反驳,毕竟人家活儿干的确实漂亮,想找茬都觉得无理取闹。
自此以后,每逢遇上大扫除,我和爸爸都绞尽脑汁,脚底抹油。躲过的暗自窃喜,失败的垂头丧气,程度堪比抓壮丁。“是不是比没打扫之前好,你们自己说。”
过了一年又一年,擦了一遍又一遍。这只是平时一个小小的缩影,如果遇上过年,强度和要求会呈几何倍数的递增。“确实不错,干净多好。”人的适应能力很强,我和爸爸竟习惯了这样的压迫。
我们爱妈妈,爱我们的家。
时间如流水,不知不觉间妈妈渐生白发。突然一夜之间,她变得不爱干净了。那些有很高难度系数的地方,都置之不理,变得佛系。之前纤尘不染的地方,竟变得有些尘埃。
我站起身,检查了很多以前的卫生死角,或多或少都藏着尘埃。蹲下身,阳光下尘埃四散逃离,闪闪发光,幻化折叠。
“妈,这边有点……”我没能把脏字说出口,拿起拖把擦干净。“妈妈。你也有今天,你也不爱干净了。”我笑了,强忍泪水。
时间你慢点走,或者,就此停住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