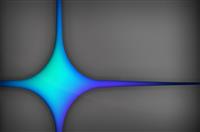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
自我懂事之日起,我就亲眼目睹了父亲用他那特有的肩膀杠起一家九口人艰辛的生活。
有几组父亲清晰的影像根深蒂固的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在小麦收割的季节,烈日炎炎的气候,在金黄色的小麦土地里,父亲戴着一顶变色的草帽,一件破旧的蓝色的中山服,在地里割麦子;汗,侵湿了衣服,衣服上的盐斑,形成不规则的图案;那汗,在脸上,豆大的珠,闪亮闪亮的;手臂一挥,长袖抹汗……
——收割后的水田,反射出耀眼的阳光,远远地就看见父亲的身影,一只手高高地扬起细竹条,吆喝着那诚实的老水牛耕田,噗噗的水声伴着那悠扬的口哨声。
——在农闲的季节,父亲斜趟在竹椅上,旁边的小木凳上一杯浓浓的茶,嘴里吧嗒吧嗒的抽着山烟,双眉紧锁,眼睛半闭着仰望着天空……
父亲个子不高,是属于中等身材,但是,父亲的力气很大,利用业于时间练就了一手石匠的好手艺。在大家休息的时候,父亲就挑起非常沉重的工具,做一些墙基石、牲口用槽等物件换钱;无论是炎热的夏天或是寒冬腊月,远远地就能够听见,从那山沟里传出的叮…叮…叮富有缓慢节奏的铁锤和铁钻的碰击声。
这声音,这节奏,也是希望的旋律;
这声音,在那艰苦的岁月,是挣扎的呐喊;
时隔30年了,只要听见这样的声音,我都会驻足聆听,是那样的熟悉那样的亲切。
父亲不识字,体会到了认不得字的苦恼,对我们读书的事情平时从不过问。小学五年级上期报名,我一期的学费是两块四毛钱,家里只有一块六,钱不够,我生死不去报名,钱不够,怕老师不收;第二天早上起来,父亲说:“走,我跟你去报名。”我跟在父亲后面,四公里的路,父亲一句话没说,到了学校,父亲找到班主任老师,说差的钱一个月后兔子卖了跟你补起来。
小学读五年,最后一期有一次去上学,由于头天晚上下了大雨,水大把田坎冲垮了,水流也大,过不去,从其它地方绕道,要多走二十分钟,我试踩水过去,刚踏出去两步,就陷下去,把裤子打湿了,我吓哭了,回了家,没去上学。
父亲中午知道了,瞪起眼睛看到我:“多转两步要死人啊!”正好他旁边有竹片,抄起就打在我的屁股上。
第二天放学回家,多远就看见冲垮的地方有个人影,仔细一看,是父亲,搬了许多石头,在砌那垮塌的缺口,石头大,搬不动,左移右移左移右移的移动,很是费力……
我远远的站在哪里看着……
父亲有一手石匠的好手艺,是自学成才的,父亲利用空余时间就用工具在山崖上搬弄石头。人民公社的时代,农村种庄稼,就和现在工厂上班一样,集体八小时劳动。父亲只有靠休息时间来做这些事情。中午十二点,大家劳动一个上午,都筋疲力尽的,回家做饭或休息;父亲回到家里,坐下卷一支山烟抽了,喝一碗凉水,挑起工具出去干活了。
在那个年代,在农村有一门手艺,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农村修房造屋、圈坝晒粮、磊锅砌灶等都少不了要用石头,父亲就靠着这门子技术,在那艰苦的年代让我们没饿肚子,每顿汤汤水水总有得喝。
父亲有一位远房的堂弟,在部队是个小干部,在回家休假的时候,戴了个手表,那个年代,手表就是奢侈品;父亲非常喜欢,最后父亲硬是用六十元把这块手表买了。六十元,在那个年代就是足够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这件事情在附近传了很久,说的是有一位在水田里犁田的,手杆上戴了块明晃晃的手表。
恢复高考,我昏戳戳的去参加了考试,没想到被中专录取了,临走,父亲把手表取跟我,就说了一句话“上课不要迟到了,好好读书。”
我没敢戴,一直把它放在胸口这个兜里,因为哪个时候我要是戴个手表去读书,相当于现在开个豪车去上学。需要时看看,看着这表就好像看到父亲在跟我说那句话;这块上海牌的机械表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时而看看。
父亲的劳累,病是勉不了的,可是他病了不告诉家人,当已经不能够隐瞒的时候,去医院检查,已经是晚期。医生告诉我们,没什么办法,最多三个月的日子。父亲在医院的长凳上坐着,我跟父亲说我上厕所,在厕所里,我让我尽情倾泻,眼睛不红了我才出来,父亲问我,你上厕所弄久哦,火重,吃点药嘛。旁边的人赶紧插开话题。
在最后的日子里,父亲痛得昏迷,也没听到他呻吟过;当他醒过来看到我们,还在问我:“天天守到我,要耽搁你上班不?”听到这话,我鼻子一酸,跑到山上,“爹:让我下辈子还做你的儿子吧!”
父亲离开了,永远地离开了。
这块手表,上起条,针还在走动,这滴答滴答的话语声:
“要晓得怎样做人,才晓得怎样做事。”
“对人要有礼貌,无论什么人。”
“钱要是找得完,前辈人就找完了。”
……
朴实的话语,言简意明,足以让人回味一生。
经常,我总是呆呆的、久久的凝视这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