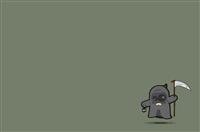“哎,王嫂,听说阿树家带了个贵州女人,看看去……”似乎,久违喜庆的村子终于要迎来一点新的气息。阿树是我隔壁邻居,他带来的女人来自贵州,是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听说她已是好几个孩子的妈了。那女人长得很壮,皮肤黝黑,名字也怪得很,叫什么“娜尔杰”来着,谁知是真是假?她老低着头,一言不发。有人议论她是不是哑巴。尽管如此,在村子里能带回个女人已算是壮举了,剩余的光棍们更是把阿树当做神来崇拜。憨厚的阿树,只害羞的抓抓脑袋,笑而不语。
农村人的习惯是哪儿有新鲜事就去哪儿唠嗑。自那贵州女人来了以后,隔壁阿树家常常被围地水泄不通。而隔壁的我常听一屋子的人在议论“阿财.阿柄啊,你们也该去带个女人了,年龄不小了。”“阿树啊,你得看紧咯,把她手机没收了,免得她随人贩子逃了去……”村里的长者都这样叮嘱。那个贵州女人照旧一言不语,呆坐着。
而隔壁阿树家,待那女人如宝。原本寒碜的一家人,一个月也难得吃肉,如今,却天天有肉,但他们自己是从不吃的;不久,家里还换了一台新电视,配上了影碟机,说是给她解闷来着。
“贵州女人热潮”渐渐退却,村子又恢复到往日。长辈们也只是私底下偶尔议论那女人靠得住否,阿树一家的盛情款待值得吗?
有一天,我和奶奶去我们家和阿树家公用的晒谷场,竟看见贵州女人坐在晒谷场的大石头上,眼睛望向远方,双手抚摸着肚子,眼神里分明充满了前所未有的微笑。她已然忘我,根本未察觉到我们的存在。虽是隔壁,我却有幸第一次听到她讲话,虽听不懂,却明显感受到她喜悦的呼唤。突然,“她怀上了”奶奶神秘地说。我愣了一下,但凭奶奶的经验绝对没错。再看她欣喜的样子,可知她终于在这儿找到了她足以欢喜与留恋的依靠。
以后的每天,她都会去晒谷场,时而靠着大石头,时而坐着,摸着日益凸显的肚子,望着远方,痴痴的笑,时而还嘀咕几句。这时候,所有人都绝得这个女人算是定下心来了。隔壁阿树一家也放松了警惕,不再时时跟踪。
几个月后,那女人诞下一子。村里,人人欢喜。隔壁人家,从此增添了几份生机,简陋的泥房时不时传来婴儿的哭声,掺夹着一家人的欢笑声。真庆幸,似乎贵州女人终于融入了这个家。从那以后,她还是每天抱着儿子去大石头那儿。看见路人,她也欢喜的用生硬的话打声招呼,还学奶奶晒谷子呢! 似乎,所有人,包括谨慎的老者们都觉得阿树一家终于要幸福了。“这下子放心了,孩子都有了,不会跑了……”
一切依旧,“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再加上我隔壁一家的温馨乐章。
可是,有一天,那块大石头旁,只有一个3岁的小男孩。他努力地想爬上大石头,却几次滑落,嘴里哭喊着“妈妈……呜呜……”伤心的泪水,铺满男孩稚嫩的脸。
不曾想,如此疼爱她的公公婆婆和深爱她的男人甚至是自己的亲骨肉,最终都没能留下她的心。或许,她在远方早已有一个温馨的家,钱骗到手,本该走了,只是她出于仁慈与感恩,留下一男孩作为回报。
殊不知,以后的多少个夜晚,总有一个小男孩在大石头上远望,呼唤他的至亲。她只留下了一个悲剧。
如今,那个贵州女人过得好吗?她会不会在她的家乡的某块大石头边遥望远方的那个村庄,那户人家?又或者,她早已在另一个角落开始了另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