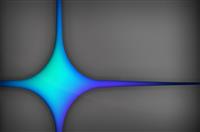有些人天天见面,常常檫肩而过,却怎么也走不到记忆里。有些人只是数面之缘,却时常想起。
每每 抬头看着挂在墙上的那缕金黄色哈达,就想起了青海隆化的一位活佛,他还是当地的一位医生。他的家离十世班禅的故居不到十里,他本人在当地是很有名望。
我与他只有三面之缘,说的话也多不过三句。只是一切还都清晰地停留在记忆里。还记得,第一次见他是因他从天水去兰州,在国道口的车里见到的。他坐在车的副驾驶座上,戴着墨镜、身着红色的羽绒服,要不是光着头,是很难把他和出家人联系在一起,只是给人的是感觉有一种气场在。第二次见面,是在我家里,他匆匆的来,给我们刚满月的孩子取了个藏族的名字:扎西才让,然后匆匆的离去。第三次是今年的暑假,因缘际会我们到青海他的家里拜访他,才和他相处了两天。
他整天忙出忙进的,听说是班禅活佛给了他一个金佛,他想修个大殿,把金佛供起来。大殿修好了,要装藏据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所有的事他都是亲力亲为的,所以,那两天里我见到的总是他忙忙碌碌的身影。还记得刚到他家的那晚,我做了揪面片,他吃了两碗。还开着玩笑说城市里人吃的是垃圾面,地沟油,哪有那家乡的小麦和青稞好吃。接着还说,你们通渭啥都好,就是水不好。顺着他的思维,我当时心里就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穷山恶水出刁民,大概也是有的吧![这是当时我的想法]。那晚,因为是佛门圣地,感觉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就睡在了车了。看着高原上分外圆分外亮的月亮,听着门前小溪潺潺的流水声,原本以为会失眠的我早早的进入了梦乡。朦胧的午夜时分,依稀听见他被车接走,天快亮才回来,据说是另外一位活佛接他去念经了。第二天早上早早的又见他忙碌的身影。中午,我们要离开时,听说他要去西宁,所以我们就送他到了西宁。那知到的是青海的藏医院,才知道他病了,是肝癌。三年前在北京做了微创手术,最近又不舒服了。我从师父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是不想让我们走的。那会我看到的不是大家所说的出家人的那种看破放下,而是孤独。
那晚我们本来不打算回兰州的,可是有人说第二天我们的车限号,进不了兰州市区,就只好乘着夜色匆匆的离开了。临走他手掌合十,念叨着为我们祈福,眼睛里有很多留恋。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里有种莫名感觉。车上,同去的那位叔叔说;“师父,在吃饭的时候哭了。”后面的我再没有听到,因为我在想那是一颗怎样的心,心里载着多少善念,多少对别人的祝福,多少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的悲凉,多少无处诉说的孤苦。哎,等到四十天以后的国庆,再次去兰州,听到的是他仙逝的噩耗。 一时间很难接受。
后来才明白,他为什么老是忙忙碌碌的,才明白我们离开时他眼里的不舍。或许他早就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了。才懂得,那会的他不仅是慈祥的活佛,更是一个孤独的病人。他不像我们可以向别人诉说心思,一切都装在心里,每天默默的忙碌的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是想在离开之前,把他能干的事干完,可惜上天给他的时间太少了,年仅四十七岁,就带他离开了。
或许,我们眼中的出家人应该是看破红放下的。后来懂得出家人首先是人,然后是出家人。是人就有喜怒哀乐,只不过是我们表现的明显,而他们淡然罢了。
人永远不知道,谁哪次不经意的跟你说了再见之后,就真的不会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