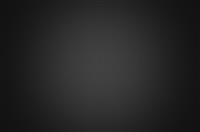六点多些,一群学生就开始敲门。不,是先有人打开房门,开亮灯,一惊诧长凳上睡着的人,被我挥手出去了,尔后,在门外叽喳聒噪,我拖着鞋子,探头到门外,说开什么会,去其它地方开吧!但他们没有走,一群麻雀一样跳在枝头继续说话。
我稀里糊涂,再睡又睡不着,醒又特别难受,索性起来,在外面刷牙,然后提了水瓶,砰地一声关门。却没有关住他们,有同事给了他们钥匙,我提热水回来,屋里竟坐满了他们。大清早也不让我消停?我沉默不语,气哼哼的撵走两个坐在我桌傍的两个学生,鼓着肚子,像蜘蛛一样,坐在自己四面透风的帐篷里。
他们见我张牙舞爪的架势,被一个知趣的我曾教过的学生提醒,不久就散会了。我说为何不在其他地方开会呢?走廊里不行吗?我忍住了,我要调整自己。于是,想到昨晚夜空中那枚将圆的亮月,其辉洒遍校园,如水澄明,又似一层层奇异的不得呼吸而清新着空气的纱幔。那园中丛丛黯然的花木,也宁静的观赏;几只人影在清水中散漫游动。
但我还不满意,为什么没有星星呢?我有些愧意自己关于天象的无知,竟不知道星辰移动的轨迹,何时在此季节出现。却又没有料到,早上被搅醒一样,没有料到,月沉西域之后,竟会有满天的星斗。
满天的星斗,何以在子夜以后,近凌晨的晚秋夜空中出现?梦幻一般,童年一样,如若不是半月一次的值夜,如若不是子夜才休息,是不会观望到这久违的天象的。尽管如此,我仍然懊恼于那群孩子对我的打扰,而他们也看我不起,以为这个老师懒怠惰性了吧。
现在的窗外,车灯,月辉,星辰,好似梦中一样……不,是我内里的幻境,是我真挚的澄明的向往,也常能共临共在的理想界域,诗情画意。如今,已深入内心,被一层薄薄的轻幔掩映,在别处的寂静中开放,在另外的时光中友伴,因为已过重阳的此时秋日,出入上午巳时,便温暖起来,金黄的色彩早已开始燃烧,闪烁着刺目的晶莹白光,整个时间都被他照亮,房屋,树林,还有操场上正在举行仪式的,正在展开运动赛事的学生队伍,统统闪烁着秋日的白炽光辉,仿佛是一个清明的世界,从没有如我睡意不醒或不能正常而生长的苦恼。
然而,这点儿苦恼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不远胜过往昔自己疯狂到子夜的放荡,那些被酒精烧迷了头脑的踉跄形骸?而且早晨,不也可以不再顶寒来校,紧张的赶来早读?想想是啊,毕竟是好的多一些的,毕竟没有差到哪儿去,就像秋寒,仅深夜一凉,如此时不久便恢复温情暖意了吗?这一段,近十天来的时光也是温情的,健康的,入睡不再困难,醒来体力充沛,一切正常。
在此正常之中,关于习作及已有作品的统筹谋划,仍在进行之中。孕育着神风雨师、应龙夸父赛事等等的种胎。而且,昱弟提醒自己原有的零碎的共计近四十万字的作品,可以重构为一部怪异面目、魂穿其里的长篇。这是正常生活中,事业得以正常的前行,一边孕育着,一边生产着,是正常秋日下的思考,是昼尽日升、月落西林后的满空闪烁的星斗和著作。
一部作品的诞生,就是这样,在骚乱之间,在此起彼伏的靠近梦幻边沿处的聒噪中诞生。没有那么理想,却又确凿如是;没有那么纯粹的星光曼丽,却也掩饰不住,纯净的深夜里,作品的碎块在顽强的靠拢、集中、融合。世界本来如此,有蜘蛛,也有玉兔,有织女牛郎,也有顽童不按时就寝,呼喊了数次,仍不熄灭的灯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