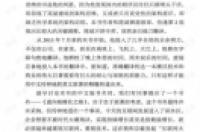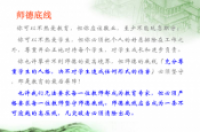
你会为落后于同辈的人生进度而焦虑吗,臭鼬说。
我的同批次香猪,都被宰杀了,香猪说,我还活着,不知算不算落后。
没有同辈了,斑鳖说,我,地球上最后一只斑鳖,150岁以后,没有参照,不知道怎样生活,不知道什么是进度,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即使与同龄不是同辈,只要仍处于这社会规范与人生进度的定义里,燕子说,就仍然要面对他人与周遭。
鸳鸯结婚了,我没有,我落后了,伯劳说,鸳鸯又离婚了,我又不落后了,实际上我没什么都没做,她不知怎么就转圈转到后面去了。
人生不是线性的,燕子说。
进度是个莫比乌斯带,伯劳说,走走走走走啊走,走了也白走噢噢。
你这歌唱的,燕子说,确实能证明你是上好几辈落后下来的。
唉,臭鼬说,我们成长于高速运转,几乎不容纳无为间隔的工具社会,每个人生阶段都被准确地设定好要做什么事情,不能掉队,不能落后,不能有差错,信仰龟兔赛跑,逆水行舟,仿佛一年的时间就会让前一刻还在平稳运行的命运跌入万劫不复。
被规范所压迫,被进度所催逼,被单调的意义追求所杀害,香猪说,即使逃离了屠宰场,我有获得过真正的自由么。
我们是社会性动物,臭鼬说。
只是动物罢了,燕子说,对竞争的忧虑,对落后的恐惧,固然有社会构造的虚妄,但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写进基因里的,社会性只是在恶毒地无限丰富着竞争的形式与落后的定义,我们可以不承认这些本能在我们体内的正当,但难以否认确定的存在,这些恐怕是凭理性难以抵御的万古心绪绑架。
我想要,臭鼬说,要对世俗的豁免券,要对轨道的脱轨权,要被抛掷到远离此刻的随便哪个过去或未来,要换个宇宙与星球、法则与定律、诞生与演化。
别想了,伯劳说,你对另一种生活的想象权,已经被自身的既有存在垄断了,生活就在这里,但你可以不热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