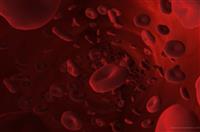《中国史学史》是一本由(日)内藤湖南著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9.00元,页数:4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中国史学史》精选点评:
●再多点带着八卦气息的别扭话就好了
●内藤湖南的这本由1949年授课笔记整理而成的《中国史学史》如今看来更多的是日本汉学学术史的价值,译者马彪也指出五十年代初期在日本进修的鲁惟一后来撰写《剑桥中国史》的过程中也未提及过内藤湖南之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贡献,如今看来本书第二章谈及《周礼》的部分,已经被阎步克的《周礼》战国说推翻。作者言及的《四书》的史学价值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问世,得以更新。《史记》的历史地位在新的史观映衬下,有了更多元的内涵。本书最精彩的史附录中的《章学诚的史学》一文,可以看作是近现代中国人开始有西方史学理论理念的一篇思考,目前也是史学文献学的必读篇目。
●大一之后的二刷,甚至可以作为目录学提要,从这方面来讲如果说汉至唐价值不大的话,宋至清尤其是清代可以说是非常有用了。可以看到在其他目录学书籍中少见的、对清代史学书籍的线索勾勒与内容提要
●渊博,好看。
●上古至元的部分处处透露出内藤史学的通识,不过略偏形式化,四星。清代的部分则更加丰富具体,甘苦之见有似清儒,甚至有纠正清儒之处,而表述的清晰与系统则胜于清儒,六星。
●很重要的一部书。
●內藤湖南為京都學派開山學者,此書為其講稿,在當時乃至今天都是一本紮實嚴謹的著作。作者對史學的範圍既根植與乙部之學,有超脫其外,將四部都視作史學,對類書文獻的頗為重視。
●大家手笔,条理清晰,清代尤详,但清代如谈迁,谷应泰等人没有收入,有点可惜~
●给跪了,湖南写的史学史信息量比瞿林东先生和白寿彝先生加起来还要多。。。
●赶在考试之前看完的,但是不知道考试的时候还记得多少……
《中国史学史》读后感(一):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
一本很好的介绍史学史的大师级著作,但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仍有必要提及.书中有少数地方读起来难称晓畅,原因很简单,标点误用和滥用.一多地方点逗不在关键之处,喜随意断句,而且还多有一逗逗到底的现象.这些虽然不影响正常阅读,但对一部经典著作来说,仍是不该有的瑕疵.或许这反应出译者的基本功不扎实,但责编亦难辞其咎.
《中国史学史》读后感(二):杂感
买这本书是因为当时相对中国史学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无意中遇见了这本书就买了下来。对作者知道是个日本人,其他买书时没想那么多。
现在想起来,知道内藤先生这个人是读《宋代政治史》,该书引用的日本著作较多。不过当时印象深的是宫崎市定,因为以前读黄仁宇的书时看到过。《史学史》这本书我是在今年上半年读完的。目前在读《剑桥隋唐史》,才知道内藤先生在隋唐史上的开创性贡献,也才知道内藤先生是记者出身。
读这本书时,我想起以前曾读过的钱穆《中国史学名著》。读完这本书后,我又把钱书翻了一遍,才发现有一部分没读。以前我羡慕钱先生的学识渊博,现在我知道日本也有这么一位先生。
我也才知道日本汉学在中国史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内藤先生对中国史学演变叙述脉络清晰,对史学发展的时代背景阐述又让人深为叹服。尤其是对中国史精神的把握更是精准。
中国史的精神是通史,用司马迁的话说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当然,通史在专门史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上才更坚实有力。
《中国史学史》读后感(三):一本生硬的“外行”译作
相对于海外汉学译丛的热潮来说,海外中国史学研究的译介仍停留在“零星”阶段,至今没有一个译丛的出炉,比如说日本与韩国的《史通》学、章学已取得了丰硕的成就,可惜没有译丛,就连一本很重要的论文集(Beasley, W. G., and Edwin G.Pulley blank,Historians of China and Japa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也无人问津,难道中国史学史研究重镇北师大或者华东师大没有这样的担当?尽管华东师大近年来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怀着这种不满的情绪与对内藤湖南先生这本由上课笔记整理的中国史学史的期待的张力,就想出了这个标题,后学无意以及无力就译者的翻译水平做出评价,仅就我的一些直观感受提出来,以示疑惑。
阅读开始于附录《章学诚的史学》,“在清朝的乾嘉、嘉庆时期,考据之学发展到了鼎盛阶段。经学领域当然不用说,即便史学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等一批考据学大家,因此,当时史学的发展可说已完全倾倒于考据学风了。”(译文第370页),原文是这样的:“清朝の乾隆嘉慶の時代は考據の學が全盛を極めた時であつて、經學は勿論史學に於ても考據の大家たる錢大 ・王鳴盛などといふ人が出て、史學の風潮を全く考據に傾けたのであつた。”这本是内藤先生在日本大阪怀德堂的演讲,极具口语化的日文风格,本不易转译(听的语言很难翻译成看的语言),至少直译成汉语显然是不符汉语书写风格的,结果就出现了上述似是而非的翻译,对于特别注重作者行文风格的我来说,即便是左思右想,还是一头雾水,这种怪异的翻译会时时碰到,不免使我兴致大减,愤愤然,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中国学者都哪里去了?
带着这种疑问继续检验自己的“学识”,紧接着读了译者的“译后感”:欧洲“历史主义”与中国史学,不免让我“哭笑不得”,译者竟然是这样认识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强调真实事物的‘个别性’、‘一次性’的特征。”对历史哲学有诸多关怀的我,还第一次听说用“一次性”来形容“历史主义”的,也就剧增了“外行”之感,这里的引号不是针对整个“译后感”,而就译者没有历史哲学的源流之感而发。
生硬之感还在继续...“作为日本人,中国史既是一种外国史,又不是单纯的外国史。两千年来,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历史发展的产物。”(译文第3页),不知这样的“笔误”(熏染了日本文化的中国文化)对得起一向以谨严著称的日本中国史研究?还是花69元人民币的读者?抑或还是有民族情结的中国人民?
以上仅是不知无畏的后学的“谬-见”,阅读还在继续中......
附录:稲葉一郎著《中国史学史の研究》 ,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06.2.
序言—中国史学史の課題と方法
第1部 戦国諸子と歴史認識
第2部 紀伝体と編年体の成立
第3部 劉知幾と『史通』
第4部 司馬光と『資治通鑑』
第5部 地方志の発展
第6部 章学誠と『文史通義』
附篇 何休『春秋公羊経伝解詁』の歴史観
《中国史学史》读后感(四):直入塔中,上寻相轮
程颢曾讥讽王安石“谈道”,只不过是在塔外“说是三级塔上相轮”而已,未能“直入塔中,上寻塔轮”。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如何能竟塔顶之功?余英时在《论戴震与章学诚》中提出“内在理路”(inner logic)研究法,在研究中抓住思想演变中的内在线索。史学是人类对自身经历的过去予以自觉认识的过程,史学史研究的“塔顶之功”就在于描绘出暗含在纷繁著目中的历史认识轨迹,内藤湖南的《中国史学史》即是此类研究的典范之作。
“史”在商代的象形字为手持簿书的形状,最早指记录文字之意。对于“史”或史官在周代的演变,湖南借用《周礼》论述周代史官的职掌,这与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点基本一致。儒家经典来源于“史”,后者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指周代史官的职掌,简单来说史官在周代负责保存所有文字与记录“先王政典”。《六经》是对古来前言往行的记录,因此《六经》所体现的不过是记载圣人之道的“器”而已,撰写《六经》的材料来源于“史”或史官的记录。清代的汪中与龚自珍也持类似“六经皆史”的观点,前者认为史在周代的世官中具有重要地位“史外无语言,史外无文字,史外无人伦品目”,即三代的所有“道”(思想与学问)都是通过“史”保存下来的;龚自珍进一步阐释“史”与经的关系,《六级》是周史的宗子,诸子是周史的小宗。总之,三代之际经史不分,刘歆、刘向父子作《别录》与《七略》整理西汉的传世文献时,就把书籍与“史”结合在一起。《汉书·艺文志》则根据刘氏父子的研究将儒家经典予以固定,即《六艺略》(《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六艺是《隋书·经籍志》中的“史部”书籍(我们现在所称的“史书”)的渊源。湖南认为《易》三代职官所掌卜筮之法的遗存,儒家在战国时期与诸子对抗时需要哲学,于是吸收了《易》。《尚书》一般认为今文经比较可信,古文是伪作,今文《尚书》中大部分内容也是孔子之后编纂的,是儒家在与其他诸子对抗中为了显示自己有传世的系统而炮制的作品,形成的最初是以有关周公的内容为中心,即孔子或其门人为了复兴孔子作为理想的政治形象所作,后来儒家内部形成了“寓王于鲁”的思想,《尚书》则增加了《费誓》;后来又逐步加入《尧典》、《吕刑》等等。《诗经》的多数成文于西周末年,其中《周南》、《召南》为“正风”,是周公、召公教化时所作,以下的《国风》为变风,是周道衰微,教化不行时所作;《诗经》与《春秋》密切相关,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王之政化普及,或“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是作《诗》的年代,而后周天子失去王道,《诗》也就不再有传播教化的功能,关于《诗》的创作也随之停止。王者教化不张,那么《诗》亡《春秋》兴,周天子在其位无法谋其政,那么孔子作《春秋》代行天子礼乐征伐之职,以《春秋》立法,孔子行天子之事,拥有了“素王”的地位。与《春秋》有关的是“春秋学”,公羊学与《左传》比较重要,前者强调大一统,汉代出于学问上、政治上、记载上的统一,采用《公羊传》,把孔子的学问统一起来;《谷梁传》则是为了订正《公羊传》中义理难通的部分;《左传》最为流行,叙事详备且长于义理。总之,六艺皆是“层累形成”的经典,其内容的增减一直与儒家思想的发展结合在一起。再看诸子学,《汉书·艺文志》认为,诸家(包括儒家)都是古代的官职,在原来传家的官职失去职守后,职掌变为了一种营业而创立一家之学,比如道家出自史官(掌图书)、阴阳家出自羲和官(掌天文历法),不一而足,此与后世龚自珍的观点一脉相承,后者把各家的职守都归到“史”中,值得注意的是诸家之间在战国末期有这样的趋势:诸家取长补短,都强调自己兼采众家之长。《汉书·艺文志》成文之时诸子与六艺尚无太大悬殊,甚至王充认为诸子可以补苴六艺之罅漏,新莽东汉时期儒生有意识地再造皇帝权力,儒学地位抬升,经学逐渐神圣起来,诸子被斥为子部;直到乾嘉学派重新发现诸子与六艺平等的痕迹,最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平等的眼光”(蔡元培语),“新汉学”的典范借此建立起来。诸子与经学之间的关系乃是把握中国学术史发展的一条重要线索,应为读者注意。
暂时写到这里,有时间再补全。
读了内藤先生的《东洋文化史》(林晓光译)再读这本《中国史学史》,之前对于先生的某些偏见完全可以抛开了。不知记没记错(因为《东洋文化史》这本书已经借给好友而不在身边了),在序言部分,宫崎市定曾经说过内藤湖南能够舍弃附属的次要的一切,而能抽丝剥茧地反映出历史变化的深刻脉络。因此在论述大的框架的时候,难免会语焉不详,阅读体验不太好,但如果去看这种专门的学科史的论述,会发现先生的议论真是鞭辟入里,一针见血。
之前也看了一些关于史学史的书,比如蒙文通的《中国史学史》,我当时记录的是:“这本书里主要侧重的是两宋史学史。明清史学史阙漏,实在可惜。当然了,宋以前也是可以讲的,不过学术气味就不是太浓了。因为史学还没有发展完善好,何论史学史呢。刚刚起步罢了。”。因此是颇没有收获的。比如白寿彝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卷)》,当时记录的是:“给五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史学史很重要,不代表这本书很好。之后应该还会看看名家的著述吧。”。因此是颇不满意的。周文玖的《史学史导论》,当时给的评价是:“这本书可以供入门所用。看了之后,一些基本的概念就明晰了。名曰史学史导论,实际上更像是史学史的学史。讲了一些大家对史学史的研究。有一种二次文献的感觉。挺好的。”。应该还是没有抓到我心坎上。因此读完内藤先生的这本,很有些醍醐灌顶的意味。有所得,写点东西是不过分的。
回顾之前,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史学方面的书应该就是《资治通鉴》、《廿二史札记》和这本《中国史学史》。《资治通鉴》因为战线拉得过长,断断续续看了一年多才勉强看完,后汉、五代那部分甚至是草草翻过去的(因为不感兴趣)。因此快乐便不像后二本来的那么真。内藤先生在《中国史学史》中对《廿二史札记》评价颇低,但是以我来看《札记》“博澹虽不能及,整理未必有愧”,也是一本不读有憾的书了。
回归正题,大师著作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于,虽然未必能够有条理清晰的条目章节,但是对于该领域知识的宏达把握、旁征博引和一针见血的议论是最吸引人的。这本书正是如此。正如我之前所认为的,“宋以前也是可以讲的,不过学术气味就不是太浓了。因为史学还没有发展完善好,何论史学史呢。”,而这本书最好的部分也是在宋以后,特别是明清易代之时。对于宋以前的史学,内藤先生论述的也颇为经常。大家做研究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敢于在别人不敢议论的地方发表议论。譬如对史记,对汉书。瓯北《廿二史札记》对史记和汉书的体例也做了比较,大体上是持平公允的,但是很多时候持平公允并不能反映出现实问题,我们还是想要有理有据的优劣之分。我不确定内藤先生对于秦汉史了解多少(因为我看内藤先生的《中国史导论》里面对于汉初的叙述错误还是比较多的,譬如汉文帝的妃子窦太后而非汉景帝的妃子,霍去病活了24岁(公元前140-前127)而非活了26岁,卫青并没有强迫长公主为妻等等),但是这些历史细节如果要追述其实也是没有多少意义的(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人订正一下,不然不了解内藤先生的人初读这本书还以为先生是个不学无术的妄人)。但是先生对于《史记》和《汉书》的拿捏还是十分精要的。大体上是说后人如何评价史记,后人如何评价汉书,出于怎样的目的,出于怎样的观点,观点正确与否,是否含有偏见,评价者的史学才能如何种种。前四史是很多人研究的,因此从千家中找到分量最重的评论也是实在是不容易的。内藤先生似乎没有去过关中大平原,我看内藤先生的著作中有到过北京、南京、上海、湖南湖北之类的,做史学研究这样的学者到了这样的境界似乎文笔都不会太好,不过内藤先生的诗词读起来还是有味道的,“儿女英雄千古恨,君臣宰相一杯春。”几首是有清诗鲜明的特点。此外插一句题外话,看了内藤先生和中国学者的对话,譬如严复之类,觉得文廷式和张元济还是颇有些见地的,尤其是文廷式,似乎对于时局有着超然的看法,很不一般,其他诸人倒是可以忽略。如果内藤先生去过关中的话,应该会对太史公有着更多的赞誉,因为先生确实会经常发一些别人不敢发不能发的议论。这是很遗憾的。
下面整理一下《中国史学史》这本书中提到的文献:
中国史学史大纲
清代史学:
清代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