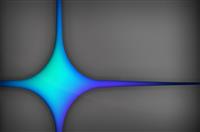
与一些心想,合其阑珊,鸣苦,投怯。很多思绪在整理,纠结,难放。似乎看清一点点,又好像还是很迷蒙蒙。干脆坐在心坎上,看着眼前,道路错综复杂,又隐隐只有一条正确的出路。
完全不加掩饰的自己,是不是不那么可爱?呵呵。无人动容的指尖心事,只是一曲自己的挽歌。往后,或笑,或泪,或言,或哑。素心夜独白,纯净眉目,清泪吹干诉憨人。一笺字,断心语。 生活在往复循环,只是凉薄渐渐深厚。吐字清晰,冷意逼人。隔绝了亲疏远近,予自己一片碧落,终夜文字,旁观着人面,在远远近近的距离外。做着自己的一些事,说着自己的一些话。淡远了一切的尘嚣,他人有着他人的尘事,自己有自己的梦话。心肺偏爱地抽紧我的疼痛,心率异常高频。就这样安生而自灭吧,可怜的周进,提着你的灯箱,踱夜挣扎。我的世界本是自己,不曾有谁停留。就是这样一个自生自灭的过程。而我却习然于在韶光里知天命,而度流年。夜,寂静的落下,没发出一丁点声响。我想,它大概是累了,孤独的累了,它需要月亮慰藉,于是月亮就出现了,而我呢,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有我,但一切没有月,是寒冷的天,任何谁都不得逞。
会独自裹着被子蜷缩在黑漆漆的角落,模糊的看着天花板上一道道光影,我知道那是时间流逝的印记。渐渐地,我到了半梦半醒之间,才发现,从早我就喜欢上了这种感觉,尤其在夜晚,就越发的强烈。窗外,黑幕洒下朦胧的雾,透过雾可以清楚的看见远处若隐若现的峰角,接着是一排排高楼接踵而至,挡住了原本的寂寥。行道灯处占据着整个世界,心又往哪去躲呢。所以,一片叶影挣脱出满是细缝的朽树,它坠落着,被寒风卷起,回旋到空中。它再次坠落,银光一闪间,小水洼中便荡起一阵心伤。夜,寂静的令人惆怅,走在无边的尽头,仿佛一切都是注定,虚无中的真真切切,无依无靠间,便释然的发现,一个人久了,就懂得更多了,便更加伤怀。
永远,在嘈杂的人群中,看着一个个陌生的面孔,他们表情各不相同,一个眼神,一个颤抖,都会传递出不一样的故事,仿佛一桩桩罪过。我不知万般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想,它的的确确能真实的让人分辨出你所拥有的颜色。虽然现在置身于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但依旧如一人前行,心还是凉的,只是有些触动罢了。
月丝缝合了我的双眼皮,缝透单薄的眼皮,模糊的对着世界,月呀逃去,渐行渐远。恍惚发现,我醒了,清楚的看着一切的一切,想用冰冷的手触摸心灵深处,却怎么也够不到,走到窗前,抚摸着玻璃传来的寒气,是啊,冬天了。空中云影化作愁脸,灰白的天又要快下雪了。淡淡的一瞬间,黑色就化为乌有。但时间过得真快,以至于在发现时,一切便成了遗憾。有时无所事事也是件好事,能静静的享受自己所谓的浪漫和自折,毕竟在所有想象面前我还是孤独的。
岁月能让人改变原有的想法,同时也能让人改变原有的自以为豪。此时,一件事往往能勾勒出不同的念想,它会影响你的此刻,却影响不了永远,也许,明天你还会回想,但一切以成空白了。定格在那一刻的唯一办法就是沉睡,呆呆的睡,可惜没那么轻易。心如灰尘,洒落到哪,就是哪,面对未来,我有梦,回忆过去,我有泪。但谁又知道未来的能否,过去的清晰。忧郁的文字,快乐的言语,有时真的琢磨不透,伪善的面孔,又能分辨多少,幼稚往往会相信虚伪,天真往往会相信谎言,我想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让人始终琢磨不透,有人也怎么说过我。
月夜落,风卷残月,夜死落归。雪映夜变格外的白,但白的幽深,白的刺骨,一个人静静的遥望,最远处的峰角,这个冬天也许这般度过。留不下的,就放它而去吧,独自坐在冰冷的书桌上,拿起与我同命相连的钢笔,书写我,以及我的一切。现在的我,只能在字里行间,寻求真实的自己,也只能在字里行间。当一个人找到有所寄托,有所喜爱的话,那么就相当于所被囚禁一样,只是比肉体的囚禁快活多了,如我。
窗台上的豆芽没有开花,只有它在我心里的影子陪着我醒了,告诉我陌生又熟悉的一天又要开始,你不知道的事。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每天都如出一辙又状况百出。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此声里跌跌撞撞,在烦闷中匆匆忙忙,在泪水上影影约约,未来会在某个夜里提笔写下:彼时年少,此时已老时,想想,我还是我,不懂的我。
曾经耳机里的《七年》已换成了《白狐》;曾经对一件新鲜事物的痴狂迷恋将会变成浅尝辄止;曾经因为一件烦事而聒噪只会摆摆手缄默不语或者莞尔一笑。
频频回首,纵使年轻,正值血气沸腾,伤,也不没意思。我的存在就是耻辱,就是疼痛,这是无需言说的,因为我这不是写文章,也不是诗。
或许在这些曲折记录的文字里,能麻醉隐藏很深的疼痛,就像刀子新划开的伤口,滴着殷红的鲜血。
癸子十一月二十九画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