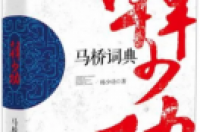
《哈扎尔辞典》是一本由(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8.80,页数:31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哈扎尔辞典》精选点评:
●当阴与阳的拇指互相触碰,我们连接永昼与永夜的断裂,便可寻获字母词句之间空白处的神性。
●黄封面
●奇书
●看不懂。。云里雾里的。。
●"人日有一死,此即为睡梦,睡梦乃死亡的预习,死亡乃睡梦的姐妹。”
●看的我一头雾水
●看晕了,没有足够的孤独来读这本书
●都是我的最爱!
●图书馆的书,有好心人为其中某些词条标上了页码,也决定了我只能匆匆按页码读上一遍而不是随心所至探寻这个庞大的故事。一直不不喜欢后现代派小说,整个形式的支离破碎妨充满了一种企图,但有时只觉充满新意。这书用词条的方式穿插了三个不同时代,以梦和神话为核心将人物联系在一起,其间充满了我无法抗拒的华丽想象,比如一上来那个阴镜和阳镜的故事,还有种种奇妙的比喻。但由于阅读方式的偏差,导致我始终抓不住这书的核心,在宗教选择上的各执一词,捕梦者和两个互相托付梦的人的同死,对死亡的体验。或许试图理解梦境的,本就皆是虚妄。
●太给力了,好想掀开爷爷的脑壳看看~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一):快镜和慢镜
某年春上,阿捷赫公主说:“我习惯于自己的思想一如习惯于自己的衣裳,那些衣裳的腰围总是一个尺寸。”
为了给公主解闷,奴婢很快给她拿来了两面镜子。这两面镜子表面上与其他哈扎尔人的镜子并无不同,都是用大块盐晶磨成的,但一面是快镜,一面是慢镜。快镜在事情发生之前提前将其照出,慢镜则在事情发生之后将其照出,慢镜落后的时间与快镜提前的时间相等。两面镜子放到阿捷赫公主面前时她还未起床,她眼睑上的字母还没有揩去。她在镜中见到了自己闭着的眼睛,便立刻死了。因为快慢两镜一前一后照出了她眨动的眼皮,使她平生第一次看到了写在她眼睑上的致命的字母,她便在这两个瞬间之内亡故了。
她是在来自过去和来自未来的字母的同时打击下与世长辞的……
(《哈扎尔辞典》)
石墙:http://blog.sina.com.cn/u/1492534280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二):旧文-小年的我们如此渴望的永恒
最后一批云燕飞过了多瑙河,它们翻转身子飞翔,水面印出的不是它们乳白色的胸脯而是黑色的背脊。雾季到了,鸟群越过森林,越过铁门,默无声息地南飞,仿佛它们把整个世界的寂静都汇集在它们身上了。
——《哈扎尔词典》
冬天的上午,窝在温暖的被里,读一本关于死亡、生命、梦、灵魂和信仰的书。窗帘拉得很严,一边看,一边在想,外面是不是在下雪,因为这个上午是如此轻柔安静。但还是接着把书看下去,每翻过一页,在书页翻动的声音里,我在想,外面是不是有雪花在飘落。
从前有个人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我盯住构成这间屋子的三面墙,他们不动声色。然而他们已不是他们,我清楚地知道,他们已在时空里又转过去一些了,而我也已经不是那个我。
千禧年的到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有他们自己的千禧时刻,这么纷繁浩渺的千禧究竟又有什么可喜呢?
一片雪花落在窗前静止的栏杆上,先是他的边缘,然后是他的身体,这个过程可以是片刻,可以是永恒。他边缘的时间先于它的身体,他在片刻中也在永恒中抵达了归宿,或者永远都在到达前的漂泊。
从前我说,没有了时间,空间照样存在。
没有了时间,还会有运动吗?雪花会怎样地落在他的归宿上呢?
合上书,我去拉窗帘,窗外雪落纷纷。
我用一支脚踏进去的那条河是一定在的,我能感到河水的凉意、温暖和湿润,感到水草和游鱼从我光滑的脚上痒酥酥地掠过。可是,站在时间的一点之上,我和我濯足的那条河都已经过去了。
《哈扎尔辞典》读后感(三):夢的拼貼
哈扎爾是一個在拜占庭時代存在的王國,《哈扎爾辭典》一直記錄這個曾經存在的沒落王國的歷史。當時由於國王發了一個夢,他召見了三大宗教派系的領袖,分別是基督教、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使者前來解夢,誰解得最準確哈扎爾便歸順於哪個宗教,結果展開了哈扎爾大辯論,後來哈扎爾改信了其中的一個宗教,不久就亡國了,但當中很多歷史史實已失傳,無法考究。這部《哈扎爾辭典》分為紅書(基督教)、綠書(伊斯蘭教)和猶太教(黃書)三部份,綜合了這三宗教各自記錄下來的史實,並是以辭典的形式記錄的,它不用時序處理,反而是字母的次序來記錄,但畢竟它不是一本辭典,每個人名和事件等都記載了關於那個名字的故事及歷史。從辭典反映的「資料」來看,三部書記錄了三段時期的事件,成了一個3x3的matrix(我猜想3會否是三位一體的象徵),它沒有說「輪迴」,但透過托夢,人物其實不停地轉世,或者是來回時空的旅程,在一段三個人的關係裡,兩個人互相「托夢」,即是彼此是對方夢裡的形象,是虛和實的兩面,另外有一個「捕夢者」,他可以深入這個夢中,如果一個人在現實死了,另一個便永久地停留在夢中。就是透過夢境,這些人穿梭時空。這本書是名符其實的「尋夢園」。
作者描述了哈扎爾這個部族,可以看得出這個民族只是個小國,而且哈扎爾人地位低微,甚至在國內所有外國人的地位也比哈扎爾人高,作者表示其實他這個哈扎爾部族比喻他家鄉和附近的少數族裔,如塞爾維亞人、阿爾巴尼亞人等。
陰陽
此書分為陰陽兩個版本,每次哈扎爾辭典被譯做外文,作者註明陽版(masculine)和陰版(feminine)必須同時出版,就像中國的陰陽一樣,有陰陽的結合才是完全,其實兩個版本中只有一個段落十多行的字是不同的,他在書後對於陰陽兩個版本給了一點意見,他說就像一男一女原本孤獨的個體相遇後,看兩個版本然後互相對照,當他們發覺其中的分別後,便像骨牌一樣成為一個整體,以後他們不再需要這書了。在書中最後一封信裡,一個教授交給女人整疊《哈扎爾辭典》的複印,這個教授本該是女人的仇人,但當她接到這個歷史的縮印時,她內在起了微妙的變化,陽書說當他的姆指碰到她的姆指的時候,她覺得這個動作變成了一個過去和現在的交接,在這一刻裡她感到迷失,她回過神來時覺得她已經有所不同了。陰書說,當她看到他遞《哈扎爾辭典》來的手,她就想起一顆樹,當一顆樹向天堂生長得越高,它的根深長到地獄也越深。這兩個版本成為了對歷史和知識的承傳的兩條軸,時間和空間的承接和增長。
帕維奇說,從古至今作者一直改變寫作的模式,但讀者只用一個方法去閱讀,他便嘗試去改變閱讀方法,他說別人都在想出色的作家,但他一直在想出色的讀者,那種作品與讀者的互動性在各處也顯而易見的,要讀這本小說,讀者確實要花不少功夫。
辭典小說
這是一部所謂的「辭典小說」,就像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裡一樣,不過不是對某一個詞語的不同看法,而是在一些人物或事件名字再加以解釋,在這些解釋的片段裡穿插了一個故事,這本網形的小說就像拼圖一樣,一塊一塊地去拼合一整個故事的畫面,故此依照作者的意思,這書可以從甚麼地方開始看都可以,甚至是打亂所有次序看也一樣得出整個故事。當然,這個「辭典小說」擁有它的後設小說(Metafiction),它的這個形式已是作者表達的一部份,他喜歡辭典的形式是因為辭典有別於不同的書,他沒有連續性的,也不需要一次過看完,這一類書是需要長時間地灌溉的,逐少地摲進式地滋潤得出的果效更多,他將此引申於閱讀。
寫作特點
其實一路讀來,這書和波赫士所表達的概念非常相似,有些地方更是波赫士的伸延,也有些情節似是作者刻意營造波赫士筆下的情景,如環形廢墟,與夢中人互相指向的關係等,關於夢境的概念尤其相似,很多評論人也提及波赫士的《特隆》,無論如何,他將波赫士關於夢境、記憶、時間等多種概念繼續延伸下去,就正如《哈扎爾辭典》裡將辭典不斷承傳一樣。
有別於一般傳統小說,《哈扎爾辭典》充滿不確定性,由於它是三堆的歷史資料,它沒有敘述一個客觀的事實,因為當時發生的「真相」已無人知曉,紅書綠書和黃書都寫道在哈扎爾大辯論之後,哈扎爾人都改信了自己的宗教,三個宗教都分別各執一詞,故此不難發現這三部書當中有互相矛盾的地方,作者也將詮釋的責任歸予讀者,讀者愛怎麼讀就怎麼讀。
其實這書已包含了幾乎所有所謂的「後現代小說」曾出現過的特徵,除以上的特點外,還有循環指涉,小說由《哈扎爾辭典》為起源,在拜占庭時代已被寫下《哈扎爾辭典》,當中經過多次的修改,依作者的意思,最後的一次修改應該是讀者手上的這本《哈扎爾辭典》了,故事裡出現的這本書其實就在讀者手上。
還有他亦有對寫作的意見和讀者的互動性,還有互文性,很多的寓意和資料也在此書裡,它確是名符其實的一本辭典。
「基里爾兄弟也用此法對待斯拉夫語言——把這種語言打破,通過基里爾字母的窗柵空隙,將碎片放進嘴裡,用自己的唾沫和腳下的希臘泥土把碎片粘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