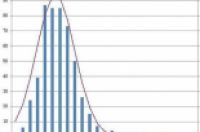
《钟形罩瓶》是一本由[美] 西尔维娅·普拉斯著作,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32.00,页数:25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钟形罩瓶》精选点评:
●要不是没找到其他版本,不会买这本
●一天什么事情都没干,只坐在床上,一口气看完这本书,现在正在去买啤酒的路上...
●没有相似经历的人读不懂的,也是幸运的。
●序言和推荐语太恶心了 这种对作者丝毫没有尊重和理解 只知道贩卖“美人”“绝恋”和作者痛苦的作序者到底是怎么混进来的
●一口气看完 看完发呆半小时
●女作家。译得一般。序言也不上档次。
●前言很好,摆脱了老套的评论模式,不写什么文学意义,以平视的角度讲述作家逸事,是一种新颖独特的表达方式,需要沉下心来慢慢品味。
●在吃了感冒药后以浑身酸痛,呼吸黏滞的状态来读,倍感亲切,甚至可以真实地体会到书中的大部分情感、氛围——拜她精准的描写所赐。看大部分小说总有总有隔阂,即使再贴地气的题材都不行,可是这篇,你会觉得这就是在身边发生的事情,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一场一场地过幕。看到她在大雨中贴着父亲的墓碑哭泣,在那个灵魂几乎被蒸干的夏天倒在一个素不相识的年轻水手怀里哭泣,在杂志社拍照时想要摆出写诗者的姿态却只能握着一支玫瑰哭泣,熟悉的「热春光一阵冰凉」又回来了,几近是微笑着等死。但是,但是,又觉得看到这样的体察和思索,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理解,实在难得。类似于浮于半中的,静静的凝视。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提及自己的自杀经历时平静得若无其事,越来越压抑。本来想给四星,但是序言写得太差了,烂得锤地,扣一星。
●我的问题在于痛恨鲜血淋漓
《钟形罩瓶》读后感(一):女文青的抑郁症出院报告
西尔维娅·普拉斯(Sylvia Plath),美国著名女诗人,小说家。诗集《庞然大物》《爱丽尔》被认为是1960年代“自白派”诗歌的代表作。八岁那年父亲去世后,她便不断在诗中吟诵死亡,也曾多次试图自杀。1956年,与英国著名诗人特德·休斯一见钟情,闪电结婚。1962年两人分居。1963年本书出版三周后,她自杀身亡。
《钟形罩瓶》读后感(二):《钟形罩瓶》
《钟形罩瓶》是美国作家,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写的一本小说。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普拉斯的自传,因为书里的事件跟她真实的生活有挺大的相似之处。《钟形罩瓶》讲的是埃丝特格林伍德得了抑郁症的感受。埃丝特在纽约的一家杂志当一个实习生,但她老是觉得很无聊,枯燥。埃丝特在书里面慢慢地变得抑郁,一次自杀未遂。
《钟形罩瓶》是本写的特别凄美的书,讲抑郁症和埃丝特的感受时很真切动人。这本书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在痛苦后重生的过程。埃丝特,书里的主角,对生活中发生的应该激动的大事儿没有兴奋的感觉,,像她的求婚和大学的成就。她自杀未遂之后慢慢的恢复,下决心生存下去。我觉得埃丝特的感受是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的。在现在非常快节奏的世界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像埃丝特一样感觉生活走得太快了,我们都没时间去体会和回味,就逐渐对生活厌倦了。但埃丝特最后还是决定不想死,还是决定要生存。她经过那么多痛苦但从痛苦中发现自己,并决心生存下去,就是一种重生的过程。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普拉斯很多时候会用镜子这个物体来反映埃丝特对自己的反思。埃丝特总会面对镜子里的自己思考。她自杀未遂之后,看到自己血腥,伤痕累累的脸,都不认识自己了。这就说明埃丝特觉得她外形和内心有很大的区别,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她在镜子里老是不认识自己,也看出来她不懂自己,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埃丝特感觉生活中别人对她的看法和她自己内心的想法,总会有很多矛盾。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别人的赞同和认可,从我们的同学,朋友或父母那里。这会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并造成外部意见和自己内心看法的矛盾,并引起对生活的厌倦的。
《钟形罩瓶》读后感(三):《钟形罩瓶》
《钟形罩瓶》是美国作家,诗人西尔维娅普拉斯写的一本小说。这本书也可以说是普拉斯的自传,因为书里的事件跟她真实的生活有挺大的相似住之处。《钟形罩瓶》讲的是埃斯丝特格林伍德得了进入抑郁症的感受。埃斯特在纽约的一个家杂志当一个实习生,是一个很扣人心弦的事情但她老实是觉得很无聊,枯燥。埃斯丝特在书里面慢慢的地变得更抑郁,很多一次以上也自杀未遂了。
《钟形罩瓶》是个本写的特别凄美的书,讲抑郁症和埃斯丝特的感受时很真切动人诚实。这本书很大的一个主题是在痛苦并后重生的过程增长。埃斯丝特,书里的主角,对生活中里发生的,因应该激动调用幸福的大事儿没有兴奋的感觉,感觉很镦和迷失方向,像她的求婚和大学的成就。她自杀未遂之后慢慢的恢复,下决心只想生存下去。我觉得埃斯丝特的感觉受是很多人都会经历过的一些感受。在现在的非常快节奏,都不停的世界里,可能很多人都会像埃斯丝特一样感觉生活走得太快了,我们都没时间去反体会和映回味过来,就逐渐对生活厌倦了。但埃斯丝特最后还是决定不像想死,还是决定要生存。她经过那么多痛苦但从痛苦中发现自己,并决心生存下去,就有是一种重生生的过程。
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发现普拉斯特很多时候会用镜子这个物体来反映埃斯丝特对自己的反思。埃斯丝特总会面对自己镜子里的自己思考的反射。她自杀最傻未遂之后,看到自己血腥,伤痕累累的脸,都不认识自己了。这就说明埃斯特觉得她外形和内行心有很大的区别,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她在镜子里老是不认识自己,也看出来她不懂自己,不知道她现在是谁。埃斯特感觉斗争生活中别人对她的看法意见和她自己内心的想法意见,总会有发生很多矛盾。我觉得这也是今天很多人,特别是青少年,面临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总是想要别人的赞同和认可,像从我们的同学,朋友或父母那里。这会可以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看法,并造成外部意见和自己内心看法的矛盾反思,并引起对生活的厌倦的可以造成内心的一个划分。
《钟形罩瓶》读后感(四):我存在,我存在,我存在
因为Lana的新歌《Hope is a dangerous thing for a woman like me - But I have it》了解到西尔维娅拉普斯,《钟形罩》是她的小说代表作。 一句话概括,这是一部向现实妥协的故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希望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被敲碎,又怎样在无奈中捡起残骸,拼凑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向现实献出假笑的。 就小说里所能呈现的内容来看,埃斯特想要的无非是这几样东西。 诗歌。爱。未来。
关于诗歌 她对待诗如同信仰。她不信教,做不到全心全意地笃信那些信条,却在以理性的方式来爱诗歌如同爱真主。她将诗歌置于生命价值之上,有一种近乎固执的虔敬。 「人的身躯不过是尘土,我觉得救治那些尘土一点也不比写诗高尚。人们悲哀时,卧病时,失眠时,会想起那些诗篇,默默地背诵给自己听。」 「我多想在太阳上打磨自己,直到变得神圣,细薄,完美,恰似一片刀刃。」一双洞明世事的眼太锐利,她追求艺术,虽不是故意为之,但她对生活也有着同艺术般的严苛。化身为利刃,剖开得了生活里最幽细的纤维,救不了最通透的自己。
关于爱 她厌烦女人婚前要坚守贞操或者是女人需要安全感这样的滥调,她有自己的理想和野心,有诗人的赤诚与洞明,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与期待,怎么可能忍受得了乏味,怎么可能甘心把自己精细的毯子当作踩脚垫在厨房里变得污渍斑斑呢? 「巴迪·威拉德曾不怀好意地对我说,等我生了孩子,看法就不同了,好像他很懂似的。他说我就不会再想写诗了。我便也逐渐觉得,也许结婚生子,真会像被洗过脑筋,人就会变得麻木不仁,沦为奴隶,活在极权统治的私人王国里。」 「我心中明镜一般,结婚之前,无论一个男人如何对女人大送玫瑰、献上温柔亲吻、请吃精致晚餐,他心里头只暗暗巴望立等婚礼结束,新娘就会像威拉德太太厨房的垫子一样,铺展开来,任其蹂躏。」 她的男友巴迪·威拉德过着双重生活,表面看纯熟不知世事,实则懦弱又虚伪。 「巴迪写道,他可能恋上了一位护士,她也患了肺结核,但他妈妈已经在阿迪朗达克山中租下一幢小屋,用来度过七月盛暑,要是我愿意和他妈妈一道去,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对那护士不过一时昏头。」 也许不过昏头。这根本就是一种威胁了,把自己的底牌揭穿,邀她演绎一出恩爱甜蜜的戏码,满足他的虚荣,满足旁人的期待。 哪里有爱?只有委与虚蛇下的利用与谎言。 面对自己有好感的康斯坦丁,她心中逐渐生发的对爱的不信任感,使她的爱意终于因情生怯。这种求不得的痛苦,在她心上硬生生凿出一道口子。这是埃斯特绝望的开始。她在杂志社照相的时候,握着一支玫瑰,望着镜头,忽然嚎啕大哭,她知道她要以诗人的身份出境,可这个身份如此单薄——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 这样的结果未必不是她性格使然,一旦有人贴近,就忍不住审视,一审视就会发现瑕疵,而一点瑕疵就足以构成推却的理由。「我会远远中意某个男子,觉得完美无疵。然而一旦他靠近,我便立刻拒之千里。」 她一直想学德语,在她九岁那年去世的父亲也说德语,以至于她「每次拿起德语字典或德文书,看到上头那密集、黢黑、扭曲得如同绞丝网般的单词,心智便立刻像蚌壳一样死死扣紧。」 后来在她盘算着如何自杀的途中,去了父亲所在的墓园。 Calling from beyond the grave I just wanna say "Hi Dad" 「爸爸葬在这座墓园这么多年,家里居然没一个人来看过他。我妈不让我们参加他的葬礼,因为那时我们还是小孩子,而他是在医院咽的气。因此上,这墓园,甚至他的死,对我似乎一直恍若隔世。 最近,我心中愿望强烈,要补偿这么些年对父亲的怠慢,就得开始拜谒他的墓地。我曾深得父亲宠爱,所以由我来补上母亲从不费心的悼念,似乎最合适。 我想要是父亲不死,他就会教会我所有关于昆虫的知识,那是他在大学里的专业。他还会教我德文、希腊文、拉丁文,这些他全懂。那我也许就会成为路德会教徒了。我父亲曾为威斯康星的一名路德派教徒,但这个教派在新英格兰过时了,结果他就不再信仰路德教派,而我妈就说他是个心怀怨怼的无神论者。」 埃斯特对书中的男性几乎没有什么好评价,除了父亲。这是书中唯一一次埃斯特带着温情回想起自己的过去。回想起因和巴迪一起滑雪的时候骨折而懊恼和怨恨,回想起康斯坦丁的时候全是遗憾,唯有想起父亲,她行将凋朽的心才有片刻复苏,看上去鲜活了那么一瞬。 然而也只是得不到回应的虚幻—— 「我将脸紧贴住大理石墓碑光滑的表面,向着咸味的冷雨,哭嚎我的痛失,撕心裂肺。」
关于未来 埃斯特「渴望改变,渴望新奇,渴望把自己发射到四面八方,像七月四号独立日庆典的烟火,腾空而起,绚烂夺目。」 她保留着孩童般的天真却偏又装作愤世嫉俗、老于世故,在两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在爱与未来中来回摇摆。若她选择爱,选择在家庭,那么她的未来便可以一望到底,若她选择更多可能性,那么她的余生都将漂泊在风里,至死方休。十字岔口就像无底深渊,她不敢也不着急作出选择,只等哪一天摔断了腿,被迫被推向看似注定的那一边去。 「我看到我的人生,就像那篇小说中的那棵无花果树,枝繁叶茂,在面前伸展。 每条树枝的尖梢上,都挂着一颗肥美深紫的无花果,那便是一个美好未来朝我招手。一颗果子是丈夫、快乐家庭和小孩;另一颗果子是成为著名诗人;下一颗是荣膺教授,功成名就;再下一颗是做伊·吉,那位了不起的编辑。一颗无花果是欧洲、非洲和南美,另一颗无花果是康斯坦丁、苏格拉底、阿提拉诸如此类,有着奇怪名字和出格职业的情人们,还有一颗是奥运会女子航海项目冠军,在众多果子上方,更远更远处,还有好多好多别的果实,我无法看分明。 我看见自己坐在这棵无花果树下,拿不定主意到底要摘哪一颗果,只好饿以待毙。每一颗果子我都想摘,可摘一颗就得放弃其他所有。就这样,我坐在树下,犹豫踟蹰,而那一颗颗无花果,逐渐起皱变黑,扑通扑通,接连坠落,掉到我脚旁。」 「我看见自己人生的每一年,状若一排被电线连接起的电线杆子,沿着道路一字排开。我数着,一、二、三……十九根,可之后那些电线悬在空中乱晃,无论我怎么努力,第十九根后头再也看不到下一根电线杆了。」 埃斯特初到纽约,脑子里一直被卢森堡夫妇被电刑处死的事占据着——沿着神经一路烧过去,是什么感觉?而这恰恰也是她对纽约的第一印象。温带大陆性气候的城市啊,终年炎热干燥,就跟蒸笼一样扣在人们头上,热气熏得景色都在变形晃动,像一场炙烈焦灼又醒不来的梦。 这样繁华热闹让她沉迷,但事实也让她很快清醒。本来只能吃廉价排骨和肉馅面包的埃斯特,好不容易享用盛宴,却因为蟹肉含有尸毒被送进了医院。虽说只是情节,但对食物中毒而呕吐的描写格外真实,「我都像一片被淋得透湿的树叶,虚弱无力、浑身发抖。而后,浪潮又再次汹涌。我身处酷刑室,脚下、头顶、四面瓷砖雪白,冷光闪闪,将我封死其中,将我压成碎片。」埃斯特感到惊慌和恐惧,她也许会因为这次痛苦的经历而把这当作对纽约城残酷印象的先兆。 她热爱泡澡,在目睹了一系列荒诞的事情之后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它。且「水必须烫,烫到几乎无法下脚」。想起《欲望号街车》里的布兰奇也喜欢泡热水澡,只有这样才能缓解她在为维护虚荣而被欺诈折磨的疲惫的神经。那是黑白电影啊,竟然能看到袅袅的水汽的升腾到镜子上。大约水越烫越能达到效果?类似于洗礼,或者蜕皮,仿佛这样就能剥离周身所有的污秽。 「在这清澈的热水中躺得越久,我就越发感觉纯净。最终站起身,把自己裹进柔软宽大的酒店浴巾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纯净甜美,宛如一个新生宝宝。」 她就这样不断地在希望与绝望里打转,感到与整个纽约城格格不入。「整座纽约市平坦铺开,好似一张招贴画,悬挂在我窗外,灿烂而闪烁。可它在与不在,对我,又有何意义?」 在纽约的最后一夜,她把自己的衣裳一件一件抛向夜风,洋洋洒洒,犹如爱人的骨灰,向这所她曾经充满了无数憧憬的城市告别。 写作班的拒绝接收,是轧死她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整个六月,那写作班都在我眼前舒展,如同一座光明安全的桥梁,跨越夏天乏味的鸿沟。可如今我眼看这座桥摇晃崩塌,一具白衬衣、绿裙子的尸体一头栽到沟里去。」 哪里有爱?父亲早已逝去,男人们轻薄虚伪,所谓的爱不过是待价而沽,是零和博弈。 哪里有未来?纽约城的富丽堂皇无法撼动你心,灵魂于此得不到休憩,仅有的可能也被一个一个钉紧。 绝望像墓碑一样静静地卧在她心上。 「我不洗衣裳,不洗头,因为这么做好像太傻。 我眼看着一年的日子在面前伸展,如同一大溜明亮的白盒子,分隔一只只盒子的是睡眠,犹如一片黑色的阴影。只不过于我而言,那分隔一只只相邻盒子的长长阴影突然砰地消失,于是我眼前就只剩下日复一日的白昼,刺眼地发亮,犹如一条宽广、孤寂的白色大道,无穷无尽。 头一天刚洗过,第二天又得洗,好像太蠢。 想想都觉得累。」 活着就相当于监禁,日复一日的循环就像是高墙,呼吸都成了一种负担。 就像是霜冻被热春光活生生烧死,世界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但世界运转的每一步都在将你往绝路上推。只能眼睁睁等死。 她甚至开始肖想,与修车店技工或者哨兵结婚,生儿养女,做着她那认为枯燥无聊的家务事也许是一种幸福,余生就这么打发掉了也好。 但生活的重担,她又未必肩负得起。 有一段关于她看分娩过程的描写真是好,又用了一副一边吃瓜一边指指点点的口吻,更显得惊悚。女人仿佛是她曾见过的停尸床上的一块肉被人拨来拨去。 「医院工作人员正把那女人往台子上搬,看到那张台子,我震惊到哑口无言。台子的一头悬着好些金属脚蹬,另一头则挂满了各种仪器、电线和导管,我甚至看不到另一头,这手术台活像给人上酷刑。 女人的肚子耸起好高,我看不到她的脸和上半身。她活像只蜘蛛,挺着大肚子,两条细长而丑陋的腿卡在高高的脚蹬里,此外身子似乎什么也不剩了。整个分娩过程中,她一刻不停地发出呼呼怪声,简直不像人。 那位孕妇被注射了一种药物,她不会记得自己曾疼痛不堪,曾咒骂呻吟,在药物的作用下,她其实神志迷糊,根本不知自己在做什么。 我想,这种药物也只有男人才想得出来。这个女人明明感到了每一丝痛苦,才不能自已地哀鸣号叫,可她生完这一胎,回家马上就张罗着再生一个。尽管药物让她遗忘了上一次的苦痛,可那漫长阴暗的苦痛通道,无门无窗,无处可逃,一直藏在她身体的隐秘深处,静待时机重新开启,再次把她紧锁其中。」 她也许想,为了那根本得不到的爱,何苦忍受这些酷刑呢。 一扇门被钉上。 她整日整夜地与文字作伴,终日无眠,熬不住了去看了一回心理医生。大夫亦有一种用自负包装出来的温柔,总带着「慢悠悠,近乎温暖的微笑」,问她的大学,知道那里有个妇女军团,但顾左右而言他,在不了解她内心所想的情况下,就推荐她去做电击治疗。 周围来看病的人都像行尸走肉,「周围这些形体不是活生生的人,倒像商店的服装模型,照人样描画,勉力支撑,尽量显出些生机。」她这么一比较,大约也觉得太惨,绝不允许自己成为他们那样。 太愚蠢了,她也许会想。 又一扇门被钉上。 埃斯特开始精细地谋划自杀,她尝试过割腕、蹈海、上吊、服药,却无一成功,并不是意志不坚定,而是肉身的本能总可自卫于无形。 「我只能以剩余的意识伏击我的性命,不然,这条命会把我套进它愚蠢的笼子,毫无道理地把我关上五十年。 我纳闷,在上吊惨败之后,是不是该放弃自杀,把自己交给大夫们,可又想到戈登大夫和他私家医院的电击治疗仪——只要我被锁起来,他们就会不断用那玩意儿折磨我。 我想到我妈、我弟,还有朋友们会去看我,日复一日,巴望我好起来。然后他们的探访就会变少,会放弃希望。他们会变老。他们会忘掉我。 他们还会变穷。 起初,他们想要我得到最好的照顾,于是就把金钱统统花在戈登大夫那种私人医院。最后,钱花光了,我就会被换到一家州立医院,和成百上千和我一样的人一起,关在地下室的笼子里。你的病越没法治,人家就把你藏得越深。」 他们还会变穷。读到这句忍不住笑出声。这本小说的亮点之一就是带着些许黑色幽默的笔调,普拉斯始终能以旁观者的视角清晰打量这个像自己又不是自己的埃斯特,抒情段落总插上几句讽刺,像是人们在谈及梦想的时候,忽然有没情商的人闪入其中,没头没脑地搭了两句嘴来戳破现实,活气毕现,又令人哭笑不得。 埃斯特的身体经不了几次折腾,还没死成,就又被送进了医院。 她一睁眼,就看见母亲焦虑的神情,听见弟弟不知所措的问候,她的老同学看到她这副样子,也许还要来嘲笑她。 但是这些关心也一样毫无意义啊。没有人了解她的病根。 埃斯特的母亲爱她,却不理解她,听闻女儿生了病,就算急得快要哭出来,也只会把她往医生那里送。她们的交流仅止于物质层面上的嘘寒问暖。 她如今变得坦然了,既来之则安之,没那么执着地想自杀,大概经历了那么多次自杀也失败之后也颇觉得好笑。 她现在只有两个选择。好起来,投入世俗中看似正常的活着?在这日复一日的治疗中熬煎过余生,被一个个医生给放弃,从一个医院转到另一个医院?什么,什么都无所谓了。 因为心死,所以面对什么境况,微笑都不是难事了。她会认真地敬畏做过脑额叶切除术的病友,再也不会生气吵闹,再也不必受情绪波动的撕扯,「永恒的宛若大理石的沉静」也不错。 Hope is dangerous for a woman like me. 这样的你,有希望就会去抗争,争又争不到自己想要的,衍生出的绝望反而像潮水一样吞噬了你。 你这是何必呢。 在医院里,她遇见了琼。对于这位与前男友频繁往来的女生,埃斯特向来没有什么好感,然而事已至此,她也忍不住对境遇相似的琼生出几分同病相怜的感情。巴迪听说她们都患上了精神疾病,忍不住问埃斯特她们的病是不是与他有关,一副不想扯上任何关系的严肃表情,又因认为这是自己的魅力所致,掩不住语气中的洋洋自得。 从前的埃斯特会做何反应?怕是早就憎恶得扭头就走了。 但现在埃斯特只会一边纵声大笑,一边闲闲地观察对方的反应,「巴迪,我们的事与你无关。」 她们的绝望,她们的期冀,她们的痛苦,她们的欢欣,自始至终都是由她们独自消弥。 你从来不会懂得—— 「尽管深有保留,我想自己会一直珍惜与琼的友谊。我俩就像被某种无法抗拒的境遇强拉到一起,好比战争或瘟疫,分享了属于我俩的世界。」 对于一直在寻求理解的埃斯特,琼是一面镜子,望着她也觉得是一种变相的相通,是与外界的连接。 但这份连接很快也断了。 在琼的葬礼上,埃斯特无声地呐喊,「我活着,我活着,我活着。」 上帝的玩笑开得不合当,会让人以为是昭示的。埃斯特知道,如果她再继续抗争下去,自己就是下一个琼。又是一眼可以望到尽头的未来。她忽然不堪忍受了。 她决定回到现实,装模作样地开始新的人生。西西弗斯忽然接受自己的命运也好,所有的抗争尽数作废也好。 这一切不过一场噩梦。 「对罩在钟形罩瓶里的人来说,如同一具死胎,毫无表情,这世界本身就是一场噩梦。 一场噩梦。 一切都刻骨铭心。」 埃斯特的故事到此结束。
对于没有相似经历的人来说,如果不了解精神疾病,又没有鉴赏人性的闲心,多半会觉得这本小说不过是苍白嘈杂的呓语,很容易就会不耐烦,何况小说的主人公并不讨喜。 埃斯特并非是那种向命运抗争的坚忍形象,事实上她的很多选择都是被迫作出的。她小家子气,对不待见的人回信都不肯多用一份邮票,有些伪善,将喝醉到呕吐的多琳拖到门口不管,指望她能自己回去,虚荣,对不怀有希望的男友,因为他邀请自己参加耶鲁大学的舞会又感到飘飘然。她不纯粹,在理想和现实之间首鼠两端。 但是她也因此鲜活而生动。 「我记得那些被解剖的尸体,多琳,无花果树的故事,马科的钻戒,共和大道的水手,戈登大夫手下那个眼镜片厚得像墙的护士,跌碎一地的体温表,送饭黑人和他的两种豆子,还有使用胰岛素时增加的二十磅体重,那块鼓在天海之间犹如灰色头骨的大礁石。」如你所见,这些支零的片段,是电影里颜色暗淡的回放镜头,是一些旁人看来没有联系的破碎物象,也是毫无意义的。「也许忘却,如同一场大雪,可以令人麻木,可以掩盖它们。」没有人知道你打翻在前襟上的菜汤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看上去只是一痕污渍。 「但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风景。」她将会永远记得。
看到很多关于这本书的评语,都有压抑二字。 你知不知道,有些故事仅仅是因为真实就足以动人?一些记录,它本身的存在,就足以构成价值,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义理,而只是想发声,说一句:我存在过。 「阅读中最美妙的时刻,当你有所领悟,你原以为只有你才能领会到,而在这里,另一个人已经表达了出来,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一个甚至已经死去的人,然后仿佛有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了你的。」
感谢西尔维亚拉普斯。像琼之于埃斯特,有时你并不需要那些对你无用的劝慰啊,一份并不完美的理解,都足以让你觉得你在被温柔地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