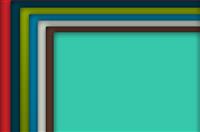天天放假,人都失去了规律性。没事,谈恋爱的谈恋爱,深更半夜才归。走朋友们的走朋友也干脆几天不回。没朋友走的就没日没夜的看录像。有赌博爱好的就聚在一处乌烟嶂气地搏杀。这是打工仔的点型生活,枯燥无味的打工生活。有拼搏精神的或有点斗志的人就跳槽到外面找工。
男的陪女的,女的陪男的。男的睡觉,女的煮饭。女的逛商场,男的不情愿地在后面跟着。男的打麻将,女的打毛衣。女的打麻将,男的打扑克。扑克的名堂很多,赌三公、打金花,锄大D……五花八门。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玩法,不怕不会,看上几天也就耳熟目染的会了。所以叫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放了几天假,毛毛就泡了几天录像厅。看完了一场又一场,到吃饭的时间就到外面买盒饭,不用考虑柴米油盐,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吃完饭回去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房间内尽是牌局,麻将局。吵得翻天覆地,何谈休息睡觉。不得不又去看录像,那比赌好,赌是万恶之首,只要染上赌瘾就是离一切罪恶不远了。
毛毛又回去了一趟,本想睡一会或写点东西。可那房间不是家里,独居一室,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谁也不影响谁。可打工宿舍不一样,一个十多平米的地方居住着八个人之多,有单身的,有半单身的,有结婚了的。
那两平方米的铁架子床,就是培养爱情的乐土,有人正在耕耘,有人正在播种。那是一块大家都仅有的唯一的,填补感情空白和空虚的地方。以前只有隔着墙壁的邻居,现在是隔着两层床帘子的邻居,从感情上是更上一层楼,人家女朋友来了,理所当然要把那空间让出来。人家老婆来了,也理所应该把那空间让给有需要的人。不能太不够哥们,守候在房间听那男人的喘气声,女人幸福的呻吟声。更有上床的人需要,毛毛还得把下床让出来,更让毛毛无奈。大家都是同命相连的人,既苦命,既兄弟,既是迫于生活环境的人,就顾不了那么多封建迷信和礼数了。
毛毛进房间就听见一阵惊惶失措的声音,很难为情。知道又是闯了谁的禁地了,毛毛只好假装拿了点东西转身出门,轻手轻脚地把门关上,就如同没发生任何事一样。其实那也是见惯不惯的事,谁都撞见过同类的事,早已心知肚明。但彼此就是要装作没事一样,仿佛谁也不知道谁回来过,谁也不知道谁在干什么一样?不知道为什么要那样做?时间长了就成了默契,就形成了潜规则,也成了相互间的理解了。要问也只有问那年代,那时,那刻,那环境。
仿佛来那房间的女人都习惯了。应该是所有群居的男人女人都习惯了。
毛毛是日看夜看,人都看麻木了,累了就在录像厅睡,那是花钱买地方睡?没办法?要不怎么说人生有很多无奈之举?毛毛那样做也算是为了朋友们奉献。
夜都很深了,要工作的人都如鸟儿归巢往回赶。路上的行人也变得越来越少,夜市上摆地摊的都收了档。本来一条挨一条的日光灯管照得到处光亮,分不出白天黑夜的。夜市的摊贩一走,整条街突然暗了下来,录像厅的门口却是灯火通明,因为那是一条充满光辉的大道,那是照亮人生的一盏灯。就是停电了录像厅的主人也不会让它熄灭?
毛毛有些睡眼蒙胧的摸钱买了票。两块钱一张,反正口袋里就两张钱,一共五十二块,那是这几天的生活费。卖门票的是一个女孩,女孩的脸很黑,两手纤纤,身材消瘦,如果是做时装模特,不用减肥就是一副天生骨感。点型的深圳女孩,长年累月离赤道太近,被晒得黑黑的也如同被太阳蒸干了一样,没有肉,缺乏水份,从蓬乱的发梢间露出一双清澈的眸子。毛毛从买票接票的时间已看得很清楚了。女孩肯定不足二十岁,从相貌和年龄和职业上判断一定是录像厅老板的女儿,毛毛太善于观察了。一双眼睛看着别人还以为毛毛是不怀好意的人。
毛毛的可乐是在外面买的,一罐易拉罐和一袋洽洽瓜子在方便袋里没开封。因为录像厅门口的东西比商场贵,这点经济帐毛毛还是算过的。毛毛很不愉快,一直捉摸着那卖票的女孩怎么就不生得白净点,长得好看点。按理说女孩卖她的票,毛毛花钱看他的录像,毫无牵涉互不相干。可是毛毛止不住就是不自觉去想那些。
午夜场划算,两块钱能看一个通宵。照样有人光顾,一般是厂里没事做放假,毛毛一类的人,还有就是倒班放假的人,当然最多的是刚到贵地连落脚点都没有的人,为了淘金,为了寻梦,身无三日粮,也不愿在外蹲墙角,也住不起旅店的人。花两块钱进录像厅寻求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也可以避免与盗匪相遇。是每一个来深的人,满怀热情却又无奈的人聚在了录像厅。
毛毛回去的时候买了瓶啤酒喝,原本想解解烦,回去好倒头大睡,用酒精来麻痹自己。没想到自己不胜酒力,一瓶啤酒喝得人红光满面,昏昏沉沉,瓜子吃了口干,可乐也就很快完了。没了可乐就不想吃瓜子,手也就停下,嘴也就跟着停了,慢慢就失去了知觉,睡着了。
椅子是那种跟电影院一样的翻板椅,很硬。前排没人坐,可以把脚从靠背下面伸过去,脚步伸直了舒服点。人睡着了就失去了控制,总是耷拉着头,颈子都弯痛。毛毛就不停的把头点一下抬一下。歪来歪去的也睡得香甜如梦。
人很累的时候睡下去,不管难不难受都不会醒的。到睡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再也承受不了那歪来歪去,毛毛也就醒了,下意识地睁眼看了一下周围,人又少了很多,熬不住都回去了,剩下的也就是那些提着大包小包没有找到去处的人。
毛毛先是看了一眼远处,毛毛又警惕性地看了一眼身边,确定一下是不是安全会有威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是毛毛最不原意看到的人,录像厅老板的女儿,就挨在毛毛的身边,刚才歪来歪去就好象碰到了什么东西?又不象是硬梆梆的椅子,把脸碰得轻微的痛才醒的。
怎么会这样?毛毛百思不得其解。想的问题一大堆,前前后后,旁边的椅子一大把,她为什么不坐?是不是想泡我?深圳开放?连女人也这么开放?毛毛看女孩的时候正好女孩也看了毛毛一眼,目光对接,不过无论怎么样也是不可能接上的?
毛毛没有看上,是因为第一印象太离谱,毛毛想起来又想说女孩简直是赖蛤蟆想吃天鹅肉。我是天鹅?好象不对,男人怎么能称天鹅?毛毛自嘲自笑。女孩见毛毛笑也对毛毛抱以一笑。母夜叉一个还想泡我毛毛?
毛毛很不好意思,毛毛赶紧起身回去,毛毛又想,想必是睡觉碰到人家的香肩了。弟兄们的事也该办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