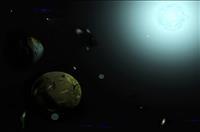水门这个古老而繁华的小镇上,居住着很多慕名而来的外国客人。他们爱死了环绕小镇的山山水水,就好像在他们的地盘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俊秀的山峰和清澈的河水。大清早,咖啡色小画眉那婉转的调子总是准时飘进卧室,钻到情人的被窝和耳朵里,催促着赶快起床;温柔的晨曦爱抚着美人儿的脸蛋,真是舒服极了。
而现年60岁的法国佬文森特﹒德﹒皮埃尔先生的精神状况却已大不如前:就在三年前,他还保持着每天早起晨跑的习惯。就在那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亲吻睡在他旁边的小宝贝的脸蛋儿时,他就起床,换上深蓝色的短衣短裤,朝着太阳的方向一路跑去。十年了,转眼间他已经做了十年的中国姑爷。当然,他每年会固定回法国两次看看孩子们,抱抱他那可爱的小孙女。除此之外,皮埃尔先生便藏进在水门镇买的这栋二层小楼里,专心摆弄着他的木雕。傍晚,他会挽着中国妻子芳芳的胳膊,在水门镇独特的夕阳下散步。
在巴黎留学的时候,芳芳认识了现任丈夫,结婚后回到了中国定居。还记得那是在吉维尼一个叫做“Tchin-tchin”(法语,音:亲亲)的小酒吧里,当时的文森特正专心和学生讲着什么。这是他的习惯,不论在什么场合,只要他觉得有必要在理论上让对方理解透彻,文森特总会一本正经、调理清晰。文森特﹒德﹒皮埃尔先生在一所中学教授物理课。那时的他精力充沛,对学生认真负责。他会记住他教过的每个孩子的名字。下了课,他会来“亲亲”酒吧喝上一杯。也许因为吉维尼是印象派大师的故居,也许是因为别的,文森特的骨子里边,也会有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东西。这些捉摸不透的内容,就好像莫奈的抽象画,有时候着实让人眩晕。肯定就是这种神秘感和对这种神秘感一探究竟的渴望,让芳芳这个年轻的中国姑娘有爱上这个吉维尼中学物理教师的冲动。
法国人天生就是浪漫的化身,不管他看上去多么一本正经。顺理成章,文森特爱上了芳芳,并且随芳芳来到了中国。他们在上海租了一间公寓,文森特找到一家外语培训学校当起了法语老师,而作为海龟的芳芳小姐,则在一家外企找了一份总经理助理的差事。头两年,文森特很满意:有漂亮妻子的陪伴,有称心的工作。可渐渐地,芳芳发现,可怜的爱人的眼睛里,总是不时流露出悲伤。他想念吉维尼,想念吉维尼的花,吉维尼的土,吉维尼的“亲亲”小酒吧,总之,可怜的法国人患上了思乡症。也许,是他根本就不能适应在中国上海的这种朝九晚五的都市生活。
有时候文森特会问芳芳,“你们中国人到底在追求什么?远离亲人,跑到大城市,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文森特感到非常不理解。他对中国人的敬业既佩服又困惑。芳芳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丈夫,如果说,那些家伙是为了钱在团团转,这种解释无疑会让法国佬更加困惑,甚至那种对中国人的佩服之情,也会因之烟消云散。说实话,其实她也不知道她的那些同胞们到底在追求什么。
芳芳不想为这事伤脑筋,反正文森特在法国赚的钱,足够他们小两口在中国过下半辈子。于是芳芳和丈夫辞掉工作,两个人过上了一路行一路走的旅行生活。仅仅一年之后,文森特发觉水门镇是个绝妙的地方,青山绿水环绕,鸟语花香、空气清新。这法国佬一下子便爱上了这个江南小镇。尤其当他看到小商店里摆着的木雕时,更是莫名其妙地着了魔。他们买下了位于楠溪江边的一栋二层小楼,过上了优哉游哉的神仙日子。文森特几乎天天忙着自己的木雕,虽然雕刻水平还比不上水门镇的孩子,但他下定了决心要当个中国的木雕匠。芳芳则每天写写文章,玩玩电子游戏,偶尔心血来潮,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几款衣服,挂到隔壁小商店里去。
无聊的日子一年又一年。
下个月又是每年一次的圣诞节,到了文森特﹒德﹒皮埃尔回法国的日子。
“亲爱的,圣诞节快来了,我们要早点订机票!”法国佬有些兴奋地说着,“不知道小阿黛尔又长高了多少。这小家伙每年的变化真大,我可能都认不出她了。”
文森特自言自语地说个没完,芳芳一言不发,背着他缩在被窝里装睡。
“怎么了亲爱的,你病了吗?”文森特觉出了点异样,扭头在芳芳的脸上亲了一下。
“这次回去一定要和我的学生们聚聚,上次去简直太匆忙,没有喝上一杯,真是遗憾!”文森特继续说着,可芳芳并未因为简单的一个吻而有任何变化,依旧缩着身子闭着眼睛装睡。
“亲爱的,你到底怎么了?怎么不说话呢?难道你不想看见埃菲尔铁塔吗?下个月就要圣诞节了,巴黎该多热闹啊。当然,我是不怎么喜欢热闹的。”
“我讨厌埃菲尔铁塔!”芳芳从被窝里挤出几个字,仍旧缩着身子闭着眼,她不想让自己挨着皮埃尔先生,也不想和他有任何交流。文森特﹒德﹒皮埃尔听到芳芳这么句话,简直感到头脑发紧。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小宝贝怎么突然间像变了个人似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亲爱的,难道你忘了你在巴黎读书的日子了吗?还有吉维尼的“亲亲”酒吧,你怎么忘了呢?”
芳芳并没有忘。当年的情景从她脑子里一点点过着。她想到“亲亲”酒吧,一种厌恶感挤占了幸福空间。她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一回忆起当年的浪漫时光,她就觉得懊恼。是啊,那时的文森特虽然比她大二十四岁,但毕竟还正直壮年。可如今的这法国人,却俨然一个老头。他整天窝在家里摆弄那些该死的木雕!搞得自己就像木雕一样。难道我也是一个木雕吗?芳芳越想越气,她干脆“腾”地一下坐起来,盯着文森特的眼睛,决绝地说:
“不要提什么‘亲亲’酒吧,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圣诞节我不回法国!”然后忍不住失声哭起来,越哭越伤心。
文森特﹒德﹒皮埃尔被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搞懵了,他在床头张着嘴像木雕一样呆坐了两分钟,然后又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话语却被堵在喉咙里什么也说不出。他无奈地轻轻拍了拍娇妻的额头,静静地躺下睡了。
文森特独自一人回法国过圣诞节。终于可以出去透透气了!芳芳就像摆脱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一样,长长舒了口气。这下只剩她一个人了,她想干什么都行。可是她到底想干什么呢?她自己也说不清。反正只要不是天天和文森特腻在一起,她就感到像重获自由的画眉鸟一样快乐。
芳芳披散着头发坐在梳妆台前,把什么香奈儿、雅诗兰黛、兰蔻统统倒出来,精心地往脸上涂抹着,不多会儿,在镜子里出现了一张妩媚动人的脸。芳芳一下子重又回到了十年前。看着这张十年前的脸,想想这十年的生活,芳芳感到莫名的恐惧。如今她已是三十六岁的年纪。三十六岁,这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就像一只画眉鸟,被关在不见天日的笼子里整整十年。一朵原本娇艳欲滴的玫瑰花,就这么,被可恶的时间给毁了。令人欣慰的是,镜子里的女人仍然如当年一样美丽,无非多了些粉饰而已。女人天生需要粉饰!真得感谢那些发明化妆品的天才,是他们留住了青春,留住了美丽。芳芳从衣柜里特地挑选出了一件她最爱的洛丽塔风格粉色连衣裙。虽然稍微有些紧,当年的柔美型变成了性感丰满型,却也不失是一次华丽变身。丰满的胸脯裹在衣裙里面,深深的事业线裸露在外,曲线顺着小腹往下走,从大腿到小腿再到脚尖,真是凹凸有致,让人浮想联翩。想不出,有哪个正常的男人会不想急于扯开这衣裙得到这女人的肉体。
芳芳满意地长时间地欣赏着镜子里不断摆着Pose的自己,真是个美人坯子。稍加修饰,就又是一个美人儿。
可看着看着,芳芳就又伤心起来,她一个人该干点什么呢?喝一杯吗?哼,去他妈的“喝一杯”吧,芳芳恨恨地想。此时此刻,她不愿意去想关于文森特的一切。看看这房子,到处都是该死的冷冰冰的木雕,只有芳芳一个活物。她丝毫不想在这个家里多待半分钟,于是,芳芳迅速套上一件长款的黑色羽绒服和高跟长筒靴,夺门而去。
外面不算太冷,套着这羽绒服甚至有些发闷。阴阴的山风随意吹着,也懒得往行人脖领里灌。街上依稀有外地的游客对着些木房子拍拍照照。真搞不懂这些古建筑到底有什么好拍的,那股朽木味儿就够让人反胃的了。已是下午四点钟,芳芳一点也不觉得饿。她厌倦这小镇,她甚至厌倦小镇的食物。那些曾经让她永远吃不腻的食物。可如今,芳芳甚至不想多看一眼。倒不如去上海逛逛!芳芳突然想。上次去上海是陪着丈夫买木雕,上上次去是去医院看一个生病的朋友。想到这,她给订票中心打了个电话,又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订了房间,便直奔车站而去。
久违的大都市又出现在眼前。闪烁的霓虹灯、车水马龙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购物中心,多么熟悉的影子。芳芳招过一辆的士,也不说去哪,就让司机随意开着车。芳芳欣赏着窗外的夜色,陶醉不已。她想,这种地方才配得上她,这才是她该有的生活。
芳芳提着一大堆衣服、化妆品住进订好的酒店房间,美美地泡了个澡。她扯过浴巾,胡乱包裹了身体,懒在床上,漫不经心地看着一部奥斯卡影片,好像导演叫做斯皮尔伯格。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照片,是米开朗基罗的雕像《大卫》,那种健美的男性身材甚是吸引人。就在芳芳想入非非时,一阵可恶的电话铃突然想起,芳芳生气地抓起电话,还没等开口,就传来了一声娇滴滴的女人声:“先生,需要服务吗?”芳芳感到莫名其妙,正在纳闷这骚女人到底是谁时,她忽地意识到她们这是做那种勾当的,便“咣”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那种勾当!恩,那种勾当!芳芳想着想着,刚刚还厌恶至极的心情,却像一片轻飘飘的云彩一样逐渐飘走了。她不由自主地盯着《大卫》想入非非,渐渐地入了神。何不尝尝那种勾当?这种荒唐的想法不知从什么地方一点点涌了出来,就像一个老巫婆的咒语一样让她感到恐惧。芳芳被施了魔法,她变得对那种勾当极其期待起来。她脑子里满是那种荒唐的想法和画面,她简直透不过气来。芳芳强迫自己静下心来,她关掉电视,把头埋在被子里,强迫自己入睡,可是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芳芳看看时间,已经晚上十点钟,干脆打开电脑,看看朋友们在不在线。可惜,好朋友一个都不在,在的那些,自己又懒得搭理。她漫无目的地看看新闻,玩玩游戏,可心思总不能安静下来。她干脆在百度搜索栏里输入“做小姐”三个字,于是跳出一堆有关如何找“小姐”如何“做小姐”的链接。芳芳随意地点进去一个,上面的文字让她越看越着迷。她竟然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尝试一下。因为首先自己有完美的身材和气质;其次自己并不缺钱,价码可以低一些;第三,她可以在酒店里尝试,这种高档酒店治安很好,非常安全。况且,入住这种高档酒店的人一般素质比较高,应该不会乱来。
这样想着,芳芳拿起酒店的电话,随意拨通一个房间号,学着那种放荡的声音
“先生,需要服务吗?”
连续打了三个,都被恶狠狠地挂掉。直到第四个,电话那头的男人淫笑着,似乎很有兴趣:“都有什么服务呀?”
芳芳似乎得到了鼓励,按照网上的内容,照本宣科地介绍着。
“那好吧,你过来吧,我等你,小妞儿。”
芳芳的心脏“腾腾”地跳个不停,她感到快要窒息而死,她觉得血液都要从血管里喷涌而出。去还是不去?芳芳左右想着。“去他妈的吧,赶紧睡觉!”一个声音说;“快来吧宝贝儿,我给你想要的一切!”另一个声音说。芳芳简直要疯了,她被自己搞得完全丧失了理智。她钻进被窝,裹紧被子,脑子一片空白。她又看到了墙上的《大卫》,好像在说“你个胆小鬼”。然而《大卫》可真是迷人。芳芳躲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可眼前却总是浮现出男女做爱的画面。她使劲掀开被子,三下五除二穿上刚买的低胸衫和迷你裙,踩上十公分黑色细高跟,照了照镜子,把头发弄乱一点,又往下拽了拽衣服领子,露出半个乳房,这让自己看起来真像个专业妓女。
芳芳紧张地敲了敲门。
“来了,小宝贝!”房内传出一个浑厚男人的声音。
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拖鞋声,门开了,一个高个年轻男人裹着浴巾站在房内,一股酒气顿时扑面而来。芳芳手足无措,丢了句“你好”便直冲房内。男人色迷迷地上下打量着芳芳,发出淫荡之光的眼睛直直地盯着芳芳的短裙,似乎他的眼睛能透过布料直射进芳芳的内裤里面。瞬间,男人像饿狼一样朝芳芳直扑而去,他死命亲吻着芳芳的红唇,用力揉搓着芳芳的乳房,像一头大象似的把芳芳按到床上。男人把芳芳的小裙急切地掀起,一把扯掉身上的浴巾开始挑逗。他时而像猎狗一样,用嘴唇从芳芳的小嘴吻过胸脯,吻白皙的长腿,直到挂着高跟鞋的性感玉足;时而用手指隔着内裤摩擦芳芳的私处,使得芳芳全身欲火焚烧。她的整个身体就像要炸开一样,她很久都没有尝到男人的滋味了。芳芳全力配合着男人的节奏,急切扯开自己的衣衫,她紧紧抱着男人的脖子,等着那最刺激一刻的到来。男人边舔着芳芳的酥胸和玉腿,边拼命拽下芳芳的蕾丝内裤,直挺挺的家伙狠劲儿插进去,飞快地进进出出出,芳芳浑身打起冷战,整个世界疯狂了。她闭着眼睛,像个荡妇一样呻吟着、索要着;男人被这淫荡之声挑逗着、刺激着、鼓励着。
整整一夜,这对淫夫荡妇变换着各种姿势做爱,直到精疲力竭。芳芳终于又尝到了人间极品欢乐。
早上醒来,芳芳发现自己赤裸裸地斜躺在床上,旁边躺着一个赤裸裸的男人。她有些慌神儿,然后想到昨晚发生的一切,感到有些懊悔,又感到有些回味。男人从睡眠中沉沉醒来,看到旁边赤裸裸的芳芳,有些诧异地问了一句“你怎么还在这里?”然后又沉沉睡去。芳芳猛然清醒了,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根本对这个男人一无所知,唯一认可的,就是他的性能力。其余全是空白。芳芳意识到,在他眼中,自己只不过是个妓女而已。她稍微有些伤感,但这种伤感转瞬即逝。芳芳认真地穿好衣服,最后看了一眼床上的裸体男人,悄然离开。
回到自己房间的芳芳脱掉衣服,泡个热水澡,赤身裸体地躺在自己的床上,回味着昨晚的艳情。她开始佩服自己。简直演什么像什么。她突然觉得,妓女是个不错的行当。既能享受欢乐,还有钱赚。钱?芳芳忽然意识到,自己原来提供了一晚的免费服务。她觉得自己真是愚蠢之极。不过转念一想,既然她想得到的是女人的快乐,又何必在乎钱呢?她不是个缺钱的女人。此时此刻,芳芳觉得自己和真正的妓女有着本质的不同。她们是为了钱,而自己是为了享受。她甚至觉得自己的行为是高尚的,因为她不但没有出卖什么,反而为别人免费服务。如果妓女这个行当有行业标准的话,那么芳芳简直是妓女里面的标杆。
芳芳又在上海随便转了几天,和朋友聚了几次,便回到了水门镇。
一切都变了。
当文森特﹒德﹒皮埃尔先生从法国回来时,芳芳特意给了他一个拥抱,还主动亲吻了他,这使得他多少有些意外。毕竟他是和芳芳吵架之后回的法国。他感到他的娇妻真是通情达理,或许是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理取闹。文森特从法国给芳芳带回了纯正的法国产CHANELFIVE,这正合芳芳的心意。法国佬意识到,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爱妻就变得更加漂亮了,脸上竟然有了红晕。
文森特想出去走走,便问芳芳愿不愿意相陪,芳芳说非常乐意效劳。于是,法国佬高兴地挽着芳芳,漫步在夕阳下。他给芳芳讲这几天在法国发生的事情。
“那么,小阿黛尔好吗?”芳芳问。
“我们的小孙女又长高了很多,我真是认不出来了,亲爱的。她还让我向你问好。”
“‘亲亲’酒吧怎么样?那个酒吧老板还好吗?”
“可怜的尼古拉斯去天堂了,他的儿子接管了酒吧。生意比去年好了些。年轻人,总有法子让生意红火下去。”
“哎,可是我已经老了,不再年轻。”
芳芳似乎有些忧伤地说,可她的眼神充满了明亮的光。
“你还很年轻呢,我的宝贝。要说老,我比你老很多。”
文森特扭头看了一眼芳芳,微笑着说道,“你还是个孩子。”
芳芳没有作声,只是挽着丈夫的胳膊慢慢走着。天上微微飘下点雪花来,一片一片落在芳芳的脸上,冰凉冰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