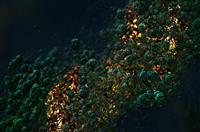今日风静高阳,天空碧蓝如洗。时至黄昏,却见天边乌云密布,浓浓阴霾沉沉而至。我独处书房,目视着垂挂在墙壁上的四幅字画《仁》《忍》《悔》《愧》良久。这几幅字是我在二十年前于山西大同慈云寺万德法师那里所求,万德法师挥笔苍劲有力,墨迹连绵如峰峦峻岭,笔画纵横飘逸似龙飞凤翔,世间少有大家可与其相匹。然此时此刻,我心系爱女,内心焦急如焚,实无雅兴观摩字画。
我已年近五十,膝下独有一个爱女,二十有二,取名念晨,人见爱怜,都叫她晨晨。小女自幼聪明伶俐,受三代老人宠溺,自比寻常人家的孩子多一些骄纵蛮横的脾气。今日一早,这孩子便一如反常的早起离家,至此时未归。若是往日,多半懒床不起,时不过午,那是绝不会起床梳妆出户的。
我走出书房,疾步奔至阳台,只见大街上狂风骤起,领家阳台上晾晒的床单服饰随风蝶舞,霎时,天边电闪雷鸣,雷声低沉滚滚像山野狮吼,大雨倾盆而至,小区外马路上人影晃晃,车挤如潮。
我返回客厅,大声喊道:吴妈~吴妈~,吴妈,晨晨来电话没有?
厨房内吴妈放下手中家务,奔至客厅,用系在腰上的米色围裙揩拭着双手,对我说:董事长,晨晨一直没来过电话,我也给她打过好多次,都没人接。这孩子早饭没吃脸也没洗就急匆匆的出门了,董事长,这孩子不会是遇到什么难事了吧?
听到吴妈如是讲,我愤而坐入沙发,拿起摆在茶盘上的一盅茶昂首饮尽,继而将茶盅扔在地板上,吼道:繁勤呢?去哪儿了?把她给我叫回来?孩子丢了一整天,她个做妈的,连人影都不见。
吴妈慌张着忙不迭的将摔碎的茶盅残片捡起来,扔在纸筒里,边用抹布擦抹水迹边宽慰我说:董事长,消消气,我现在就给夫人打电话,叫她回来,晨晨这孩子虽是骄纵了些,但这孩子聪明伶俐,为人处世有礼有节,这孩子贪玩,想是跟同事朋友们一起去游玩聚餐了吧,不会有事的,您多放宽心。
我沉哼一声,气得连连气喘。只听吴妈这边已然接通繁勤的电话,只听她拿着话筒喊道:喂~喂~是夫人吗?我是吴妈呀,对,对,对,夫人啊,家里出事了,晨晨不见了,董事长要您赶紧回家一趟。
待吴妈挂断电话,我余气未消,问吴妈:她在哪儿?怎么说?什么时候回来?
吴妈唯唯诺诺的回道:董~董事长,夫人她说了,她~她马上就回来,我已经让阿进开车去接她了。
‘那,她现在在哪?一整天不见人影,是不是又出去约那些不正经的阔太太摸麻将去了?一个妇人家,既不工作,也不在家相夫教子,一整天一整天的在外面厮混,丢人现眼。’我越说越怒,说的面红耳赤,口干舌燥,拿起水盅,自斟自饮,一连喝了五六盅方止。
约莫二十分钟,天色渐黑,只听楼下门铃响起,吴妈惶急道:肯定是夫人回来了,董事长,我去开门。
吴妈急促的奔下楼梯,我随后跟至。门外繁勤推打着门心,吵嚷着:这么大个人了,怎么说丢就丢了?吴妈~吴妈~开门,快开门呢。
吴妈一路小跑,边跑边急喘着说:夫~夫人,我来,来了,这就给~给您开门。
我在楼梯口冲吴妈喊道:吴妈,您慢点,小心摔着。
只见吴妈打开门,繁勤鬓发黏湿成缕贴在额头,穿着一双男人的骆驼牌黑色皮鞋,衣衫均被雨水打湿,散乱不整。阿进赤裸着双脚,右手持伞左手拎着一双断根的高跟鞋跟在繁勤身后疾步入内。
看到繁勤这般狼狈污秽的模样,我心气更甚,我强行克制着冷哼一声:你瞧瞧你,成什么样子?像个当妈的吗?像个董事长夫人吗?衣衫不整,天天在外面厮混,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岁数了,还当自己风华月貌呢?在外面招三惹四,还要不要颜面了?女儿都是跟你学坏的。
繁勤高脚一甩,冲我横眉白眼,扬声怒喊:哟,董事长这是教训我呢?我在外面招三惹四,花天酒地,丢您老人家的脸了?瞧您,西装革履衣冠楚楚,歪瓜子头上顶这个董事长的帽子,狗戴礼帽装人装绅士啊?我呸~
我这边被她一句话噎的上气不接下气,自感在雇员面前丧失了尊严。只看她风风火火的闯进浴室,我本欲疾言以对,顿时想到晨晨安危,冲她喊道:你还有心情去洗澡,还不快跟我去找女儿。
她对我听而不闻,自顾洗起澡来,我气喘道:好好好,你作你的吧,我自己去找。女儿要是有个好歹,我跟你没玩,我跟你离婚。哼~阿进,开车,我们去找晨晨。
我转身看到阿进一身狼狈,气道:你怎么也弄成这个样子,瞧我这一家子,乱吧,就。
阿进怯怯的说:董事长,外面风大雨大,回来的路上,董事长夫人一不小心,踩在了裂开的路缝里,将鞋跟崴断了,所以,我就把我的鞋子脱给董事长夫人穿了,所以~就~
‘所以就现在这个样子了,是不是?’看见阿进冷的有些发抖,我转身对吴妈说:吴妈,去,到我衣帽间里给阿进拿身衣服来。
吴妈小声问我:拿哪件,董事长。
我不耐烦的说道:随便哪件都成,赶紧拿来给他换上。
吴妈连连称是,应声而去;我对阿进冷眼沉声地说道:还不快跟着去,赶紧换上,跟我一起去找晨晨,别再感冒了。
阿进连连摆手说:董事长,不用,不用,我没事的,咱这就去找晨晨吧。
我斥他说道:什么不用,快去换上,若是生病了,要我怎么好跟你爸妈交代?
待阿进换过衣服,我对吴妈交代:在我们未回来之前,全不要熄灯,都给我敞着。
我走出门口,只见天色已晚,雨势稍缓,只是寒风袭体,吹在脸上,犹如冰雪敷面。我陡然想到晨晨必是衣衫单薄,转而冲吴妈喊道:吴妈,去晨晨房间拿件外套来。
吴妈连连自责说:对对对,瞧我疏忽了,还是董事长心细啊,我这就去拿。
阿进说:董事长,您先进车,我去取。
我钻进车厢,阿进跑去,从吴妈手中接过一件裘皮大衣,我接过这件衣服,轻轻的抚摸着绒面,触感甚是柔滑光洁。我想起这件衣服还是去年晨晨生日,我在黄岛麦凯乐旗舰店为她买的一件生日礼物,此衣乃貂皮材质,皮大绒厚,皮色鲜艳,斑点清晰优美,绒毛短平油亮,价格实是不菲。我还记得晨晨在收到礼物时那欢天喜地的神情,还记得晨晨在烛光熙熙的蛋糕前,在她妈妈佯装嗔怒钦羡的目光下于我额头上那深深的一吻,吻印丝丝清凉如春泉晨露。我深深的陶醉在这温馨的回忆里,轻轻的揉搓着貂绒,就像爱抚着娇女柔顺的发丝一样,心暖如阳光普照。
我痴痴的回忆着过去,浑然不觉阿进在叫我。阿进一连喊了我几声,我才渐渐清醒,只听阿进问我:董事长,咱们转了好几条街了,还是不见晨晨,我们接下来该去哪儿?
我手拭着干涩的眼睛,对阿进说:打电话,试试能否打通。
阿进拿起手机一连拨了几次,都被挂断了。然后我把我的手机递给他说:用我的,快。
阿进答应着拨过去,接通了,却无人应答,只听电话里声音噪杂,杯瓶撞击声嘡啷不绝。阿进说:董事长,通了,不过没人说话。
我嚷道:给我。
我接过电话,大声喊道,像是带着嘶哑的哭声:宝贝,宝贝,我是爸爸呀?你在哪儿?说话呀?宝贝,别让爸爸担心,好吗?乖女儿,你快说话呀?
好久好久,电话那端传来一丝嘤咛,接着我听到手机坠地的声音,听见一个青年男子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过来:~漂亮哎~兄弟们,有福了,走起~走了,小妹,哥哥们疼你,来~。
接着,我听见酒杯坠地破碎的声音,听见青年男女打情骂俏的淫笑声时隐时没。我紧张的紧闭着声带,感受到一阵阵像是声带被撕裂一样的痛。我抽噎着喊阿进:阿,阿进,晨晨,晨晨她有危险了,有~有流氓,你听出那~那是什么~什么地方了吗?
阿进思索着说:董事长,是酒吧,对,肯定是酒吧。
我胡思乱想的猜测着:酒吧,对,对,是酒吧。
我强逼着自己必须冷静下来,此时,危机在即,我必须争分夺秒的及时找到晨晨,否则定要终生遗恨。我沉静的思索着,口中默默呢喃:酒吧,酒吧,晨晨还从未去过酒吧,可那分明就是酒吧,附近的酒吧没有几家?可时间短暂,危机迫在眉睫,也不能一一查看了,会是哪家酒吧呢?
陡然间,我想到几个月前,繁勤和她的那些麻将友在锦江路一家棋牌室耍牌,彻夜不归,我赌气也不去找她。直至次日凌晨,晨晨牵挂母亲,再央求我未果的情况下,找到阿进,求着阿进带着她用了整整一上午的时间,翻遍了整个黄岛城,搜遍了所有的酒吧、KTV、棋牌室等娱乐场所,终于在锦江路这家棋牌室找到她,好女儿连哭带劝的求她回家,她才答应。只是还非要去附近的一家酒吧喝酒尽兴才愿意回来。女儿依着她的性子,陪她一起来到这家名叫‘伊人醉酒’的酒吧。这家酒吧开业不久,但暗地里名声斐然,据说,老板路子很野,权交黑白两道,出手豪阔大方。我猛然想起阿进曾跟我提起过,说伊人醉酒开业,酒吧老板邀我前赴开业典礼,还送上一个厚厚的红包和几张面值两千元的利群金卡,我因不识此人,也不乐于和这等人结交,就让阿进辞退了礼品,谢绝参加。
我大声喊道:伊人醉酒,快去伊人醉酒。
阿进应声道:是。
我们用三五分钟的时间赶到这家店,只见店前门庭若市,停车位爆满拥挤,各样的名贵轿车可谓是琳琅满目。店前竖立着四个彩灯大字‘伊人醉酒’,字体潦草,像浓妆艳抹的歌妓一般眉飞色舞,此四字在霏雨中绮靡瑰丽,万种风情。我冲阿进喊道:阿进,别等我,快,你快进去找晨晨。
阿进快步疾飞的冲开店门,我随身跟到,只见在一张掀翻的酒桌旁,繁勤和女儿紧抱在一起,女儿已是神昏意迷泣不成声,繁勤搂抱着女儿的肩膀好生抚慰,脸上也是泪水横流。几步之外,阿进拳打脚踢的和几个年轻混混打在了一起。
阿进自幼习武,从小就像个太保一样在街面上鬼混,荒废学业,一事无成,他的父母也为此苦恼无策。后来,这孩子日渐长大,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脾性不改,一无所长,他的父母便四处张罗打听,托关系将他安排进我旗下的一家子公司出苦力,望他可以有个营生,有点长进。哪知他依然匪性不改,好吃懒做,迟到早退犹如日常便饭,很快便被公司辞退了。此后,这孩子更是无法无天的滚混,整日与一些浪荡懒散不学无术的人在一起打家劫舍混吃混喝。直到某日深夜,这孩子与一群狐友在网吧里通宵网游,凌晨走时拒绝付账,网店老板便叫了几个小混压场,阿进仗恃武艺强行出头,将一些人打得头破血流,更是有几个骨折指断,网店也被砸的一片狼藉。哪知网店老板也非善类,又叫了十多个身彪体肥的壮汉过来收场,阿进的那几个狐友眼见事态不好早就溜之大吉,只剩阿进一人孤身顽抗,最后被人制住关押起来。几日几夜不给吃喝,轮人看守,时不时的还被人拳打脚踢鞭打廷杖,到最后被救出来的时候已是遍体鳞伤不省人事。网店老板打听到阿进的住处,便派人到阿进家一番轰砸,临走时拿着阿进被打的衣衫褴褛的照片,威胁阿进父母说:你儿子打伤了我们兄弟,还砸了我们的店,限你三天之内,拿一百五十万来换你儿子,不许报警,到时敢少一分钱,你就给你儿子收尸吧。
阿进父母均是老实巴交的工人,一辈子也攒不足五十万,阿进母亲更是不曾见过这等架势,吓得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阿进爸手足无措,惶急中向老友陈继光求救,陈继光是我旗下一家分公司采购部经理,为人持重,他苦思无策后便拉着阿进爸找到我,阿进爸俯身跪求老泪纵横,我本不想沾染黑道之人,但念其可怜不幸,心中实是不忍,便出钱给阿进爸二百万,让其拿去赎人。后来,阿进爸带着阿进妈与阿进向我谢恩,又恳求我收留阿进为我做事,以作报答,我不忍拒绝,便答应将阿进留在身边做司机,打打杂。此后,这孩子对我感恩戴德,俯首是听。
阿进那边三拳两脚便将那几个小混混打的遍地哀嚎。我抢步过去扶起繁勤,从繁勤怀中抱过女儿,将貂皮大衣覆在她身上,紧紧地裹着。看着怀中的女儿面白如纸,浑身瑟瑟发抖,牙齿磕碰着嗒嗒作响,我的心痛如刀割。繁勤此时更是失声痛哭,刚换过的衣服又是撕烂成缕,俯在我身上捶胸顿足,抱怨着:死老头子,你怎么才来呀,你?要是再晚一会儿,你~你~我~我~我们娘俩就~就~就被这几个兔崽子给~给糟蹋了,就,呜呜呜~
我强定精神安抚着繁勤,将她的脸轻轻的俯靠在我的胸口上,连连说道:好了,好了,亲爱的,没事了,没事了。我稍稍整理了繁勤的衣裙,拢拢她松乱耷拉下来的头发说:走吧,宝贝,走,咱们回家,和咱女儿一起回家,啊~没事了啊,没事了。
我怀抱着女儿,阿进在旁开路,繁勤随在我身边从哀嚎在地的那些人身上一一绕过,正欲走出店门,却听到门外有一人在众人的围护下走过来,高声嚷道:是什么人?敢在我的店里闹事?我看,吃了雄心豹子胆。
阿进护在我身前,待那干人一进店,我便看到中间那位枯瘦如柴,形似枯槁,然双眼炯炯有神,下颌侧边有一道深深的疤痕,像是被利刃所留。
待他与我对视片刻,便见他形色立变,枯瘦的脸皮像波纹皱起,嬉笑着迎向我说:哟,费董事长,是您啊,幸会幸会,您屈尊光临小店,我钟某人真是三生有幸啊。
我颜色示意阿进,阿进附耳说道:董事长,他就是这家酒吧的老板,钟万发,道上人称‘黑夔’。
我平声静气的回道:哦,钟老板,您好,您好,在下就是费天翔,今日小女有恙,恕我不能施礼,请见谅。
只见他满脸讶异的询问道:费小姐这是怎么了?莫非喝多了?在下这里有解酒茶,费董事长若不嫌弃,可带费小姐里面请,酌饮两杯,为贵千金醒醒酒。
我致谢道:不必不必,钟老板客气了,今日小女在贵店喝酒,遇到几个流氓骚扰滋事,我的人就在贵店与他们打起来,不小心损坏了贵店的物品,实在是对不住,我留下我的人在这跟钟老板清理一下,然后理清损失,我他日定如数赔上,此时,小女身体抱恙,不宜耽搁,他日再请钟老板吃饭道歉。
钟万发连连摆手,说:哎,岂敢岂敢,不敢劳费董事长,既然费小姐身体不适,我就不便再留费董事长了。费董事长,就是地上的这几个小子吗?费董事长只管去,我来收拾他们。
只听他冲人群中喊道:彪子,来,叫弟兄们把这几个人给我扭到派出所去,给李所长打电话,就说这几个人在我们店寻衅滋事,要他看着给办了。
只见人群里一个肥头大耳虎背熊腰的光头汉子应声而去,我扭脸对阿进说:阿进,我先回去,你留下陪钟老板的弟兄们清理一下,列出损失清单,明日给我,如数赔给钟老板。
还未等阿进应声,钟老板抢先说道:哎,费董事长,您这就见外了,这区区小事,我钟某岂会看在眼里,改日,我钟某还要登门拜访,探望费小姐。
我回应道:岂敢岂敢,钟老板既然如此大义,那我们也就不再客套了,告辞,钟老板。阿进,代我向钟老板谢礼。
钟万发一干人送我们至店外。此时已风停雨歇,高高的夜空中乌云散坠。夜路上人烟已尽,四周一片沉寂,偶有几声蛙鸣从遥远的郊区野外传过来,零零散散。待我们赶回家中,已是深夜十点多,吴妈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打着瞌睡,我悄悄的叫醒她,要她赶紧去房间歇息。她却偏要熬一锅松茸参汤给繁勤晨晨阿进每人喝一些。待阿进吴妈繁勤均已睡下,我轻轻的来到晨晨房间,坐在女儿的床边,我亦止不住清泪涔涔而下。看着女儿熟睡的面容深埋在软绵的锦被里,我轻轻的抚摸着女儿洁白的额头,抚摸着女儿消瘦的面颊,轻轻揩拭着垂滴在她纤长的睫毛上的泪水,心有余悸。我于此时刻骨铭心的感受到妻子女儿之于我的人生是何等重要,亲情家庭之于我的余生是何等珍贵。我起身给女儿拽紧被脚,在我转身正欲离开的那一刻,我听到女儿在睡梦中哭喊着‘姒(si)源,姒源,别离开我,别离开我~’,我的心阵阵揪痛。我轻步走到窗前,看见阴残的月色拂过阴霾,看见冷月蓉蓉的从乌云里溢出,我感受到我的双眼暴露在凄寒的夜色里,一阵阵冰冷。我咬牙切齿的复念着女儿在梦中呼喊的那两个字‘姒源’,姒源,我要挖地三尺把你给找出来,将你千刀万剐,将你挫骨扬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