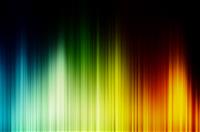某天,梦到自己坐在一列火车上。火车驶向哪里,我并不清楚,好像也不想搞清楚。因为它的方向是永远固定的,我的经验可以毫无疑问地预判这一点。所以,现在的我只不过倚在窗边,目光始终保持与玻璃的垂直,于是,窗外的景物不断从我眼前飘过。外面在下雨,这是我好久才注意到的。我的思维似乎还一直游离在另一个地方,它也恰似一列火车,要么晚点,要么永远都回不到始发站台。我回过神,原来,这里的灯光已经暗下去了;而那些当时跟我一起上车的人还全在那里,没有离开。我已经记不起他们原来是怎样进的车厢,是我跟着他们还是他们跟着我,抑或两者都不尽然。现在只见他们把半张脸埋在阴影里,对坐着,又微笑着,眼角的余光对着我,好像要我从中发现些什么。而他们所分享的谈话内容,虽然听得不甚分明,但却可以确定与我毫无关联。那或许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不过这样的场面确实非常吸引人,出于一种莫可言传的理由。他们对我来说无疑是陌生人,但他们共同的神态又让我感到是那样熟悉。于是,我作势要站起身来,舒展一下四肢,想以一种极合适的姿态朝他们走去,以探问一个究竟;然而,就在这一对我而言至关重要的时刻,一个低沉的嗓音,突然中止了计划要发生的一切。
我一时听不清这个声音说了什么,因为口音很重,而且我也实在辨不出这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也许快要绝种了的语言。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他——那人已像一尊纪念碑一样落到我的身前。我将目光一点点往上移动,像是要搜索什么诡异的东西;最后,停在了他脸上——原来这是一张黝黑方正的面孔。它正因为某种奇特的笑容而扭曲变形;他两腮的肌肉堆在颧骨下方,好似两个突出来的肉瘤。不过,他很快就把这副表情收回去了,代之以普通得近乎平庸的笑——就像车厢里对坐谈话的其他人那样。我困惑地看着他,可他也总是一如先前地看着我。他的眼神里——尽管他拼命掩饰——开始流露出某种难以名状的得意。而后,好像是他认为我通过了他的某项考验似的,他果决地打破缄默,那低沉却富有感召力的嗓音又开始活动了。他的眼睛突然变得炯炯有神,身体的其他部位甚至还加入了某些动作,乍看起来,夸张得近乎自负而且做作。然而,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在他简洁却又略显滑稽的讲演戛然而止的时刻,我竟也一下子全明白了他要我明白的意思,这是我先前根本不曾料到的。他要我马上去这列火车上的某节车厢,而等我到了那里,我自会明白我所要面对的使命。而且,尽管我可以确定他没有告诉我究竟是哪一节车厢,但我也竟能——也许是出于下意识地——了解了他的具体所指。不过,为了保险起见,我还是虚虚地向后摇了摇手。看到这个,他脸上掠过一丝惊疑,但很快又消散了,代之以激赏与宽慰的快意。他点点头,而后又稍稍停顿一下,补充了一通话语与动作,大意是说(我竟然又全听明白了),结束使命回来,我就能跟他一起,参与分享他的全部,就像旁边交谈的人们那样,笼罩在柔和的昏暗当中,永远都不会出来。这样的魅惑在不知不觉间钳住了我。我告诉自己,这应该是一种无上的光荣。至少,他选择了我,这便是我应该欣然接受的安排。于是,我默默向他表露了感激之情,便带着他的默许与怂恿,朝着那个似知未知的目的地飞快移动。
是的,我的确很快就到了那里,以至于路上发生了什么有些什么我都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这该是与火车运行方向相反的一个目标,而且显而易见,我的移动对于火车整体而言是那么的微不足道。当然,我并没有那样的野心,妄想身后紧跟一群从天而降的追随者;只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使我这仅有的一点发牢骚的权利也显得是那样不合时宜。因为赫然出现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一节空空如也的车厢,而此刻我的大脑竟也和这节车厢一样空白。我确信我没有收到任何使命,而且我也相信我没有被欺骗,因为我不可能被自己欺骗。我不禁有些惶恐了;也许,是我把什么重要的东西落在那个人那儿了吧,我也只能聊以自慰地这么想。可这至少是有可能的;所以事不宜迟,我要从原路返回。我这时才确信这路上只有自己一个人,路过的这些车厢跟刚才那节一样空无一物。然而,这归途却似乎在无限延伸;抑或我的双腿开始变得异常沉重,我的速度变得极其缓慢;我穿过一节又一节车厢,而一切都只是简单的重复,但又好像是永无休止一般。我感到自己已经掉进一个没有出口的隧道里面去了;终于,我全身麻木了,踉跄着,停住了一切徒劳的迈步,不自主地向前弓下身去,仿佛要向无尽的前方致敬似的;末了,缓缓地抬起头,却发现,那个人,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像从地底下穿出来一般,已经直挺挺地挡在了前面。
我不由得吓了一跳;可不想他也同样吃了一惊。我定了定神,看到现在那张黝黑的脸上已经浮上一层愁云,两瓣嘴唇无节奏地拉扯两边的肌肉,痉挛般地颤动;那两座颧骨也耸得出奇地高,仿佛就要从皮肤里滑出来一样。显然,他不但受了惊,而且更是气坏了。可他的眼睛却没有吐露半点愤懑的光芒,甚至也失掉了基本的神采,眼睑半遮半掩,于是越发显得是那样空洞。接着,他又开始像先前那样做起动作来了,只是不再优雅,不再矜持,背着一只手,另一只却攥成拳头,仿佛在夸耀自己的力量,似乎这才是他认为当前我最应该引起重视的东西。然后,他开口了,声调依旧低沉,然而话音却开始不由自主地颤抖。又一次,我听明白了:他以为我不应该出现在这里,或者,他不愿看到我出现在这里。我不由得向四下看看,没错,这儿是我返回的唯一路径;看来,还有不少至关重要的真相,亟待我向他一一禀明。听了我的申诉,他的身子像被狠狠电击了一下,而后便在惊恐中沉默了,仿佛心里在盘算着些什么。不过,像是从某个地方又收到了新的启示、获得了新的支持似的,仅仅一小会儿,他便由震恐的尴尬恢复了威严,甚至产生了更大的魄力,完全下了决心。于是,他舍弃了先前那一晦涩得令人头痛的、奇怪的古老方言,使用了我们谁都听得懂的现代语,只是卸去了所有冠冕堂皇的表演,利落得无以复加,口气则完全变成了诏令式的:你必须立刻离开这列火车,因为你丧失了你仅有的机会,你没有资格再见到我,而至于我这一方面,那就更不必徒费唇舌了。随即,他便转过身去,恰到好处地把脸孔完全移出我的视线——就这样,他果决地了结了一切,面对着唯一的一个我,俨然置身事外。
同样地,到了这个地步,萦绕在我脑际的一切惶惑,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因为我已聆听了判决,也多少领会了判决的精神。于是我迟疑了一会儿,便机械地迈开步子,向车门走去,然而那个人铁塔一样的身躯依然结结实实地挡在当口。我明白,以我一己之力,要推开他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至于他,也照旧侧着脸,高昂着头,两手抱胸,一动不动地矗立着,似乎只在看我的笑话,等待着我最后意料之中的选择。其实,我也明白自己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因为我很快就想到了,这里只有那些车窗好供我离开。于是我砸碎玻璃(当然,费了好大力气),把一条腿伸了出去。而就在我伸出另一条腿的刹那,我侧过头,用余光瞄了那个人一眼,柔和的阴影跟他的眼睑一起把他的上半张脸遮起来,同时,两瓣嘴唇轻松而满足地上下摩擦着,好像卸掉了所有包袱——但这些对我来说再没有任何意义。我只是感到自己已经不能支撑了,于是,脚掌向后轻轻一蹬,整个人就像空饮料瓶一样跌进了车轨旁边那片潮湿的矮树林中。
是的,我用自己仅剩的一点力气作了一些最后的确认:那列火车仍旧朝着那个方向行驶,似乎永远都不会转弯;而那节我原先置身其中的车厢,还有那节我曾经为之奔波往返的车厢,也很快从我面前驶过——两者的间距看来并不很大,但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去搞清楚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不过,不管怎样,毕竟我还是相对自由的,因为我至少还能够像刚才那样破窗而出;而在最后,这副躯体还可以永远融到外面这片略显阴湿的绿色里,或许也是我这个平凡的坠落者能得到的、唯一合理的一点恩赐与安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