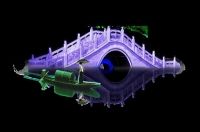作者/(河南)王自亮
一
老潘是山西人,在这里开了三十年的锁。老潘在这里,比当地人还当地人,除了那口音,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外地人了。老潘的摊子就在中心街路边,两辆三轮车,一辆装了一架配钥匙的小机床,车头上焊接的铁架子挂满了新锁,这些锁是售卖的,长年累月的晒,包装已经有些泛黄,积满了灰尘。三轮车两边的棚子上,红底白字刷了“配钥匙开锁”几个大字,下面就是老潘的电话号码,一个怕不够用,老潘把两个手机号都印上了。另一辆车是机动的,谁家钥匙丢了,或是落在了家里、门锁坏了,一个电话,老潘就骑了车赶过去。
不用担心哪个地方老潘不知道,这一片地方,哪个小区老潘都不知去了多少趟,可以说闭了眼就能摸到。其实按行规,修锁摊是大致都有势力范围的,虽然不像行政区划那样明确,可是,明火执杖的去人家地盘上抢生意,终归不好。但老潘很精,他在各小区物业那里都留了电话,并且讲明,只要是通过物业联系,开锁就便宜。这样既保证了客源,也照顾了同行——毕竟通过物业要光明正大很多。
时间长了,老潘在这熟的很,认识很多人。前门的老刘,后街的李七,书院街的阿三,还有对门的虎妮,大家都认识老潘。不管男人女人,没事都爱到老潘这坐坐,说几句,逗逗笑。有这里走出的人,想找找以前老街的记忆,人家就说,问老潘呀。老潘就会告诉他,二十年前这街什么样子,这里有株槐树,甚至旁边还有个大苇坑,而现在呢,都没有了,现在都是楼,密密的净是人。老潘还常常感叹,说以前这道街多热闹,天天车水马龙,特别是逢了会。现在,老潘头摇得拨浪鼓一样,“现在留不住人了!单行道,开不好就要罚款。”
熟识老潘的人都不叫老潘叫老潘,叫二狗。老潘行二,至于为什么叫二狗?农村人都知道,命贱呗!在乡下,特别是苦焦的地方,农民是怕金贵的,他们总觉得,越是金贵越被天妒,越会命运多舛,因此这些人家,生了娃总是拼命往贱里叫,什么屎蛋、狗啃、黑妮、柴火、三猪,越贱越好。在他们印象里,牲畜是贱的,因此起猪狗的名字,肯定鬼神见了也讨嫌,也不会搭理你。不搭理你不找事,这孩子不就无病无灾长起来了吗?
事实上还真是这样,老潘说他弟兄几个,长到十六七,还不知道针管是啥样,感冒发烧很少,即使有了,也是熬一锅葱根姜片水就过来了。哪像现在孩子,天天感冒。老潘没事了跟人聊,一扯就扯到这个话题。
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老潘租住的小房(一间没有窗子的大门旁边的小黑屋)房东的孙女天天发烧,一发烧就要住院。一家几个大人忙得手忙脚乱,看不住一个孩子。
二
前几年,老潘收了不少徒弟,可这些徒弟学时都挺好,尊重师傅,什么有我一碗就有师傅半碗,可是,一旦学成,翅膀硬了,不但没有师傅的饭,还恨不得抢走师傅的饭碗。他们在这城市和四郊开店设摊,逼得老潘的地盘越来越小。有一个徒弟叫青牛的,还特别有生意头脑,不光开锁配钥匙,还擦皮鞋、搞皮革保养,几年下来,连锁店好几个,穿金戴银,女朋友就像衣服一样换。老潘有次开锁见过他,胳膊上纹了一条青龙,一身花格子衫,架着一个女孩子飘然而过,他已经认不出老潘了。
老潘就下决心不再收徒弟,想再等一两年,把自家小潘带过来。小潘是老潘的大儿子。关于老潘的家,很少听老潘提起。只说是山西一个县,很穷,属于山区,地不成庄稼,成苹果。老潘家那一口,就在家里种苹果,老潘说我们苹果好吃,可脆可甜。他说话声音极短,甜字一吐就戛然而止,总让人觉得有那半截甜被他吞到了肚里。
其实除了身材矮点,腿有点罗锅(这是以前山地人的通病),老潘其实长得很帅,四方脸,浓眉,大眼睛,短头发密密的,像一顶小帽。鼻子有点肉,两颊的肌肉很发达,一说话线条分明,显得很有男人味。没事的时候,他就爱用腕上的镯子,在头皮上摩弄,或是靠在阳光下闭目养神,那样子,像一尊青面佛。
老潘人老实,技术精,而且要价合理。因此,生意很好。老潘经常很忙,常常摊位前钥匙配不完,那边又接了电话,要去开锁。老潘就要换钥匙的等一等,对于老潘来说,开锁是大活。
这要技术,老潘开锁开的又快又利索。不像有的人,开不好,就把锁匙弄坏了。或是一扇门,二三十分钟还弄不开,业主急,他也急,越急越乱套。不管再复杂的门锁,老潘三五分钟就能鼓捣开。看老潘开锁简直是一种享受,那么粗壮的手,却又那么灵巧,捏了细细的铁丝,只那么几拨几挑,门就啪嗒一声开了。整个过程行云流水,老潘气定神闲,粗气也不喘一口。这世上一切技艺都是相通的,最高的境界,技术就是艺术。
老潘最喜欢人家和他谈锁。和老潘谈起锁,老潘就来了劲。不管是十字的、斜纹的、暗格的,还有密码锁、指纹锁,都能开。只不过有的简单,有的稍费点功夫而已。“这世上哪有打不开的锁呢!”老潘一面配钥匙一面说,这一句话,修锁匠老潘足以让很多哲学家羞惭。
老潘平常很逍遥,没事了,就爱哼山西情歌。《亲圪蛋下河洗衣裳》《走西口》张口即来,有时哼的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歌。
“满天的星星一颗颗明,
天底下挑准你一个人。
马里头挑马不一般高,
人里头挑人数哥哥好。
黄河边上的灵芝草,
谁也比不上妹妹好。
大树小树千万棵,
挑来挑去数哥哥。
麻雀子落在圪针上,
一心心操在你身上。
凉水热水温温水,
心里头有谁就是谁。
——”
他声音很哑,但很好听,沙沙的,再加上那种山西味,就特别耐听。
他一唱,房东大嫂就爱跟他打趣。
“二狗,又想媳妇了?”
老潘嘿嘿一笑。
“嫂给你在这找个吧?真的呀。攒那么多钱干啥,给谁花?”
老潘就挠挠头,“家有了么!”
老潘很节俭,不打牌,不吸烟,唯一爱好就是哼哼歌,打打手机游戏。白天在街上摆摊,晚上就旁边小巷的出租屋里住。他自己做饭,馒头咸菜对付,就是头发都是自己理。老潘说那一次,他去一个理发店,剪了头,竟然要十元。“出来,我就去买了一副推子。娘娘的,以后别想再挣我一分钱。”
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老潘是怎么过的。
三
老潘怎么过?老潘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其实,老潘很多时间也睡不着,他就喝酒。老潘床下就有酒。那是在散酒铺里塑料壶灌的,二元一斤,很便宜。老潘咕嘟嘟喝几口,看似压下了火,其实,老潘没想过,酒不能灭火,还能催火。但火焰腾腾起来时,老潘已经睡着了。实在不行,还有手。时下常有时尚青年说,右手姑娘么。
其实,老潘也不是没有机会。
老潘租房的那家嫂子,就对老潘颇有好感。平时孙女生病发烧,儿子儿媳都住了院,女人就在家里做饭送饭。她男人在外面跑车,常常遇了活,十天半月不回家。平常家里有了重活,比如倒垃圾桶了,扫地了,搬桌椅了,收拾线路,换灯泡了,或是家里的电机、洗衣机坏了,这些都难不倒老潘。老潘勤快,眼里有活,又能干,总是三五下就鼓捣好了。
女人在一边,就常常带了一种柔柔的眼光看。那眼神,老潘不敢看,那眼神里有水。让人陷进去就拔不出来。
有一天夜里下了雨,女人从医院出来,正愁着怎样回去。老潘却骑三轮在旁边等了。
女人感激,到了家,老潘帮女人收拾好院子,关了门就睡。一会儿,女人敲老潘门,给老潘送了一个瓜。
“潘哥,你尝尝,这瓜可甜。”女人不叫老潘二狗了。
老潘说睡了,不吃了。
女人脸红红的,往老潘屋里钻,你看这屋乱的,我给你整整。
女人不好看,但也不难看。平时不怎么讲究的她,还梳了头发,脸庞红红的,眼睛像星星一样。
老潘说别,我睡了。
女人不甘心,说你平常唱歌可好听,这几天咋不听你唱了。你唱几句呗,就唱那什么阿妹泪花花落——
老潘说,谢谢嫂子,我睡了,明天就给你唱。
女人推门的身子缩回去了。老潘听到了一声轻轻叹气,那叹气如响雷。
老潘也在叹气。
老潘知道自己的底线,老潘有一把心锁。他知道一个异乡人处世,必须守好这把锁。
女人对老潘冷了很多,还常常指桑骂槐的抱怨。老潘不听,见了女人总是低了头就走。
四
其实,老潘的心锁不是没有打开过,那是唯一的一次。
那天晚上,老潘要睡了,他接了电话,到老城根小区开锁。
开锁的是一个白净的女人,钥匙丢在了屋里。
锁打开了,那女人却倒了水,非要老潘去喝点水。
“潘师傅。”女人很白,眉宇间藏着一股忧色。老潘摆摆手,就要走。
“那你也要洗洗手啊。”女人说。
女人很憔悴,有五十来岁年纪,后来老潘才知道,女人正在与丈夫闹离婚。丈夫在外面花了心,被女人发现了。过几天,女人的钥匙又落在了屋里,要老潘去开锁。
老潘自己都不好意思了,说钥匙怎么一个劲丢,这样不行。
这样吧,老潘想了个办法,你拿一把钥匙,就装在身上,或是放在朋友亲戚家。这样,就好多了。末了要钱,老潘只收二十元,老潘原本不要的,还是女人非要给。这可是第一次,老潘从来没有收这么少。五十元,不还价,这是铁价。
女人就隔三岔五来找老潘了,还请老潘吃饭。
晚上下了班,老潘正准备回去了,女人却真的来了,开着一辆车。
“潘师傅,你人真好,嫂子呢。”
“她在家里么,还有地。”
“在家里你放心?”女人笑着。
老潘说,“哎,有啥不放心。老夫老妻了。”
“你是好人,你这样的人真少找。”妇人咯咯笑着,一会幽叹着,或许触动了伤心事,又嘤嘤哭泣起来。
这一哭,老潘倒不知所措了,他平常刚硬惯了,就见不得人哭。
“潘哥,咱俩喝点吧。”
“不,不。”老潘要走,女人拉了他,“潘哥。”
老潘铁打的人也化了。
那一夜,老潘没有走。
这一次,老潘的心锁开了。后来,女人又找老潘,女人离了婚,要老潘跟她走,老潘没答应。从此,那女人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老潘把这事和那个女人深深的锁在心里,又加了一把锁。可是,实在睡不着的时候,他面前还会浮现出女人那张脸,浮肿的、苍白的、巅狂的,还有床上那么多令老潘都脸红的花样。老潘竟然发现他有点后悔了。他不但一点没忘那女人,还想那女人。
她在哪呢,还好吗?
五
就在秋收之后,小潘来了。小潘与他爹完全不同,小潘高高大大,而且四方脸,比他爹更英俊。
小潘才两个月,就学会了他爹的全部手艺。他有老潘的那种灵性和钻劲,又有老潘没有的胆魄。小潘一来就对他爹站街的行为表示了强烈不满,毕竟,以前可以,现在这城市开始文明城市改造,对路边摊进行清理,虽然有时候城管碍于面子,对老潘不说什么,但总不是长期的营生。
小潘把街中间一间原来麻辣鸭脖的门脸租下来,挂上了开锁配钥匙的牌子。而且不再像老潘一样,只是在纸牌上随便写几个字,而是用正经的广告公司制作的门牌。
“这还要到城管上备案,要二三千呢。”老潘说。
“二三千就两三千,这钱要花,多少也得花。”小潘说。
话语里满是责备,老潘听出来了,意思是说他,你这些年弄不大,为了什么,就是因为胆太小。
小潘不但开了店,还注册了店名,就是潘师傅。设计了卡通形象,老潘的大头卡通像,手里拿一把钥匙。你别说,还很像。
因为有老潘镇着,生意越来越红火。活少时,开始是老潘带了小潘去开锁,后来就是老潘看了店,小潘去跑。活多时,两个人都分别去。但这样的时候很少。
老潘发现,小潘在店里时间越来越少。
才两个月,小潘就嫌老潘住的地方太小,住不下,他自己,就在店里备了铺盖了。
小潘爱听歌,爱交友,爱吃喝。
很快,老潘就发现,店里面满是烟蒂酒气。
老潘说小潘,可小潘说忙一天了,不歇一歇,玩一玩?其他不要老潘管。
店里面有了淡淡的脂粉气。有一次,还从床下发现了避孕套。
老潘觉得不能再容忍了。他觉得要跟小潘严肃谈一谈了。
“那人是谁。”
“谁?”
“还装糊涂。”
“一个朋友。”
“啥朋友,交朋友也不给我说一声。你问清人家情况了么?”
“这?现在都是这。”小潘有点不屑。
“儿呀,这不是家。咱这是在外面,咱没有担待,听我话,不要再跟那女人来往了。”
这女人,是小潘修锁时认识的女子。这是一个富婆,因为空虚,而喜欢上了小潘的英俊强壮。两个人各取所需,自然一拍即合。
小潘不但生活混乱,还破了行业规矩,不再像老潘一样谨慎,偷偷摸摸去做外小区的活,而是明目张胆,甚至城西天远城的活都接了。这是明显的破了行业规矩。虽然有人提醒,但小潘不管,“都是市场经济吗?公平竞争,谁想做谁做,人家想叫谁做叫谁做。”小潘说。
六
没几天,几个人气汹汹来了,要找小潘。小潘躲在屋里不敢出来。几人嚷一阵,把修锁摊子砸了。老潘不吱声,站在一边看那些人砸。几人泄了气,扬长而去。
“你想怎么办?”
“爹,咱走吧。”
“去哪?”
“去家。”
“去家干什么,啃黑馍?你那出息,走什么,哪也不走。”老潘忽然异常坚定,腮帮下的肌肉一突一突的。
“一顿打就吓趴了?孩子,咱是手艺人,开锁匠,咱是给人家开锁的,但啥时候,都要先锁好自己的心锁。”
老潘看着羞愧的儿子,忽然脸有点红。那女人的模样又飘出来,像一团软绵绵的云。
他看了一眼外面,晴亮的阳光下,那草坪上的红花,竟然开成了彩色,弥漫着绚烂的光泽,一切都是那么美。几个花花绿绿的女人说笑着,梦一样飘过。
老潘忽然有点迷惑,不知道是自己错了,还是儿子错了。或者他们都错了,可什么才是正确的呢?
老潘不知道,或是知道了,也没法说。
(作者现供职于河南省长垣县委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