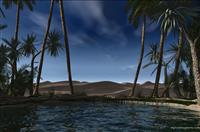听母亲说,父亲从宝鸡调到绵阳三十八队工作时,每月一次探亲时家里打牙祭,而父亲调回致民路省客后,一个月和母亲我会四次光顾杀猪房。每次两斤肉票两元钱(肉价0.75元)。每到父亲休息半天的前夜我便一个通宵辗转反侧,天不见亮浑浑噩噩随母亲飞奔过去排班站队,一眨不眨严防死守。不言而喻,橱窗口倘若多了个嘀嘀咕咕长袖善舞的他,有限的猪肉份额里就一定会少上一个一板一眼蹈矩循彟替死鬼的你,有钱有票也一定买不来猪肉!多了这一餐餐让人扬眉吐气大快朵颐的牙祭,却从此再也就没有了百年洋槐树下那间我呱呱坠地风雨飘摇上漏下湿的油毛毡棚,再也就没有了那一个个风雨交加的雷电夜把惊魂未定的我从父亲肩膀接入温暖被窝历历在目的叔叔婶婶,再也就没有了父亲染着风尘大包小包的板栗、冰糖、核桃、花生、骨肉至亲血浓于水的思念、和牵挂,再也就没有了那位丢盔卸甲尚挂着鼻涕眼泪又卷土杀来的手下败将隔壁邻居姚二娃。唉,命运啊,你让人该如何是好。压根儿我就没指望鱼和熊掌,只不过熬锅肉、板栗和冰糖。
杀猪房,六十年代初落成,位于巷子上街尽头的左边,下街方向的起点,正对右边公厕、张伯住家,两者之间矗立着一根水泥高压电杆,电杆上悬挂着整个巷弄唯一一盏低功率白炽灯泡。杀猪房,火砖、小青瓦结构,青石板地面,分为前后两个部分,以木门互通,成直角尺相交,面积三百平米。前排,杀房带橱窗,后排,收购点带临时饲养场。临时饲养场为火砖圆木铁栅栏开放式结构,可以临时存放二十头肥猪,紧挨着打煤场大门,距离房管局、哑巴堰分别五十、一百米路程。大灶台火口、正门、长方形橱窗面向巷弄。橱窗长五米、高一米五,距离地面一米,半装铺板。油腻、血腥、肮脏。从窗口望进去,里面密密麻麻吊挂着猪扇,随人的走动猪扇群起群落大大小小的苍蝇,光滑的青石板上流淌、囤积着猪扇落下和自来水冲洗后浅红的血水。全副武装的水胶衣叼上香烟风风火火说说笑笑,渣渣渣渣的步伐中尽情挥霍着内部特供的幽默、笑靥和有色桥段。而一旦面对了伏低做小的各路草民,他们瞬间嬗变为登峰造极如假包换的变脸大师。可以肯定的是,这条巷弄没有单独命名,依然隶属于沙河堡的直接序列。我也丝毫未曾留意过它曾经门牌的标注,只记得巷里巷外的人家无论老少都亲切地称呼这条巷子,杀猪房。
杀猪房,对沙河堡方圆好几个生产队的纯农村户口人家而言就是阎罗殿。不管你卖还是买,也不管你见还是见逑不得,情不情愿终究你还是得拜倒在它的石榴裙下。不管你***觉得自己有好了不起!一百八九十斤,小标准,它总也算是标准,最起码可以挣回来32.5斤入场券。莫不再拖回家喂一年,看是你想它的大标准还是它定让你颗粒无收。一斤肉票七毛五一斤!聊尔不提同靠天吃饭挣工分如出一辙获得入场资格的若何艰辛,聊尔也不提胜利在望孤注一掷一气呵成后毛猪价值能否结清负债小有盈余,七毛五就当时中等水平的生产队而言,一个全劳力三天以上的工分日值。对三月不知肉味四五、七八口子一家的多数人家说来,只是一个娃娃,怎么也得斤把五花肉解馋吧?不可能年多月久开一次荤,还不许人幸福的打上半个饱嗝吧?让人除了瘟猪肉一年三百六十四天身上不带一点肉香如何在三家村小学堂给一惯穷追猛打宝宝霜们一个了断了好奇的满意答卷?象这样多子女入不敷出的人家,各个生产队占八成以上。一靠生产队分配的瘟猪开戒,二靠孩子们雨天戳鱼,晚上四处照黄鳝,甚至偷狗杀。我苦命的骨瘦如柴的压细压乡坝头最善解人意的一辈子只见过簸箕大个杀猪房的孩子啊,要不就送进寺庙杵上戒疤赐予法号素贞而索性就了绝了红尘诸多不切实际的欲望转而长素了吧。阿门!饶恕了吧,他只管造不管养荷尔蒙泛滥罪孽深重的老头子!马路边核武器家(又叫白兔)人手三片次的牙祭生产队尽人皆知;房管局李显明一年一次半斤八两牙祭的困顿无人可及;夏二哥你可不可以先把铁锅偌大的漏洞补齐了再给我摆红烧狗肉等同于某年某月某一天蓝标猪肉的色香味全;原子弹(黑武器的哥哥)你能不能不要这个样子寡逆,等人生吞活剥了下去,才吞吞吐吐咨询,“诶,老三,耗子肉是不是和腊肉一样的好吃?”。唉,我可怜的连耗子肉也绝不放过的亚细亚孩子的见不得丁点儿荤腥而一发不可收拾的素嘴!
杀猪房就是沙河堡的太上皇!盘踞着食言而肥翻云覆雨九五之尊。有没得道理都别去招惹里面的防水衣,除非一辈子不喂猪,除非喂的猪不拉屎,除非拉的真的是猪屎,除非安了心这辈子情有独钟的只是小标准。人心是杆秤,十秤九不一,豁皮,听过没?杀猪房的小标准除了蔑条笆子、猪屎巴巴、死吃烂涨、猪毛头发、如此等等只荴到个位数,那是红芙蓉使起秋的结果!嗨!再咋个不服气,最起码经他七扣八除下来还算生猪,而不是蜘蛛!杀猪房的猪血两毛钱一脚盆,那是心花怒放时的计量。杀猪房的猪下水、脚油、板油是人都可以啖,就看在他的瞳孔中印出的你是不是人。老子再给你说一声,杀猪房收的是猪,不是造粪机!你***,牵了头非洲大象过来吃诈钱嗦!180在老子这儿就是小标准!你敢赌咒你没有灌?你敢赌咒你出门前没有喂?他妈大起个血吸虫肚子屁眼上血流血滴走路都偏偏倒倒打酒饱嗝你给老子好生解释一下哩。
从杀猪房折回,第一家是沙河堡国营理发店老派高级技工朱师傅。我所目知眼见的朱师傅对于他业界无可匹敌的造诣而言,已经到了点石成金鬼斧神工的境界。尽管如此,却牢牢把守着他职业操守的底线,你脑壳上蠕动的怎么可能会是虱子呢?头发,头发,呵呵。他手里飞龙舞凤的剃须刀宛如绣娘手里运斤成风翾风回雪的绣花针。他的职业已经融入并贯穿于他生活的始终,除了睡觉,一年四季职业象征的白披风、搪瓷盅、剃须刀、接尖鞋。如对门的谢家、起义,安分守己的朱师傅也冲动了一回,把厨房搬上了街沿。四十出头的他,中等个头,性格开朗。以他炉火纯青的技艺掌控着沙河堡地区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豆渣、弹子盘、猪脑壳,以两毛五几毛的天价引无数沙派豁皮竞折腰。也才让卢老六之流走街串巷见钱眼开的机会主义有了有机可乘死灰复燃的土壤。而发型千篇一律,学生头、平头、撇三、中分、光头。请注意,一边是资本主义投机倒把见钱眼开自绝于人民的剃头匠,而另一边是德才兼备冰壶玉衡为人民服务的理发师!一边不同流俗,一边沾满铜臭!一方高山景行,一方不堪入目!可悲的是,不知丁董的我竟然被卢老六的搞头蒙蔽了双眼!不排班,还相因一角钱。起初我并不知道,朱师傅与生产队压强的母亲沾亲,路过他家门我见过一次朱孃正在堂屋放下夹背倒出红苕。退休后朱师傅把堂屋改作了门脸,用余热延续了他曾经热衷于的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巷子里来来去去谈笑风生的朱师傅依然如故,白披风,搪瓷盅,剃须刀,黑皮鞋。“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
朱家的下家,街面只是一扇单扇木门,正房在里面深处向右展开,是集天地精华(披星戴月、栉风沐雨)为一体,三家村土地上最勤劳最朴素最广大劳动人民的代表之一,杀猪房巷弄三架马车豁皮之一的艾家。同朱师傅一般,积重难返,根深蒂固,即使几十年后转为居民户口,她依然无怨无悔热爱着她曾经典身卖命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社员、干部、镰刀、尿桶、锄头、瘟猪。而且每每在小区遇上,总是会拉住母亲一次又一次满怀感慨老生常谈起五十年前母亲带上她们几位年青女社员进城杀大馆子的历历往事!鹤唳华亭行思坐忆,感今怀昔泪沾衣襟!艾家六口人,性情温和的男主人老艾是供销社正式职工,爱人李孃花果一队社员,老大、老二在生产队挣工分,老三我小学、中学低一年级学友,艾四则要小我好几岁。过了艾家,是打煤场高高的后墙。墙下,巷弄几户人家老年人在那片空地上盆栽了指甲花、葱葱、白菜、丝瓜。打煤场改成为电动打煤机后,轰鸣的噪音严重影响到周围居民的正常生活,更为严重的是,它随风扬起的粉层波及到整条巷弄的四面八方,里面出来的无论男女和非洲君区别不大,除了滴溜溜乱转的眼珠,被揩成两条的鼻线,高高扬起的乌鸦脖子,整个一煤球!
2017仲夏,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