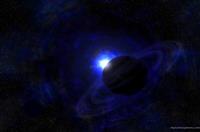每逢回到老屋,眼光无论如何也不敢投向那个角落——堂屋的一隅,偶而的掠过,也犹如在揭伤口上那层沾染血迹的纱布,那种痛让人无法忍受。那个角落是父亲离开人世间最后三个月所呆的地方,那三个月,父亲已基本不能行走,但他坚持要从里屋搬了出来,为此还跟母亲吵了一架。堂屋临街,小巷里的小孩,车子随意穿梭,闹腾得很,根本就无法休息,无论怎样,父亲都不肯改变主意,而且坚持坐着,叫我们不解了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他的日子不会很多,也就随着他了。
那个角落平时也是属于父亲的,那个位置是传统的上位,吃饭父亲坐那,喝茶父亲坐那,有时父亲的朋友来串个门,聊个天,打个牌,父亲也爱坐那个地方。父亲坐在上位吃饭,菜上桌时父亲的头每次都会扭向一边,这时,除了大一点的姐,余下的我们仨都会飞快的挟菜埋入饭中,然后象什么也没发生的样子细细的吃着剩下的菜。这时的父亲脸上会有一丝的笑容,在我的记忆中,只能搜寻到父亲这时一瞬的笑容了。
角落里放着床,堂屋的空间小了很多,大家的活动,基本上都在父亲的视野也内,那时,除了小弟,我们姐妹几个均已成家,各自的孩子尚小,他们只有在外公的床第间玩耍,这时的父亲有时便会叫着他们的小名,然后从口袋中找掏出大白兔奶糖,剥开纸放入他们的口中,所以,只要父亲醒着,那些小家伙无论谁也不肯到街上去玩的。由于父亲生着病,我们的心也一直压抑着,只有那么一天,小弟考上这警察,在那种边缘地带的小街上,警察很是一份带有理想色彩的职业,中午,家人全到达齐了,小弟穿上了警服,就要去警校报到,我以为父亲会说些嘱咐的话,但是没有,父亲只是帮弟拉了拉衣角,一脸的凝重。
父亲是大年初五走的,那是十年前的春天,那天正好立春。在立春的爆竹声中,父亲安祥的闭上了眼睛。办完父亲的事的时候,我的心一直麻木着,直到回到老屋,望着那空荡荡的角落,心一下象那个角落一样空了,我知道:我已经永远的失去了父亲!
今天,我们几个又回到了老屋,那个一直空着的角落放着父亲亲手做的竹椅,母亲坐在那里,见我们来了,母亲忙乎着做饭,我坐到了带有母亲余温的竹椅上,看着穿梭于堂屋的母亲的身影,终于明白了父亲的坚持,渐渐的,我的周围弥漫着父亲的气息,我仿佛回到了童年:父亲坐在门前的泡桐树下,我坐在父亲的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