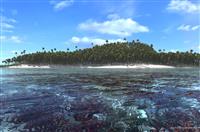
记得我小的时候,母亲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是中等身材,经常穿的一身破旧的青色粗布线衣,上面打着许多补丁,但非常整洁而合体。外婆习惯于将自己半白稀疏的头发盘在脑后,外婆的面色黑红但很慈善,她的一双勤劳的手也让人感觉干裂而温暖。
母亲是外婆的小女,也是三个姊妹中离外婆家最近女儿,相隔有十里多路。父亲在外地农场打工,家里只剩母亲和我,所以外婆常到我家里来。
我与外婆的关系极好,这大概是外婆对我的疼爱所致吧。外婆隔几日不来,母亲便开始念念叨叨,那个时候我还小,虽然不太明白母亲的的话,但也会绊着小腿儿“跑”到外面向外婆家的方向看,有时还真的迎到了外婆,外婆总是笑着用双手将我举过头顶亲呢一番,随后我便搂着外婆的脖儿,脸儿贴着外婆的脸,外婆便笑着逗着我说:“想外婆了吗?”“想了!”“哪想了?”“这儿!”我便用小手指着自己的肚呱呱给外婆看,外婆开心地笑着,有时笑出了泪儿。
外婆每次见到母亲后,都喋喋不休地夸赞我又长出息了,不像刚出生那阵儿,瘦小的可怜,吓得母亲时刻也不敢离开,外婆也整日整夜地陪着担心,现在总算离手了,母亲一边干着手里的活儿一边应和着。
外婆每次到我家里来,都总不闲着,像是特意来为母亲帮忙做家务的,什么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烧火做饭,省出母亲大部分时间照顾我和做其他的事。母亲因为有了我而不能下生产队干活,父亲在外地打工也只是填饱自己的肚子,没有多少结余,所以母亲经常用高梁桔的皮编织成草帽、炕席、米囤子等到集市上去卖,换点儿钱养家糊口。外婆也一边哄着我,一边给母亲打帮手,外婆虽然上了点年纪,但干起活来一点儿也不比母亲差。
一次,外婆由于过度疲劳病倒了,而当地又没有医院,母亲便请来了当地的私先生为她治病,外婆硬是不肯,说什么年岁大了,生病长灾儿是正常的,母亲好说歹说,外婆才吃了药,并一再埋怨母亲说:“过两天我就好了,还花这份儿钱干嘛?”我似懂非懂外婆的话。外婆的刚强却激发着母亲,使母亲更加勤奋得过日子。
就这样,外婆为母亲打帮手几日,就得回去看看,忙忙自己家的活儿再来,时间久了,我便把外婆当成自己家的一员了,每当外婆走时,我总要挡在门口哭着不让外婆走,外婆便学着偷儿着走。
后来我多少长大了,母亲便将我完全托付给外婆,从此我便在外婆家与外婆形影不离。外婆年岁大了,不能下地干活,她接管着家里的一切杂活,白日磨面、做饭、上山挖野菜,喂猪、喂鸡、做饭等,晩上还在煤油灯下给家里人做鞋,缝补衣服,整日从早到晚忙忙碌碌,几乎直不起身子,但她从不说声累,总是任劳任怨。外婆家的人口多,爷孙几代人生活在一起,外婆总有操不完的心。到了晚上,外婆安顿这个,又嘱咐那个,等到其他人都睡了,外婆才能静下来。我从来都不知道外婆是什么时候将我搂进她的被窝的,也从来不知道外婆早上是什么时候起来的,反正我一睁眼的时候,总是看见外婆忙不颠地走过来为我穿衣服,洗脸、梳小辫,然后端上热腾腾的玉米馍给我吃,我香香的吃着,外婆脸上挂着笑。
时间久了,外婆怕我想妈妈,总要背着我回家看看,来来回回数不清有多少次,母亲见外婆年岁大了,走路都不方便了,就劝外婆不要来回受累了,外婆却很随意地说“你放心孩子,我还不放心呢!”这话虽然是唠叨话,如今仔细琢磨起来,才感觉到外婆不仅仅是疼爱我,而且还悬挂着一颗惦念母亲的母爱之心。
外婆每次走时,母亲也一再嘱咐:“妈,您别再来了,大老远的,过些天还是我回去吧!”外婆总是用背晃着我说:“不用,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来回多溜达溜达,身子骨儿更结实,再说你还得下队干活,想法多挣点工分不是?”
事实也是这样,母亲还真的没时间来外婆家,外婆照旧挤出自己的时间送我。夏季,遇上刮风下雨,外婆总要用她那渐渐瘦弱的身体遮住我;冬季,外婆总要把我的一双小脚放进她的裤腰儿里,然后用棉衣大襟儿将我的身子裹住,暖呼呼的,一点也不冷。
再后来,我长大了些,自己能走远路了,外婆也实在背不动我了,每次带我回家就领着我,我蹦蹦跳跳地拉着外婆干瘪的手,外婆的肩上还要带上一些领我上山挖的野菜。外婆说,母亲一个人在家又下队干活,又操持家务,没时间上山挖野菜,别看这些野菜不是啥金贵东西,乡村里过日子还真用得着呢!的确,那时家里很穷,喂猪喂鸡得全靠这些“山里特产”,所以母亲见了外婆带去的野菜,就像得了宝贝似的,把其中嫩的拣出来,上锅煮了,再放进面糊糊里搅拌,蒸菜馍馍吃。
到了我该上学的年龄,母亲便把我从外婆家接了回去,我为离开外婆哭了好几场。但每到星期日,我便急着去外婆家,当然路也熟了,来回都容易。外婆见了我,笑不合嘴儿,问这问那儿,总有说不完的话,冷不?热不?渴不?饿不?还有上学好不好?学习好不好?我依偎在外婆的怀里一一作答。
后来,我上了初中,成了住宿生,只有寒暑假才能到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也许是我和外婆见面的时间相隔太久,我发现外婆的变化相当明显,身体由健壮到瘦弱,头发由半白到全白,牙齿也满口脱落了,但外婆仍就拄着拐杖,捣着小脚在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我劝外婆年岁大了该享享清福了,现在搞了生产责任制,家里条件好了,就别再操劳了。外婆却说:“闲不住了,这把老骨头干点活比闲着舒服”。为这儿事,舅妈儿常常与外婆意见不统一,但最终还是外婆站了主角儿。
外婆经常对我说,“你们这代年轻人,摊上好时候了,要好好学习,别不争气,我们那时想上学都没地儿去,有私塾又上不起。”我记住了外婆的话,在学校倍加努力,后来我真的考上了学,街坊邻居无不羡慕。临开学时,我又特意去了外婆家一次,这一天,外婆似乎年轻了许多,她有说有笑,用双手攥着我从小被她攥大的手,仔细的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说:“嗯!我女儿总算有你这么一个长出息的女儿了!”“外婆!”我倒在外婆的肩上,像孩儿提时一样亲亲外婆的脸,我知道今天的一切与外婆慈母般的爱是分不开的,外婆那饱经风霜的脸绽着幸福的微笑。那次我离开外婆家吃的最后一顿饭就是外婆亲手为我做的一大碗荷包面,我叫外婆吃,外婆却说这是专门为我做的,吃了管着出门顺利的,我依了外婆,不管灵不灵,这是外婆的心意。
我走了,外婆拄着拐杖与家里人把我送出很远很远,快要看不见时,我回过头去,外婆一个人依然站在那儿,她一面挥着手一面还在抹着她那早已老迈昏花的眼……“外婆!”我用心呼喊着,眼泪顺着脸颊直淌下来。
几年学业结束后,我回到了家里,游子返乡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养育我供我上学的母亲与退休不久的父亲及弟弟们早早地迎了出来。岁月如梭,时光流逝,我看到父亲母亲也老了,透过母亲那逐渐斑白的头发,又想到了外婆,“外婆……她好吗?”不知不觉中母亲也变成了外婆的样子,喋喋不休的告诉我说,“你外婆前几天还念叨呢,听说你快回来了,就让你舅舅掰了很多自己院子里早熟的玉米给我送来,说给你煮煮吃,怕是以后上了班,身子忙不能及时回来,吃不着这一年到底的新鲜东西”。我看着母亲边说边捧到我面前的熟玉米,鼻子酸酸的,我颤抖着手将玉米捧在手中,饱含深情的用舌头舔上一口,好香呀!
后来,我被分配到异地乡政府工作,在我工作之余,又去看过外婆两次,但都是来去匆匆,都没能在外婆面前多陪陪外婆。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外婆病逝了,寿年八十七岁。我得知外婆病逝的消息,急忙告假启程,但由于那个时候交通通讯设施落后,我没能见上外婆最后一面,舅舅告诉我说,在外婆患病期间,念叨遍数最多的人就是我,因为知道我工作忙,是外婆坚持不让舅舅舅妈给我去信,她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我好好工作,有了文化知识好好报答社会,报效祖国。我听了心如刀绞,泪雨穿肠,悲痛万分,心神魂祭。舅妈告诉我,外婆走的时候,戴着的是她最喜欢的,我给她买的那顶黑绒帽,这也算是给我一点点安慰吧。
外婆走了,永远的离我而去了,但是,她的身影依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