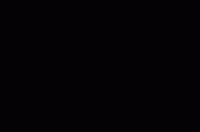满满的半年一直都是关在房子中度过的。
调休,终于可以出去走走,提着包站在路边等车,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将本应该绿草茵茵的春天淹没了,手冷的无处安放。
我有大把的时间等车,我有大把的时间站在这里,我有大把的时间感受喜悦的过程。
野虎坡那里有个老头子吃力地推着三轮车,冷风里一点点的将他的三轮吃力地向前推移。丢下包,跨过来来往往的车子,没有问是否需要帮助,便将车子推了上来,老头不断地朝着我离开的地方说着感谢的话,天太冷,冷的耳朵完全可以不理他。快些上路吧,天黑的好像马上就有雨要落下来,你继续推着你的车子赶路,我继续等我的车。
自打退役后再也没有怎么穿过皮鞋,这次我将发下来的皮鞋翻出来擦得很亮,配上一次都没有穿的裤子,即使站在冰天雪地里也是很高心的,其实高兴的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接到了一条信息。
“在哪里?我想……来找你”
那会的我几乎激动的快要将面前运作着的电脑抱起来丢窗外,奈何上面还有我好不容易码好的文案,领导大爷已经催促了好久的文案,扔掉之后我将面临继续上班的可能。
受疫情影响,公交车的班次调整成了两个小时一班,等了或许两个小时多一些了,它依旧没有驶来,点了支烟,准备继续等待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候,有一辆五菱神车紧挨着我锃亮的皮鞋巧妙地擦了过去,气急之下的我将脏话脱口而出。
“哟呵,小伙子会说脏话了呀!”
话是从这辆车子里传出来的,是奇哥,前晚喝醉酒后硬要让我给打醉拳的他写诗的人,我的前辈,我的同事之一。
他将准备跟公交车钢到底的我一口气拉到了我准备要去的地方,两个小时的车程,我问他来城里干什么,他摇下车窗,淡淡地说,他来送我一程。
五十岁的小老头缓缓掉头,一溜烟消失在了雨雾中,我呆呆地望着这个平时只有工作往来,感情纯粹到只是同事关系的他,竟找不到一句表达感谢的话来。
由于工作的性质,我的工作地很偏僻,甚至偏僻到了荒凉的地步,举个例子,白天奇哥带着小范两人出去跑步,两人在一片荒地上发现了一个彩钢修建的屋子,好奇心的促使之下,推开彩钢屋门,一口夺目而来的棺材让小范连续吐了好几天。
扯远了,继续回来。
刚子给沉浸在奇哥给的感动中的我当头一铃声,当听到我站在他在的城市里的时候,他挂掉电话开着车子冲了出来,顺道还拉上了我们两共同的好友瑞瑞。
或许是他们两人都因为公司裁员的事情喝了很多白酒,锅里的水熬干了又换,换了又熬干。我抽空跑出去给女生打了一通电话,我担心她会久等着我,电话就像沉进了大海,只有无人应答的嘟嘟声传了过来,我想她可能此刻正站在雨中冻得瑟瑟发抖,或者举着快没有电的手机期盼着我的到来。
刚子和瑞瑞还在喝,我准备辞别的时候,信息响了,是她发来的,她只是淡淡地回复我,她的生意忙,抽不开身。
还好,她没有站在夜雨中。
后来,刚子和瑞瑞被我左拥右抱地塞到了他们公司的安保手中,看着一个个躺在自己床上,熄了灯带上门走了出来。
雨已经变大了,亮起灯的整个城市显得格外的矮小。
钻进刚子的车里,刚刚开到地下室门口的时候,我拨转了方向盘,我想去找她。
七楼的灯依旧亮着,多年不见的她依旧坐在阳台上,宛若刚刚分别的场景。她的身后的橱柜里摆满了各色的商品,她在网上给客户细心地一一讲解,略显疲惫,突然她的身后有一男子出现,蹲在地上慢慢挪移,慢慢躲过客户可以看见的范围,挪移到她的膝盖跟前,轻轻地给她盖上一件毯子,然后又慢慢地移出了视线。
……
哦,这一路匆匆赶来,似乎忘了她已嫁,已经有了家。
补光灯还在她健康的头发顶空亮着,远远看着就像信仰里骑着风马旗的神仙一样漂亮。蹲在她身后的那个男人亦那样温柔。
离开的时候已是夜半,这座城市将春意短暂地藏匿起来的时候。
司机师傅问我该怎么走,我说沿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天会亮起来,瘟疫会过去,成千上万的奔走者会到达目的地,那里春暖花开,而你……
顶着野花编织的花环,提着长裙,漫步花丛中,美的像个行走在人世间的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