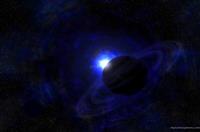有些老旧的床榻,我们结婚时的,盖有二十多年的光景,搬了新居之后,有闲地儿养养花草,尤其是这两年更多,便在卧室放上两盆,皆为竹类,一棵三尺高,另则两尺有余,是不会开出鲜花的那种,卧室内光线略暗,不宜花儿的开放,也不宜明媚中的欣赏,而此竹类的,生力坚韧,又四季常青,婷婷然,皆欢喜。却不知为何,仰卧床头,凝视伸展的竹影,想到追悼场面的亡灵。
那不会是香水的味道,那应该是鲜花的香馥,是白色的百合、黄色的菊花,在逝者的灵前,散发出淡淡的香泽:如果你不是战战兢兢思考亡人的往事,或者尚存于世的当场光彩;如果你不是仅仅看到那冥冥火烧的味道,或者沉醉于玩世守丧的夜酒,甚至那一次,我在拔掉遗弃的那些鲜花之时,手中依然有鲜花那淡淡的味道。
那些白色的黄色的鲜花,在追悼的哀乐之前,就已经整洁的摆放在灵柩的四周,满满盈盈,像春天的花海,艳艳颜颜,像青春的模样,除却表达对亡灵的哀思及尊重的礼仪之外,也许其生前并不喜爱这些鲜花,大抵也知道什么是祝福的百合与康乃馨,甚至一世未曾得到一次的掌声和鲜花?那隆重而追悼的花饰于他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生前的好,像我床脚之下的,相类松柏长青的竹木,现实地在自己的目下,任我凝视而赞叹,引我沉静而神宁,却又是生活的,蓬勃的,是常青的翠绿的,而且一年要高过一年,那笔直的干和舒展的叶,几乎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家庭的一部分,是我的心灵与眼光的一盆安抚,一缕惬意,完全属于自己的,不是礼仪给看客和场面,不是常青给文字和传说,这些花花草草,普通如自己的生命,不分你我。
于此我还要在床前摆放时令的鲜花,让自己熟睡在鲜花草丛之中,在梦里觅到桃源,嗅到幽幽的香味在世界里弥漫。我的妻子早就知道这些吧,即使并不涉及生前与死去,却知道自己的床前应该有美好的东西,陪伴自己入梦;她的枕边常常放一枚苹果,红润的硕大的光洁的,散发着幽香把陈梦迷荡,又或者放就一箱子的水果,虽不急用,她会打开,让香味在我们安息的地方,把安宁和平凡的夜晚,微微的荡漾。
当然,虽非伟者学人,却也常常在床头枕边,发一摞的书,那是另外的花木,让自我身心沉浸在涛涛花海汩汩淙流之里,随手一个翻阅,就是花草的注视,随眼一眸光亮,就是一种希望。在这新鲜的草木间漫步,在一瞬间安逸神飞,不惧眠前的人世烦恼与是非曲直,所以,当为“卧室榻前以古书”。
而朦胧的光线中,花草与古色古香的书,依旧散发着一类的香馥,而目光洒进我的卧室,那又是如何的模样?在花木的榻前刚刚读到刘禹锡的怀古:“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于生死茫茫者,这是什么模样,又是什么花草?我们的人间和冥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