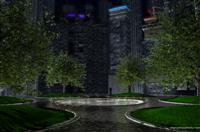
核心提示:实际,刚到北府时,溥仪就已经暗中策划,作好了投奔日本人的打算。他先是以去德国医院看病的借口,暗中地出入日本大使馆,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交易的默契。
文章摘自《末代太监孙耀庭传》 作者:贾英华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溥仪悠闲地走进了储秀宫。
这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太阳刚刚露出了一个侧脸,储秀宫凌空翘起的飞檐邸吻上,稍稍染上了一层淡淡金色。
晨曦微露,孙耀庭起了床,匆匆赶到储秀宫婉容的屋外站班。
“万岁爷到!”随着一声传报,溥仪走进了宫。他身穿一套西服,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脚穿一双锃亮的皮鞋。
“万岁爷,”孙耀庭小心翼翼地向溥仪禀告,“现时,皇后还没起床……”
“知道啦。”溥仪一摆手,自顾自地走进了屋。
“来,寿儿,”溥仪进屋后,见婉容果真没起床,就叫醒了她,然后,又走了出来,“跟我踢毽玩儿。”
孙耀庭转身进屋拿出了一个鸡毛毽,走到了院中。
“接活儿……”溥仪踢了几个之后,猛然将毽挑到了孙耀庭眼前,他急中生智,马上用脚接了过来,将毽子又高高地踢到了空中。
前不久,婉容的生日过了没多少日子,十月二十日,端康太妃突然发病,在永和宫溘然去世,灵柩移奉慈宁宫。仿佛为这即将寿终正寝的末代王朝发“丧”似的,满朝大臣都披起了孝衣。
外人不知,宫里有一个奇特的规矩,平时谁也不准擅自拍巴掌,如有违犯,定是轻饶不了。只有皇上、皇后、太妃殡天或忌日,由敬事房的太监通知,约定时辰,乾清宫太监总管一拍三下巴掌,众太监便齐声哭出来,叫作“举哀”。
其实,这最多是无泪干嚎,民间通常贬义地俗称之“嚎丧”。哭上几声,再由乾清宫太监总管拍几下巴掌,遂告“哀止”。由于孙耀庭一直伺候端康太妃,还真的抹了几滴眼泪。
在一片悲凉的哭丧声中,还没等棺椁正式“发丧”出宫,震惊中外的“逼宫事件”,又敲响了逊帝那“小朝廷”的最后丧钟。
多事之秋。一九二四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与直系军阀冯玉祥拉开了一场“中原逐鹿之战”。对峙的双方,剑拔弩张:吴佩孚当时是直系总司令,亲自上阵督师作战。冯玉祥当时任前线总指挥,九门提督王怀庆任副总指挥。时任直系陆军检阅使的冯玉祥,又亲率两师人马驻兵南苑。
直奉战争的结局,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正当双方面临酣战之际,冯玉祥突如其来倒了戈,回师京城,将贿选上的大总统曹锟囚于中南海延庆楼。随着冯玉祥的一纸“和平通电”的发出,直系军阀彻底宣告崩溃。
宫外急转而下的局势,对于“小朝廷”非同小可,然而,宫内仍是一潭死水。溥仪没有因此丧失了雅兴,一起床,就到储秀宫踢起了毽子。
表面看上去,他神态自若,绝没有想到,直奉战争竟能使他的命运发生历史性的突变。
紧锣密鼓中,京畿警备司令鹿钟麟建议紧急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修改“优待清室条件”,与此筹备成立“清室善后委员会”。
)
当毽子高高地被踢起在空中时,溥仪的命运实际已经发生了变化。只不过,他全然不知罢了。
这当儿,孙耀庭边陪着他踢毽,一边时时地观察着婉容的动静。他见皇后起了床,就对溥仪奏道:“奴才听皇后起来啦。”
“走,进屋去。”溥仪叫他进了屋。见婉容到西暖阁去漱洗、梳头,孙耀庭去后边拿出了一块布,“万岁爷,我给您擦擦皮鞋。”
“得,你少打点儿油。”溥仪随便地跷起了脚。
“是喽。”孙耀庭仔细擦着皮鞋,又恭维着与他聊天。没过一会儿,溥仪抬起了脚。“得,行啦。”
溥仪又随心所欲地走到钢琴前坐下,欢快地弹起了钢琴。岂料,这正是“出宫”的前奏曲。
弹了没几下,琴声戛然而止。溥仪忽然想起了还没喝早茶,便吩咐孙耀庭传“茶盒子”。
“回万岁爷,‘茶盒子’还没来呢。”
“就拿娘娘的喝吧。”溥仪倒不十分在乎。
溥仪停下来,洋洋自得地喝着早茶,尔后,又继续弹起了钢琴。
一曲未终,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宝熙,以及溥仪的老丈人荣源,紧急进宫求见。溥仪知道这时,没有十万火急之事,他们无论如何不会追到储秀宫,于是一声:“传……”
“传见!”孙耀庭马上对外边的太监喊道。
“走,你跟我到翊坤宫去。”溥仪起身吩咐孙耀庭。
他赶紧随溥仪身后到了翊坤宫,他知,溥仪若非急事不会在皇后读书的地方召见。
“内务府大臣到……”奏事太监一声传唤后,绍英等人匆匆而入,孙耀庭便按规矩退了出去。
“嘛事儿,这么急火?”孙耀庭问站在外边的奏事处太监。
“咳,你还不知道?”那个太监瞧了瞧四周,压低了声音,伏在他的耳边嘀咕说:“冯玉祥派鹿钟麟和张璧带着手枪队进宫来啦!”
“啊?!”孙耀庭闻听,大惊失色,他知道进宫的这两人是赫赫有名的战将。鹿钟麟是京畿卫戍司令,张璧是警察总监,都是京城人所共知的军界实权人物。他神情惶遽,不断叨念说:“这可咋好呢……”
“你猜怎么着?”那个奏事处太监,谨慎地推他到了墙旮旯,“他们带的手枪队和大刀队都进了宫!连内右门都给关上了,谁都不让随便进出喽!”
听到此,他吓得一吐舌头。“哟,这下要出大事啦!”
“谁说不是呢?!”奏事处太监也面显惊恐。“万岁爷还不知道吧?”
“可不是,刚才还和我这儿踢毽呢。”他明白了,事态的严重,在于皇上还根本不知这回事。
早在前不久,他就听有的太监传闻,冯玉祥的军队可能要进宫抓溥仪,估摸是个谎信儿,也就没当真。过了几天,他又听说原先被溥仪驱逐出宫的太监,有的联名去了冯玉祥的京畿警备司令部,揭露溥仪盗卖宫内珍宝之事。对这些,他也没听进耳朵里去。谁知,传言如今竟成了事
呆了不长的时间,绍英等人慌慌张张地走了出去。溥仪又吩咐孙耀庭与他返回了婉容的屋里。
“你不知道,冯玉祥要逼我出宫!”他气急败坏地对婉容说着,神色极为慌张,早已没有了之前的潇洒。
“万岁爷,先甭着急……”表面上,婉容倒还沉得住气。
“他们让咱立刻离宫,要不,景山上架着大炮,就要对准宫里头开炮啦!反了,反了……”溥仪愈说愈有气。
“寿儿,”溥仪冲墙角站着的孙耀庭吩咐说,“你赶紧到长春宫告诉淑妃,就说让她越快越好,收拾完‘细软’,到储秀宫来!”
“……”孙耀庭闻听,一溜烟似的奔了长春宫。
当他气喘吁吁地跑进长春宫时,文绣已然听说了风声。“传万岁爷的话,让您马上拾掇东西,去储秀宫。”
“万岁爷呢?”
“回养心殿了。”他如实禀报了淑妃。
这时,文绣显得比婉容又沉稳多了。“寿儿,我知道啦,你回皇后那儿去吧。”文绣马上吩咐随身太监,麻利儿敛裹东西。
当孙耀庭一溜小跑儿回了储秀宫,婉容正急得团团转。“寿儿,万岁爷正找你呢!”
“皇后主子,您知道是嘛事儿?”
“你问一下皇上就知道了,他大概是让你帮着找人。”
于是,孙耀庭又转身跑去了养心殿。整个宫内简直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太监和随侍来来往往搬运东西。
刚进殿,溥仪一眼瞅见了他,心急火燎地吩咐说:“寿儿呵,赶紧把荣源找来……”
“……”孙耀庭又立马离开了养心殿。
结果,他四处寻找了一圈,大失所望。有的太监告诉他,荣源与那些内务府大臣被宫外的大炮吓昏了,不知躲到哪儿去了。
在此前后,绍英作为内务府大臣,正出迎鹿钟麟。在宫内,鹿钟麟向他出示了国务院通过的清室优待条件,要他转告溥仪,立即迁出皇宫!绍英虽几经斡旋,仍告无效,见确实无法阻止鹿钟麟,于是说:“请稍候,我去禀报‘皇上’……”至此,他不由仰天长叹:“大清国算完啦!”
这时,鹿钟麟眼看时间延误,灵机一动,故意对随从大声喊道:“快去告诉外边,时间虽然到了,事情还可以再商量,先不要开炮,再延长二十分钟……”
这个戏剧性的情景,绍英马上告诉了溥仪。其实,这正中鹿钟麟下怀。溥仪闻听大惊失色:
“告诉他们,我答应迁出宫外,容我收拾一下衣物。”
惊人的消息,像长了飞毛腿,瞬间便传遍了皇宫各个角落。
“皇上答应出宫啦!让咱们马上拾掇东西,晚了军队一冲进来,可就来不及喽……”
“万岁爷刚刚交出了‘传国玉玺’,给了鹿钟麟!”
莫辨真伪的几声惊呼,皇宫可就全炸了窝。孙耀庭向婉容这么一禀报,她没了主意,哭丧着脸,小声地对他说:“你可甭为了咱们这点东西丧了命啊!要是有军队的大兵来要这些个东西,你就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主儿’的,非要不可的话,索性痛痛快快地递出去,就是千万别出什么乱子,能保住人怎么都行……”
这一番话,把随后走进来的几个太监、宫女深深地打动了。没想到,平日她对大家没显出过多亲热劲,节骨眼上还挺有点儿情分。
这时,婉容哭了,眼泪一行一行地往下落,随之,大家也禁不住痛哭失声。瞬间,整个储秀宫内哭成了一锅粥。
午饭端了上来,谁也没有心思吃,大家你瞅我,我瞧你,哪个人都是心事重重,愁眉紧锁。饭,由着它凉了,又撤了下去。午饭没吃成,外边又喊了起来:“赶紧出宫,出去晚了,可就不行啦……”
怎么个不行法,哪个说得清?可谁也不想把性命当儿戏,纷纷七手八脚地拾掇东西。
“万岁爷让咱们一起从顺贞门出宫。即刻准备停当。”奏事处太监赶了来,传达了溥仪的最后一道旨意。
总算能活命了,孙耀庭叹了一口气。惟恐发生其他变故,婉容与孙耀庭等人商议,不多带什么东西了,只拿几件随身的衣物,先保住命要紧。众人点头称是。
午后两点钟,一嗓子不知从哪儿传来的吆喝声:“出宫喽……”凄凉地回荡在如临大敌的宫内,更增添了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感。孙耀庭明白约定好的最后出宫时限已到,用眼角瞟着婉容的脸色,悄声地禀告说:“皇后主子,时候到啦。”
“走……”她的嘴巴张了张,只说出了有气无力的一个字。
这一行人,以婉容为首,提着大小包裹,在御花园东头迎候溥仪。一会儿,溥仪身后带着几名非太监的“外随侍”,淑妃文绣、溥仪的岳父——荣源、内务府大臣绍英、宝熙、耆龄,也随之疾步走了过来。其中最显眼的是,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刚才,溥仪让孙耀庭四处找荣源时,他就见到了载沣走进宫门,神色慌张地奔向了养心殿。他身穿上朝的“补服”,头戴宝石顶的帽冠,引人注目的是那三眼花翎,在顶戴上微微颤抖。
正当几股人从御花园走向顺贞门时,载沣面对景山的万寿亭,慨然兴叹,“咳……”随之,又悲痛欲绝地吼道:“大清国从此完啦……”
众人,包括溥仪在内,眼看他将三眼花翎的朝冠,顺手扔弃在假山旁,谁也没吭一声。溥仪和皇后、淑妃以及身旁的三十多个太监、宫女,默默地走向了御花园后门——“顺贞门”。
微风中,只有那三眼花翎,随风轻轻地颤动着。
丢弃的三眼花翎,不仅标志着清朝摄政王的地位,早已付诸东流,也成为了溥仪前途的谶兆。
孙耀庭跟随着溥仪走近神武门,只见几辆轿车在那儿已等候多时。鹿钟麟神情严肃地通知溥仪:“这是要接你们到北府去!”说话的口吻,没有丝毫余地。
也没向溥仪打招呼,张璧径自上了第一辆轿车。溥仪第一次被指定坐在了第二辆轿车上。孙耀庭和另一个宫女陪着萎靡不振的婉容,坐进了第三辆车,淑妃文绣则坐在了第四辆轿车里。第五辆,是负责殿后的鹿钟麟乘坐。绍英等内务府大臣登上了末后的轿车。只见宫门两旁,站立着戒备森严的手枪队和大刀队,一个个面色铁青,如临大敌。
轿车驶出神武门时,孙耀庭偷偷地朝外瞧了一眼,吓得汗都冒出来了,一看婉容也是紧张得要命,不错眼珠地瞅着前面车子将要驶往何方。
街上,除了警戒的军队以外,挤满了围观的老百姓。驶近后门、柳树井时,路两旁围观的人群挤了一街筒子,人山人海。
“‘皇上’出宫来喽!”
“看‘皇后’噢……”
街上的人们,指指点点,朝着车子驶来的方向拥着,嚷着……孙耀庭见婉容拼命地低头,惟恐百姓认出她来,宫女害怕得脸都变了色。此时,他两手紧攥着车上的把手,额头也沁出了大滴汗珠。
一连串的汽车喇叭,驱散了路上的行人。张璧乘坐的汽车在前,鹿钟麟乘坐的汽车殿后,仿佛押送一般,在不断的鸣笛声中,轿车驶向了什刹海北岸的醇亲王府。
事后,孙耀庭才听说,他们刚出宫,鹿钟麟便下令让太监和宫女们自择出路。一时,宫内一片泣声。
这些人,大多自幼进宫,毫无生活技能,出宫哪儿有什么活路?有的太监和宫女,在宫中多年,藏有点儿私房钱,便卷起铺盖,出宫自谋出路去了。但也有的太监无人可投奔,连路都不认识,才出宫,就跳了筒子河。这比溥仪当年遣散太监更轰动,一时竟成了京城爆炸性的新闻。
有的太监见此,重提当年溥仪从宫中轰赶太监的旧事,对“皇上”被驱除出宫,幸灾乐祸地喊道:“这才是一报还一报呢……”
孙耀庭伴随溥仪和婉容等人一下车,便见持枪的国民军站上了岗。他悄悄地对一个小太监说:“这可不好,好像又进了牢笼!”说着,一吐舌头,扮了个鬼脸儿。
下了车,鹿钟麟义正辞严地说,让他们去北府,是为了保护溥仪的安全起见。实际,这等于把溥仪又装入了一个结结实实的“罐子”里。“不许随便出入”,这是鹿钟麟对溥仪等人的一项强制要求。
几十年后,一位记者潘际垌先后造访了溥仪,以及隐居天津的鹿钟麟,以见证人的身份,追述了这个“逼宫事件”的内幕始末。
逼宫的情景,溥仪是跟我谈了的。当时他在储秀宫和后妃在一起,是内务府大臣绍英,耆龄他们慌慌张张进来通知这件大事的。他特别提到,在醇亲王府门前,还和鹿钟麟等人握了手。后来,我在天津专诚拜访了当年的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才完整地知道那富有戏剧性的一件史实。鹿老先生此时七十四岁了。
在天津著名的饭馆周家食堂,我们倾听着鹿老先生的回忆。同座的有胡若愚先生和我的一个朋友。
谈起逼宫这件事来,有远因,也有近因,豪迈的鹿老先生喝了一口绍兴酒,从容地说下去,他带着浓重的河北定县口音。‘远因是辛亥革命,不彻底,近因是张勋复辟。当时我们许多人觉得,宣统太不安分了。’……
‘是啊,我记得有一个时候,北京的铺子里又卖做辫子的假发,又有人挂龙旗了。曹锟甚至到处打听会写奏折的人才呢。’胡先生笑着插了一句。
是那样……我们是奉冯先生的命令逼宫的。在逼宫的前一天晚上,内阁总理黄郛(膺白)、警察总监张璧(玉衡)和我三个人筹划这件事。他们要我主办。我当时就想,千万不能打草惊蛇,真的在宫里打起来,外国使馆一定出面干涉,那就糟了。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后来,谈到行动时我们这方面要带多少人进宫的问题。我想了一想,伸出两个手指头。
黄膺白就问:‘要两万?’我摇摇头。
他又问:‘那么是两千人是不是?’我又摇摇头。
他最后说:‘总得带二百吧?’我还是摇摇头。我说:‘只要带二十个人的手枪队。’他们一切都信任我,没有反对。第二天我带着手枪队,自己怀里又揣了两颗手榴弹。进宫以后,看见一个守卫的,叫他站住,不许动,看见一个送饭的,挑水的,也是如此。跟着我就去找内务府大臣绍英,说明了来意,限溥仪在二十分钟以内离宫。
我还对绍英说,景山上已经架好了大炮,过了二十分钟就向宫内开火。我呢?我可不能牺牲在自己的炮火之下,说时就将怀里揣着的两颗手榴弹,往绍英面前的桌子上一掼。绍英吓死了,答应立即报告溥仪。他又苦苦央求,希望放宽些时间,收拾行装。我说:‘再加二十分钟。’转身又吩咐手枪队:‘告诉兄弟们,再加二十分钟为限。’
‘后来呢?’我问。
后来,溥仪就在这四十分钟以内离宫了。我们替他准备好了汽车,把他们送到什刹海的醇亲王府,他父亲的家里。
……
“到了他父亲家的门口,我就跟溥仪握手,并且问他今后是自称皇帝呢?还是用平民的身份?溥仪说愿意用平民的身份。我说那我们就保护你。”
无疑,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听其言为次,最重要的是要观其行。综观溥仪尔后的行径,并非真要做平民,仍是发自衷心地要当“皇帝”。照此看来,倒果如外界所评论的:
“溥仪进了醇亲王府,过的日子不是平静的,也不可能是平静的。”……
“皇后主子……”
刚进北府,孙耀庭就从兜里掏出了一个几斤重的金光闪烁的大元宝,继而,又掏出了整整十个小元宝,别看才手指头大小,每个却足有十两重。“这是奴才给您带出来的!”
“哎呀!”婉容一见这些,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了。“你连这些也带出来啦?”
“这是奴才的一点忠心!”他双手紧合,两眼诚挚地望着婉容。
当时,到了北府的太监,绝大多数一丁点儿东西都没交出来。有的没跟着坐车出宫,有的虽说是坐车出宫的,却丝毫什么也没交出,只谎称,慌乱中没顾得上带出来。
就在出宫之前的当天下午,孙耀庭见桌上仍摆着婉容大婚的订礼,两个手掌大小的大元宝,以及二十个手指大小的元宝,像平时那样纹丝没动。他与太监时来祥商量,一人带一半,由富妈把婉容平时使用的一些头饰,加上拾掇的一些细软,带在身上,等到了北府再交给皇后。
混乱中,时来祥到了北府,只露了一个照面,连招呼也没打,就悄悄地溜走了,任何财宝也没交。他从前当过御前太监,曾深得溥仪信任,为了关照婉容,溥仪特地将他从身边调往皇后处,可才两个来月,就赶上了这场乱子。据说,他发了这笔横财后,就回了老家南苑,从此再也不露面了。
然而,婉容心地单纯,到了北府还一个劲儿地问:“为什么见不到时来祥了?”孙耀庭不好点破,只好支吾了过去。“周福呢?”她又问起了与时太监一起从溥仪处调来的周太监。
“压根儿呀,他就没来北府!”孙耀庭见无法隐瞒,只好将一些情形,据实以报。
她又一连问了几个妈妈的下落,他心知她们乘机拿走了宫中的珍宝以及皇后的私房,怕她伤心,不愿全点破,只得搪塞说,“这些人,全没来过北府,连影儿也没啦。”
“知道了。”婉容也顾不得这些,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命就得了。
“奴才得跟主子告假……”
“上哪儿呀?”
“奴才光顾给主子拿财宝,自个儿的东西,连铺盖都还没拿呢。”
“去吧,”婉容听到这儿,感动万分,自然不阻拦他了。
于是,他独自一人回了宫。在军队的监视下,他到翊坤宫拿出了平时穿的几身衣服,以及铺盖,又悄悄收起了平时积攒的四百块现大洋。之后,他又如约返归北府。
自打跟着溥仪躲进了摄政王府,他一直伺候婉容,没敢动窝儿。一天,前边的小太监悄悄对他说:
“春寿,听说张宗昌进府来啦!”
“做嘛来了?”张宗昌在被逐出宫的皇族眼里,俨然是个“救星”式的人物。孙耀庭如今与北府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忒看重军阀的实力。
“不知道,”小太监摇摇头,自然说不出子丑寅卯。
“是吗……”他告诉了婉容,但她有些不太相信,却比在宫内明显关心起了外间的事儿,不消说,这直接关系着她的命运。“打听一下,他来干嘛?”
此时的形势瞬息万变,他再明白不过了。前去打探了几回,都没问出个究竟来,他只好懊丧地交回成命。
刚刚起了床,婉容就听说溥杰的夫人唐怡莹请安来了。“进来吧。”
“主子,夜里歇觉歇得好吧?”唐怡莹当时与溥杰结婚不久,打扮得十分俊俏。一进屋,双手扶膝,向她请了一个蹲儿安。
“好……你坐会儿吧?”婉容说着言不由衷的客套话。
贵族门第出身的唐怡莹,自然懂得这些,见势便客气地告辞:“不了,我还得去太太那儿。”说完,嗒嗒地踏着高跟鞋,走了。
尽管难以置信,但确是如此。在北府“避难”的一个多月中,婉容住在东跨院,淑妃住在另一侧,而溥仪住在她们前头院。其间,溥仪竟连一次也没到过婉容院里,甚至他与“后”、“妃”三人根本没在一起吃过一顿安生饭。
仅从婉容这儿说,与宫里的吃喝差得邪乎了。往日,婉容总爱吃馒头,很少吃米饭,可在这日子口儿,如果仅是米饭端来,她只能是勉强咽肚,一顿只有两三个菜,主食也就那么一两样。先仅着婉容吃,收了盘子后,孙耀庭再原封不动地把残羹剩饭端到厨房,悄悄地往嘴里扒拉两口,就算是吃过了饭。
“端康主子还在慈宁宫停灵呢,现如今谁也顾不上了,这总得有个着落啊。”孙耀庭与赵荣升议论说。
“是呵,要不是赶上天凉了,还不有了味儿?”赵荣升也焦急此事,他毕竟伺候过端康几年。
其实,不仅端康的灵柩没人管,连溥仪出宫后的当月十一月二十一日,才从宫里慌慌忙忙跑到荣寿固伦公主府的敬懿皇贵太妃和荣惠皇贵太妃,都没人顾得上了。只有一两个出宫的太监恋着旧情,才去大佛寺西街看望过这两位“女主儿”。
乍进摄政王府那阵子,溥仪急得火急火燎,哪儿顾得上端康的灵柩?但皇族都注视着溥仪在危难之中的此举。载涛向溥仪主动请求,一手办理端康的后事,溥仪正巴不得有人出面,乐得答应由他筹办。不多日,在载涛的操持下,赵荣升、蔡亚臣两位太监组织出宫的太监和其他一些杂役将端康的灵柩,暂时停厝在京城北边的广化寺。后来,才又移棺安葬在了清西陵。
此时,在摄政王府内外,休说孙耀庭,就是婉容也不知,勾结与阴谋的阴影已经完全地罩在溥仪的头上。躲是躲不过去的。
实际,刚到北府时,溥仪就已经暗中策划,作好了投奔日本人的打算。他先是以去德国医院看病的借口,暗中地出入日本大使馆,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交易的默契。
当一切都已在幕后策划完毕时,他带着贴身太监,装着没事人儿似地溜达到了北府门口。
“您哪儿去?”奉命把守北府大门的丁营长,一个立正,然后客气地欠身问道。他是冯玉祥的部下——京畿卫戍司令鹿钟麟的亲信。因为,他们始终耽心溥仪出宫后的安全和去向,所以派他来专门看管溥仪。府门口西边一拉溜平房里,驻扎满了军队,正在对他实行着“保护”。
“我出府,瞧瞧我的姑姑去。”溥仪小心翼翼地对付着。“你放心,我看看就回来。”
丁营长犹豫再三,实在找不出任何理由来阻拦他,只好一挥手:“可麻利儿回来!这是上头给我的任务嘛!”
可是,溥仪一出府门,却如“黄鹤一去不复返”,径直奔了荣寿固伦公主府。日本公使芳泽早恭候已久了。
翌日,婉容和文绣也到了摄政王府门口。
“你们上哪儿去?”门口的大兵把枪一横。
“哟,这我们可做不了主,得请示上司。”说着,两个大兵将丁营长叫了出来。
“这可不行。溥仪出去看姑姑还没回来呢。”丁营长毫无通融的余地。
这时,北府的管家张彬舫走上前,虽有些文绉绉,却是理直气壮地说:
“丁营长,你不让人家去看姑姑,无理可言。前两天,你听见了吧?溥仪已平民之化,你能让人家两口子再分家吗?”
一席话,说得丁营长哑口无言。
“我再回报一下,你们稍候。”
“还回报什么?溥仪都是平民了,家眷就更甭提啦。这会儿呀,愿上哪儿上哪儿去,没什么可说的!”
趁丁营长犹豫的当儿,张彬舫连蒙带咋呼地带着婉容和文绣离开了北府。
其实,远非按照事先策划,连溥仪出走,婉容之前也丝毫不知。尔后,婉容和文绣也没去荣寿固伦公主府,而是直接奔了日本驻华公使馆。
为了避免嗦,孙耀庭这些太监统统没有跟随,只是不明真相地暂时躲在了北府。对于张彬舫带两位“后”、“妃”出走北府之事,太监们服了气,议论纷纷。
“管事的可真行,见着带枪的愣不怵!”
“张管事的不是一般人,他是张作霖的把兄弟喏。”
“噢,怪不得这么能干呢。”
是啊,孙耀庭情知溥仪这一去可就没谱儿喽,自己今后出路何在?人海茫茫的京城,何处是立锥之地?
当他们这些太监,确切获知“万岁爷”出走的消息后,惊愕万分。婉容出府的当天,他们就没了饭辙,王府的膳房不再开伙了。孙耀庭要求见王爷——摄政王载沣。
这位稍一紧张,说话就微微结巴的王爷,在书房接见了孙耀庭等几个太监代表。
“你……你们有什么……事儿呀?”载沣待人蛮和气。
“我们这些人没饭吃啦!”
“还请王爷开恩啊。”
孙耀庭与另外几个太监七嘴八舌地央求着。
“这是怎么回事儿?谁让撤的伙?”载沣叫来了管事的。
“这是没法子,万岁爷走前也没留话儿,今后怎么办呢?请王爷做主。”张彬舫深知内情,没好意思出面,仅让一个小管事的出来禀报载沣。
“你……们好好……看……着家。照旧……照旧……”这个“照旧”,他一连说了两遍,越说越结巴。
孙耀庭觉得没个明确说法,只管几顿饭,今后咋办呢?他们不走。载沣进了里屋,不再出来了。
他们无奈回了房,正合计着,过了不大工夫,管事来了:
“王爷再叫你们去一趟。”
于是,他们二次进了载沣的书房。不一会儿,载沣仰着头,缓慢地从里间走了出来:
“这么着,你们一人拿五十块钱先回家吧。赶以后需要的时候,再找你们去嘛……”
管家把预备好的钱,分别递给了孙耀庭、德寿,以及跟着淑妃文绣的几个太监。当时,皇后与淑妃的几个宫女,几天以前就已经跟随去了日本公使馆。
孙耀庭心里头明镜儿似的,无疑,溥仪已经抛下了这些人。现如今自己上哪儿去呢?考虑再三,毫无生路,他们只得挟着简单的铺盖卷儿,沮丧地离开了北府……
蓦然回首,他觉得,北府门口的那对活灵活现的石狮子,仿佛张开了血盆似的大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