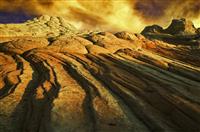我们这些熟谙金融史、明白金融危机及其影响相关经济思想史的经济学家有理由为我们过去五年中的分析感到自豪。我们知道我们在向何处去,因为我们有前车之鉴。
特别是,我们知道房价的快速上涨加上杠杆的扩张给宏观经济带来了危险。我们看出杠杆金融机构所持资产因泡沫破裂而遭受的损失将导致人们朝安全性多路狂奔,明白阻止深度萧条需要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官方干预的积极介入。
事实上,我们知道货币主义疗法很可能并不足够;知道各国需要互相担保偿债能力;也知道过早撤销支持意味着巨大的风险。我们明白过早追求长期财政平衡会恶化短期危机,从而不利于长期生产。我们也理解,我们面临着无就业复苏的威胁,这是由周期性因素而非结构性变化导致的。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重视历史的经济学家都说对了。说经济不会下行者、说会有很快复苏者、说经济的真正问题乃结构性问题者、说支持经济会导致通货膨胀(或短期利率高企)者、说立刻采取财政紧缩将收到扩张性效果者都错了。不是错一点,而是大错特错。
当然,我们重视历史的经济学家对于他们的错误并不惊讶。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的信条根本不是基于市场的。相反,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他们的名声早已一片狼藉了——死抓错误信念不放,显然是寄希望于形势有朝一日能够发生逆转,如此,人们或许会忘了他们此前糟糕透顶的预测记录。
因此,主要教训相当简单:相信那些站在白芝浩、明斯基(Hyman Minsky)、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肩膀上的人。这意味着相信克鲁格曼、保罗.罗默、加里、高登(Gary Gorton)、卡门.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肯.罗格夫(Ken Rogoff)、拉古兰.拉贾(Raghuram Rajan)、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奥利佛.布兰查德(Oliver Blanchard)及其同侪。他们说准了刚刚过去的形势,也最有可能掌握正确的未来概率分布。
但是,在过去四年中,我们——或者说,至少是我——在诸多重要方面都犯了错。有三件事让我感到很惊奇(现在仍是如此)。首先是中央银行没能采取以名义GDP为目标的政策(或其等价政策)。其次,我原本以为北大西洋工资膨胀会进一步下降到(接近于)零。最后,美国收益率曲线并未显著陡峭化:联邦基金利率如我所料降至了零水平,但30年期美国国债名义利率保持2.7%则出乎我意料之外。
我至今仍无法理解为何央行没能以名义GDP增长为目标,在我理解个中原因之前也无意撰文探讨此事。置于工资问题,尽管三分之一的美国劳动力每年都要换工作,但社会因素和人脉网络联系在工资变化率方面的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超出了我的预料,而这是以牺牲供求平衡为代价的。
不过,最有趣的还是第三件让我感到惊奇之事。2009年3月,诺贝尔奖得主卢卡斯信心满满地预测美国经济将在三年内重回正轨。正常状态下的美国经济伴随着4%的短期名义利率。由于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总是会高于未来十年预期短期利率平均水平1个百分点,因此即便预期深度萧条只维持5年、短期利率会下降到零,10年期国债利率也不应该在3%以下。
事实上,2008年末—2011年年中,10年期美国国债利率大体上在3%—3.5%之间波动。但是,2011年7月,利率下降到了2%,今年6月初更是下降到了不到1.5%。常规经验法则告诉我们,如今市场预期在经济重回正轨之前将经历8.75年的短期(近)零利率时期。以30年期国债为基础做类似的计算则指向时间更长、幅度更深的萧条。
结论是无情的。一种可能是金融市场的投资者预计经济政策将是无能的,全球经济将维持当前萧条状态达十年之久或更长。此外只存在一种可能:即使是现在,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已经三年的时候,金融市场为相对风险和回报正确定价的能力仍处于严重受损的状态,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承受和管理风险,从而将储蓄导向创业冒险。
不管那种可能,都不是我此前所能预测的,甚至连想都不敢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