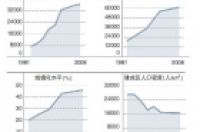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数据称,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
城市化的好处显而易见。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邦,为了更好的生活留在城邦。”城市化是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这已为现代经济史所证实,因为人口在城市中聚集,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大幅度降低经济活动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使得经济收益大幅度增加。这是中国政府大力推进城市化的最重要原因。
城市化的好处并不仅限于经济上,同时还体现在公共治理和民生等各个领域。由于城市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公共服务(比如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边际成本大为降低,这使得普及基本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成为可能。更重要的是,城市化有助于促进公平的发展,逐步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以《中国统计年鉴2009》提供的数据为例,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城市化水平越高的省份,省内的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也越小。参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发展报告2010:促进人的发展的中国新型城市化》,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早在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指出,工商业都市的增加与富裕,为农村的产品提供了巨大而便利的市场,促进了农村的开发,并使农村突破传统关系的制约,变得更有秩序,有好的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
从理论上讲,城市化更有利于集约利用土地。但是,如果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类似国家相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存在诸多的土地利用不当: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急剧扩张的1980年至2005年间,经济每增长1%,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在1965年至1984年的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的占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参见陆铭:《城市化三辩》,《财经》2011年第18期)
同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土地浪费现象严重。据统计,全国城市建成区面积由1981年的7438平方公里增加到2008年的36295平方公里,年平均拓展速度为6.3%,远高于同期城镇人口的年增长速度4.21%和城镇化的年增长率3.11%, 建成区人口密度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见图1)。
为什么更多的城市面积却容纳不了更多的城市人口?城市化的成本,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城市化的成本,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为城市化提供基础设施的成本,即路桥建设、地下管网和其他公用设施的成本,我们称之为“土地城市化”的成本;二是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即从基本不享受公共服务的农民转变为享受现代城市公共服务的市民的成本,我们将其称为“人的城市化”的成本。从过去三十多年,尤其是近二十年的城市建设经验来看,各级政府为解决土地的城市化,已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比如城投债就是地方政府为解决城市化过程中基础设施建设的经费问题而形成的金融机制。但是对于“人的城市化”,地方政府的举措却乏善可陈。
地方政府应对“人的城市化”缺乏积极举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需要巨额成本,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最终导致人口流入地经济停滞。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也就是城市给非本地户籍居民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自然需要财政支出。从短期看,缺乏“人的城市化”的“伪城市化”对现有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是有利的:由于不需要为外来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大大减轻;更多劳动力在城市里创造了更多财富,但受益人口并没有增加,因此城市原有居民也会支持这样的制度。(2012年年初,网上流传着一位上海年轻母亲的一封信,主要内容是认为“外来人员子女入学分享了上海本来有限的资源”。据统计,到2011年末,上海常住人口达2347.46万人,其中外来常住人口达935.36万人,已占全市常住人口总量的39.8%。这些外来人口及其子女都要在本地享受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自然会对本地财政带来极大压力。)
但由此导致的问题也显而易见。一方面,在现行模式下,由于非户籍人口无法在工作地享受公共服务,这部分群体的理性选择就是压缩支出,将工作地只视为一个工作而非消费处所。这样,认为城市化会促进内需的说法,就并未在这个群体上得到印证(一项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组成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课题组的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2010年平均年度结余9684元,其中寄回家的钱为5654元,占比58.4%;老一代农民工平均年度结余15378元,其中11063元寄回家,占比72.0%)。另一方面,从长时段来看,公共服务若不能均等地让所有居民受惠,将导致社会族群分裂,城市内部纷争增加(目前很多群体性事件往往是由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引起。从2010年开始,很多地区爆发了原住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冲突,如广东增城市新塘事件、浙江湖州市织里事件;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东部地区,很多经济发达地区的外来务工人员数量已经超过本地区民)。
二、如何测算“人的城市化”的成本?
以往有关“城市化成本”的研究,具体涉及“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时,存在三个特点。一是研究对象过于狭隘,专指农村户籍人口流动到城市,忽略了大量城市户籍人口的跨省区流动;二是将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界定为政府投入成本和个人投入成本,虽然具体内涵仍然没有共识,但大多包括社会保障成本(医疗和养老)、义务教育成本以及住房成本,且这三类是成本最高的类别;三是将非户籍人口市民化过程中的公共成本都归为政府投入成本,没有将相关公共开支中政府成本和个人成本分开考虑,依然在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分析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
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以上海为研究对象,集中研究上海市政府2008年至2012年在义务教育、基本养老保险这两项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最高的刚性支出项目上的收支情况,测算出非户籍人口、本地市民分别在这两项公共支出上的占比情况。
人的城市化,或者说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进展之所以缓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成本。在现有模式下,土地能够给地方政府带来巨额财政收入,因此地方政府更有激励去推动土地的城市化;但由于非户籍人口市民化需要支出,因此在推动人的城市化方面,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并不强烈。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对于基础设施的成本,都视为经济机遇,但是对于人口城市化的费用,却一直视为政府的负担(参见李迅雷:《城镇化:中国经济再增长的动力或阻力?》,华尔街日报中文网,2012年11月19日)。
那么,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如表1所示,自2005年以来,包括中科院、原建设部、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社科院等六家机构测算过,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成本从1.5万元到13万元不等。
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金三林和许召元在《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中的估算,这些成本大致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1.非户籍人口随迁子女教育成本;2.医疗保障成本;3.养老保险成本;4.民政部门的其他社会保障支出;5.社会管理费用;6.保障性住房支出。如果以每个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再乘上目前的非户籍人口数量,总支出当然庞大,因为,据国家统计局于2013年5月27日发布的《2012年全国非户籍人口监测调查报告》,我国非户籍人口总数已达26261万。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支出都是当下立即支付,很多是未来几十年内的成本。就像金三林和许召元对媒体解释的那样:“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支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不是需要一次性投入,而是伴随着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短期来看,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是主要支出,远期来看养老保险补贴是主要支出。其中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的支出占总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养老保险补贴约占总成本的40%-50%,但养老保险补贴受养老金支出政策的影响很大。” (《新京报》2013年3月30日)
更需要注意的是,包括医疗保障、养老、住房等支出,绝大多数都是由非户籍人口自己承担或者是由其供职的企业承担,不需要政府额外支出。同时,越来越多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会带来巨额现金流,改善当下城市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支出结构。与年轻的非户籍人口相比,大城市的老龄化挑战已经凸显,在现收现付的养老金体系下,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给城市带来的收益远超过公共服务所需要的成本。
基于这个思路,我们提出一个“以社保换教育”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思路。在目前的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下,对城市居民而言,教育资源被分摊可能是看得见的利益受损,社保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却是隐性的。从政府的财政支出来看,养老金支出的压力才是真正的压力,教育支出则是小问题。但对于外来常住人口而言,社保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子女教育则是当下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样,新老居民和地方政府在这里找到了最大公约数。更需要注意的是,教育经费支出,还可以增加相关就业,对很多大城市而言,由于本地户籍人口减少,很多学校的老师已经有失业的危险。(以上海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2012年上海普通高中的招生数为52497人,高中在校生人数为157709人;但是在1999年,上海高中的招生数为80024人,在校生人数为232828人。短短13年间入学人数减少了近一半。)
之所以选取上海作为样本来讨论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与收益问题,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很有代表性:第一,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上海的常住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1100万变成2013年的2415万,新增加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非户籍人口(根据《2013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3年末,全市常住人口总数为2415.15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25.14万人,外来常住人口990.01万人。2011年5月,上海市统计局负责人曾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上海常住人口近5年的增长可谓迅猛,但上海户籍人口自然增长已连续18年为负增长。”参见《中国经济周刊》2011年第19期);第二,上海作为国内人口最多的城市,非户籍人口在2013年已占常住人口的40%,如果上海非户籍人口市民化不存在巨大成本,那么非户籍人口对其他城市来说就更加不是负担。
(一)为什么2010年到2011年养老金缺口由负变正?
作为国内老年化率最高的城市,上海在2010年前一直存在巨大的社保资金缺口。这从2010年上海分户籍的人口金字塔图可以看出来(见图2)。一个户籍人口按年龄分布呈现“头重脚轻”特点的城市,养老金显然是紧张的,这种紧张程度会随时间的推移,对上海财政产生极大压力。
奇怪的是,从2010年到2011年间,养老金缺口由负变正,年度余额由-103.54亿元变成了211.61亿元(见表2)。在老龄人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为何社保资金年度余额会由负变正?上海社保征缴基本面发生变化是重要原因。正如上海分户籍的人口金字塔图显示的那样,非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刚好是“中间大两头小”,缴纳养老金的劳动年龄人口庞大。
我们观察到,上海市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从2010年到2011年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增加,参保人数由542.87万人猛增为926.93万人(见表2),增长率几乎达到70%。在上海劳动人口没有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参保人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这与上海市政府自2011年7月起实施的社保新政有关。根据该政策,原本强制缴纳的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变成强制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2011年6月下发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外来从业人员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与本市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外来从业人员”,“应当参加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于是,那些本来缴纳综合保险的都变成了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当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缴纳增加人数为384万人,这与2010年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的404万人的数量大致吻合。
从养老金年度余额也可看出,来沪人员综合保险取消,变成强制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之后,尽管离退休人员在持续增加,但社保资金年度余额却由负变正,这与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与上述两种保险缴纳份额不同有关。按照规定,“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每月缴纳数额=上海市城镇职工社会平均工资×60%×10%”,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每月缴纳数额=缴纳基数×30%”。其中,根据2011年上海市社会保险费缴费标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缴纳基数为2338-11688元。
我们首先假设所有来沪就业人员都以法定最低标准缴纳养老金(2338元)。那么,以2011年上海市职工月平均工资4331元来算,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金额为每月260元(保留整数,余数四舍五入,下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每月缴纳金额为701元。按照年来计算,来沪就业人员综合保险金额为3120元,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金额为8412元。这样,每年缴纳的养老金增加了1.7倍。
用以上养老金变化额(8412减去3120)乘以2010年缴纳综合保险人数,即404万人,计算可得214亿元,这一数字大致相当于表2中2011年养老金年度余额相较于上一年度增加额(由-103.54变成+211.61,增加约315亿元)的三分之二。如果用2011年非户籍正规就业人口(449万)来计算,数据会更接近,计算出来的增加额为238亿元。因此可以认为,2010年到2011年养老金缺口的变化,大致可以由上海市强制所有非户籍就业人口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来解释。
综合表2和表3可知,非户籍人口中的就业人口,绝大部分都缴纳上海市规定的养老保险金,从2008年至2010年期间,不缴纳来沪就业人员综合险的只有不到38万人。而在2010年,上海市户籍人口就业人数统计数为660.24万人,其中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42.87万人,这样,不缴纳城镇职工保险的户籍人口有117.37万人,约占户籍就业人口的17.8%。大致估算,强制非户籍人口缴纳养老金之后,上海市养老保险收入中的接近一半是由非户籍人口提供。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简称“六普”)资料,2010年上海外来常住人口(897.7万人)中,20-34岁的青壮年人口为 422.03万人,占外来常住人口的47%;劳动年龄人口(男性15-59岁,女性15-54岁)为783.35万人,占87.3%,与“五普”相比,又上升1.2个百分点(见表4)。普查资料还显示,20-34岁这个年龄段的外来常住人口占当年上海全市常住人口(2301.9万人)的18.3%。也正因如此,这个群体子女的入学问题成为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根据表5的数据,到2012年,非户籍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总入学人数中的占比已达45%。按照官方统计,2012年上海市区县小学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18839.33元,区县初中在校学生人均实际支出24485.17元(参见《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上海市统计局2012年上海市区县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的通报》)。按照该标准,上海2012年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中,小学阶段为14324526532元,初中阶段为10594733059元,两项合计249.20亿元。如果以2012年义务教育阶段非户籍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45%来计算,那么用于非户籍人口的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为112.14亿元。
需要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经费都是按照上海市义务教育生均经费标准执行,因为很多非户籍人口子女并不是在公办学校就读,而是在非户籍人口子弟学校就读。这意味着,这部分非户籍人口子女的教育成本以自己承担为主。尽管近年来上海加大了对非户籍人口子弟学校的补贴,如在2013年政府规定:“各区县应根据招生人数,按每生5000元(不含租赁费)的标准(其中市级承担2000元,区县承担3000元),对经政府委托以招收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民办小学给予基本成本补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对区县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管理的意见》)
换句话说,很多非户籍人口子女所需教育经费并不是按照生均经费享受,那么他们所占经费支出的比例是低于其占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人数比例的。
如果以上的计算正确的话,现在非户籍的常住人口每年为上海贡献的养老保险金数量至少200亿元,但每年其子女所享受的教育经费却只有不到112亿元。这意味着在现有的财政结构下,真正实现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并不会损害原有城市居民的利益。
四、初步结论
我们认为,传统的有关非户籍人口市民化成本的观点存在问题。首先,分不清哪些成本是直接由政府承担,哪些是非户籍人口自己承担;其次,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并不只会带来成本,同时还会带来直接收益。我们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认为非户籍人口承担了和其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不成匹配的负担。同时我们还指出,户籍居民并不会是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受害者,因为非户籍人口缴纳的社会保险远远大于其子女的教育成本。
有鉴于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至少在直接的成本收益层面,对于像上海这样外来人口持续增长的地区已经不存在所谓的“非户籍人口市民化的成本”问题。如果像上海这样非户籍人口接近50%的城市都能够承受,那么外来人口更少的地区就更加没有压力。从这个意义而言,以成本来回应户籍改革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站得住的理由。
(作者傅蔚冈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吴华丽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助理。受见报篇幅限制,编者对原文文献综述有大量简化,并略去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