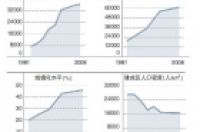政府无法采取果决的措施解决本国的经济增长、就业和分配问题,已成为各国担心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国会僵局和不负责任的哗众取宠获得了大量关注,许多人担心由此造成的经济后果。
但最新一份分析表明,一国在某些方面的相对经济表现与其政府的运转状况基本无关。事实上,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六年来,美国在增长、失业、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方面的表现都胜过其他发达国家,尽管其国内政治两极分化程度创历史新高。
也不能一概而论。德国、加拿大和日本的失业率更低;美国的收入分配也比大部分发达国家更不公平,并且其收入分配不平等还在加剧。不过,从整体经济表现看,美国显然没有为政治功能失调付出沉重代价。
我们并非否认更果断决策的潜在价值,但显然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考察这些因素对许多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一体化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开启了为期数十年的深刻变革。这些国家参与全球经济可贸易部门,正在影响着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此同时,半导体价格的下跌,助长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兴盛,从而取代了劳动力,促使供应链脱媒,并减少了发达经济体可贸易端的常规工作岗位和低附加值工作岗位。
这些都是长期趋势,需要前瞻性评估和长期的应对措施。相对短浅的政策框架在战后早期运转得还不错,当时美国处于主导地位,一群结构类似的发达国家贡献了全球产出的绝大部分。
但当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在行为和结构上适应比较优势和各种人力资本价值的迅速变化时,这套安排就不管用了。
那么,什么能够解释美国经济在危机后相对出色的表现?那就是美国经济结构上的深层灵活性。去杠杆化比其他国家更快,资源和产出快速向可贸易部门倾斜,从而填补了内需持续低迷造成的缺口。
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保护经济部门或就业的措施,从而造成了结构刚性。随着采取结构性变革以维持增长和就业的需要增加,这些政策的代价也在增加。相对而言,德国、北欧、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结构刚性相对较低。
消除结构刚性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些刚性来自社会保障机制,其关注点是就业和经济部门,而不是个体和家庭;其他刚性则反映了仅仅保护经济部门免于竞争并产生经济租金和既得利益的政策。简言之,对改革的抵制可能很大,因为改革的结果具有分配效应。
这类改革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是指市场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以任何方式进行干预。政府在结构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它必须把路让开。
相对美国而言,欧洲有两类问题。一是需要加强结构灵活性并提高生产率,特别是南欧。在欧元诞生的第一个十年,南欧经济体的单位劳动成本与德国、北欧背道而驰,它们的增长要么靠过度公债和总内需中政府部分维持,要么通过举债经营的房地产泡沫维持。在缺少汇率机制的情况下,重构经济体系、让可贸易部门实现增长,必须经历痛苦的相对通缩,而在低通胀环境下,这一过程需要更长时间。
二是欧元区放任这些差异的发展,因为影响增长的政策是分散的。共同货币和货币政策与分散的税收、公共部门投资和社会政策决策间永远存在矛盾,而税收、公共部门投资和社会政策会影响国家的结构灵活性。
光靠结构灵活性是不够的,更高水平的公共部门投资也有助于产生可持续复苏,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但在许多国家,严重的财政约束可能推迟这一政策反应要素,因此,加强灵活性的改革是正确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