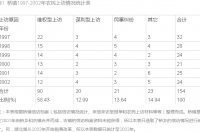——简·伯班克与弗雷德里克·库珀在华东师范大学的讲演
今天,我们为什么仍然要去思考帝国?——我们所知晓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其中。民族国家们在联合国有各自的席位,还有各自的国旗、邮票和政府机构。然而,民族国家是一种起源晚近、有着不确定的未来,并在很多情况下有着破坏性后果的“理想”。一战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罗曼诺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以及二战后,法兰西、不列颠、荷兰、比利时和葡萄牙殖民帝国的去殖民化,其后果并不是民族国家所组成的稳定世界取代了帝国。由于难以找到可行的帝国政体的替代品,在1918、1945和1989年之后,在卢旺达、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阿富汗、前南斯拉夫、斯里兰卡、刚果、高加索、利比亚、叙利亚及许多别的地区,爆发了多次流血和破坏性冲突。大国们宣称这是一个各国互不侵犯、相互平等的世界,然而,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部署会暗中削弱国家的主权。
对帝国的眷恋——对失去的世界,如英属印度或法属印度支那,伤感的招魂术于事无补;同样,对帝国霸权的谩骂——乞灵于用“帝国”或“殖民主义”这种词汇使美国、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干涉失去道义立场,也不能为理解和改善当今世界提供方法。然而,审视帝国演进的道路能够告诉我们为何当今国家呈现出多种形态,也会提醒我们一些在最近几十年被遗忘了的事实:在过去及现在的许多地区,国家主权是一种复杂的存在,其能够被分割、层叠和构建于多种多样的立国原则及实践之上。
我们的这次演讲以简·伯班克教授与我合著的《历史上的帝国》一书内容为基础。我们关注两种帝国演进的轨迹——帝国之路和帝国解体之路,以20世纪的非洲和俄罗斯为例。我们将探查20世纪这两个地区的帝国对政治意象和政治活动家行动的影响,并试图表明,帝国不仅没有消失转变为民族国家,相反,帝国在20世纪乃至21世纪激发了对权力的期望和国家政权形式的多种可能性。我们分析的重点在于“主权转移”和“联邦主义”。这两个概念在20世纪都很活跃,并且都对国家的创建及其公民的生活带来重要影响。不过,我想首先就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作简要分析。
何为帝国?
帝国是一种持久的政体形式。作为宏大的政治实体,帝国奉行领土扩张主义或对扩张念念不忘,以武力或其他手段将人们统合起来,在人群中维持差异性和等级关系。民族国家被想象为同质性的——单一民族、单一领土、单一政府,然而,帝国却意识到并不得不应对其臣民的多样性。帝国以不同的方法治理不同的人群,其多重治理策略使之具有适应性,能够远距离、长时间地控制资源。且不提中华帝国绵延的王朝统治长达2000多年,相比于600年的奥斯曼帝国的长寿,民族国家也不过是历史地平线上的一个光点罢了。如果我们认为单一民族国家是一种通则,其他政体形式是一种违例,那么,我们就忽视了塑造政体和政治行动的真正历史过程。
无论帝国统治者如何看待“其他”人民及其文化,征服者不能仅靠自己去治理帝国。他们需要中间人。帝国统治者经常利用来自被征服社会中的精英的才能、知识和权威——这些人出身于合作者或那些从前处于边缘地位、而意识到为胜利者服务的好处的群体。另一类中间人是那些来自母国的殖民定居者或行政官员。
理论上,20世纪的欧洲帝国本应用官僚机构来取代这种中间人的个人关系网络,然而,这一做法很多流于纸面。在帝国的全部历史中,中间人既必要又危险。殖民定居者、本土精英们、下级官员群体都可能希望称王称霸。
为何1945年时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曾追求过的目标——民族国家,最终在1960年成为法属西非各前殖民地的结局
一种未经检验的习惯说法——最近200年的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变——使得许多学者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1960年法属西非终结于若干个民族国家,而在1945年时没有任何一个重要政治人物寻求过这一结果?直到1958年,几乎所有法属西非的政治领袖们寻求的是联邦:非洲国家之间及其与法国的联邦。
为什么这样一种选择在20世纪中期时对法属西非是可行的?出发点基于他们的帝国经历。法属西非自身是一个复合结构,置身于更大的复合结构——法兰西帝国之中。其由法国在19世纪晚期获得的8个殖民地组成:塞内加尔、毛利塔尼亚、几内亚、苏丹(法属苏丹,今马里)、尼日尔、科特迪瓦、上沃尔特(今布基纳法索)和达荷美(今贝宁)。1895年,法国决定由一位总督对其进行集权统治,驻地达喀尔。
1945年,法兰西帝国改名为法兰西联盟,殖民地改称海外领土。它们是具有典型帝国特征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直到此时,法国统治下的人们有不同的身份:
在欧洲法国,即宗主国,除了外国人,居住于此的人都拥有法国公民身份。
在老殖民地加勒比地区,大部分人口是非洲奴隶的后裔,1848年法国废除了奴隶制并承认前奴隶们为法国公民。
在阿尔及利亚,这片1830年时法国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取的地区,法国宣称将沿用奥斯曼帝国允许不同族群采用自己法律系统的政策。穆斯林因其私事,主要是婚姻和继承,服从于伊斯兰法律而不是法国民法典。他们是“臣民”,被任意处罚,仅有受限的政治发言权,而不是法国公民。
在新殖民地,即19世纪晚期法国在非洲征服的许多新领土,其本土人口的身份类似于阿尔及利亚的穆斯林。
在受保护国,也就是法国强迫其君主签订条约,接管殖民地政府的国家,如摩洛哥、突尼斯、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一部分,维持了国王或君主仍是最高统治者的表象,人民仍保留本国国籍。
另外还有委任统治,后来叫作托管领土的地区。一战后,当国联分配德国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一些省份时,法国在非洲获得了两处托管领土,多哥和喀麦隆。
以上每一类都代表着不同的法律地位。这种不同将会形成它们脱离帝国后的不同道路。1945年时,法国不得不重新思考帝国的整体结构。
* * *
二战对世界范围内的帝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法国也不例外,尤其是在印度支那的大部分最有经济价值的殖民地也被日本所占领。二战结束后,法国的统治者意识到他们已经没有力量仅凭高压统治来恢复帝国。帝国的非洲部分比之从前更重要,而这里的统治需要新的合法性基础,那种白人应当统治黑人的观念不再有意义。那么,法国应当如何对不同类型的海外领土实施合法的权威呢?
1945年10月,法国的“公民们”和“臣民们”分别组成选举院选出代表成立了制宪会议,为新成立的第四共和国制定宪法。法属西非选送了6位黑人代表前往巴黎,他们的主要诉求是法国平等对待殖民地并将公民权扩及法国海外领土的每一个人。在制宪会议上,非洲代表们为这些条款斗争得很激烈。通过联合抵制大会的方式,他们使大多数人意识到,如果宪法在没有得到非洲人的同意下通过,它在海外领土就不会有合法性。
一些改革建议在联邦主义的观念下提出。戴高乐在1946年说道:“在我们的旗帜下生活的1.1亿人民的未来在于一种联邦性质的组织。”而1946年的宪法以妥协结束。大部分权力仍属于巴黎的国民议会,其中非洲人的席位很少。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不过它满足了非洲代表的最低要求:在帝国内普遍授予公民权,同时允许非洲人保留其“个人身份”,也就是在婚姻和继承方面适用伊斯兰法律或传统法律,而不是法国民法典。
1946年的法国真是文化多元和平等的吗?实际上两者都不是。1950年代,非洲的政党一直要求弥补宪法的缺陷:实现普选权、单一选举院、更多的自治权力。同时,非洲的工会还积极争取所有种族的工人享有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尽管道阻且长,这一运动还是取得了主要成果:1952年劳工法。该法将法国工人享有的每周工作40小时、带薪假期、组织工会的权利和其他福利给予了殖民地的全部工资劳动者。
在这一时期的争论中,塞内加尔的两位政治领袖利奥波德·桑戈尔和马马杜·迪亚构建了一个清晰的框架。他们努力将“水平联合”(非洲人彼此之间的关系)和“垂直联合”(保持与法国的关系)结合起来。结束殖民主义就是将帝国转变为联邦国家,其中各海外领土的特性得到承认,在内部事务上自治,同时作为更大的联合体的成员,对其资源如公民一样享有权利。
公民权在帝国范围内赋予人民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二战后的社会背景非常重要:在欧洲,福利国家的概念深入人心,这表明对于国家应当以某种方式保证公民获得养老金、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期望日益上升。因此,在1940年代把数以百万计的贫穷的“臣民”转变为公民意味着高额成本,因为法国的资源和法国的生活标准将是关键的参照物。
非洲的领导人们还必须应对战后具有精神分裂特质的法国殖民主义——时而能够与非洲和亚洲的政治家们冷静讨论,时而残酷镇压被认为“举行起义”的人们。1947年对马达加斯加起义的镇压以及1954-1962年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法国军队对那些被认为包庇了反叛分子的人们滥施暴力,严刑拷打。
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发现他们进退维谷:要么接受公民权的逻辑结果——以法国为标准要求经济和社会权利,这样做代价巨大;要么在国际舆论倾向于反殖民统治的时代里陷入起义和镇压的循环之中。法国政府能够使非洲领导人放弃前一条道路的唯一方法就是给予海外领土更多的自治权力。
1956年,巴黎最终在非洲人要求的普选、单一选举院和海外领土的真正自治等问题上屈服。次年,非洲政党在所有海外领土的选举中获胜并开始行使权力。改革的核心在于这些政府将控制行政事务并为其买单。对工资和福利需求的满足现在是非洲人政府需要考虑并承担的问题了。
* * *
1956年的法律终止了法属西非的集权政府。桑戈尔所说的水平联合的载体——非洲联邦,成为1956-1960年间争论的关键。
1958年戴高乐的新宪法将前殖民地从法兰西联盟中的“海外领土”地位提升到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国家”地位。1958年9月,各海外领土进行公民投票决定是否接受该宪法。从几内亚投票决定脱离法国开始,公投迅即开启了独立之路。直到1950年代晚期,欧洲和法属西非的政治领导人们都试图将法兰西帝国转变为某种形式的联邦或邦联。但法国首先放弃了联邦解决方案:对于非洲人的社会和政治运动,公民权已经被证实是一柄双刃剑。这就是法国在1956年给予各海外领土实质性权力的原因所在。
非洲政治领导人发现自己处于结构性的困境中。选举政治的单位是基于领土的,政治家创建政治机器需适合其选民基础。1956年,各海外领土的第一代领导人们获得了真正的权力——分配资源、政治分肥。毫不奇怪,最富裕的科特迪瓦首先站出来反对西非联邦,然后应者云集。
就这样,当欧洲得到了共同市场时,非洲得到了领土国家。他们获得了主权,除此之外一无所有。牢牢扎根于领土国家,第一代统治者努力掌控资源而不让其落入任何潜在的反对派手中。几乎所有前法属西非的国家都消灭了多党选举,对工会领导人或拉拢或监禁,不让最富生产效率的农业生产者保有足够的资源以挑战现有统治集团。殖民统治结束之后,非洲团结的梦想并未实现。这些国家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分肥以及不断发展的非洲精英与法国统治者之间的依附关系。就这样,1945年时双方都不曾追求过的目标——民族国家,最终在1960年成为法属西非各前殖民地的结局。
为何两次政权更迭都没有促使俄罗斯大多数民族集团走向完全独立
我想以喀山地区,今天的鞑靼斯坦共和国为例,探讨俄罗斯帝国的演进轨迹。我将聚焦于20世纪俄罗斯两个主权变更的特殊时期,1917年和1991年之后。我们会看到,帝国传统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的政治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在这两个时期,俄罗斯崩溃了,但并没有导致民族国家的产生,相反,产生了一种联邦主义,主权在各组成单元之间分配,复杂而异质的政体结构得以保留。这种“基于差异的统一”的结果来源于一种附属主权的长期历史经历。帝国经历产生了有关臣民和统治者各自责任的特定观念,以及在持续的政治激进主义、冲突的灵活解决方案和统治权的转移背后的行动机制。
喀山地区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附属于数个更大的政体,其民族和宗教极富多样性。我们在喀山、在苏联、在俄罗斯联邦所见的是源自于“欧亚主权政治制度”的政治权力的各种概念和实践,这一制度数个世纪以来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持续塑造着各种政治结构。
1552年,喀山被伊凡四世征服并入俄国。在此之前,喀山500多年的历史里,政治运作的主要特征有六个:1.统治者必须和中间人合作,如市议会、部落领袖和宗教权威;2.持续的统治需善于借用外部势力,例如与那些拥有军队表示忠诚的领袖们结盟;3.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希望臣民们不会是“相同的”,他们的身份归属于种族、部落或其他集团,有不同的宗教和文化习俗;4.君主(经常出身于外族,甚至信仰不同)被认为应当统治这些集团,在他们之间保持和平、尊重差异、化解冲突;5.在政治体系中,通过被授权的代表统治人民的垂直体系必不可少。地方精英与帝国统治者的合作能使其大获其利,但地位很不稳定;6.这种个人化、灵活的代表结构促进了机构和统治的多变、适应性和活力。
1552年俄国人统治喀山之后因循成规,不过沙皇取代了可汗成为最高统治者。在19世纪时,喀山成为了鞑靼文化的中心。20世纪初期,喀山的帝国传统建立于王朝统治以及省和地方层面的官僚体系的基础之上,依靠精英们的灵活治理,以法律保护多元种族和宗教文化信条。政治与被统治者无关。
* * *
最初,联邦式的国家组织并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目标。但1917年后,面对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要求独立、白军在“自由”芬兰大胜、前帝国解体、大部分国土被敌军占领的局势,列宁重新考虑了联邦主义的可能性,作为将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和人民再次统一起来的手段。
由列宁起草的《劳苦大众和被剥削阶级的权利宣言》于1918年1月3日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第一次正式申明了联邦原则:“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将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自由联盟的基础上,是由各苏维埃共和国组成的联邦。”不过,那年冬天还有另一个宣称代表俄国的机构:制宪会议。制宪会议宣布“俄罗斯民主联邦共和国由人民和各地区组成不可分裂的联盟,最高权力受联邦宪法限制”。
事实上,这两种形式的联邦主义有显著的共同点,尤其是两者都以中央政府领导附属单位的垂直结构的方式重建俄国,体现了帝国传统的影响。尽管两者都将中央权威置于地区之上,但对中央和地区、地区与地区之间权力界限的划分仍留有博弈空间。1918年的这些基础性文献表明,国家主权既是联邦性质的,又是可调整的。
1917年的鞑靼地区,政治活动家为建国原则的问题——根据民族的、区域的还是文化的原则来组织国家,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如鞑靼与巴什基尔的关系问题,争执不下。不同的联邦形式都被提出——伏尔加鞑靼人自治领、联邦内独立穆斯林国、与其他共和国结盟的伏尔加-乌拉尔共和国。不过,当布尔什维克党于1918年1月宣布在喀山进行军管时,这些设想都嘎然而止了。在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下,1918年3月成立了鞑靼-巴什基尔共和国。1920年5月又成立了鞑靼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喀山为首都。当苏联成立时,其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
* * *
在俄罗斯政治制度重构的紧要关头,所有的重要角色都以联邦主义为指导思想。主权被认为是可以被分割的;权力是可以被代表的;在个体或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等是不存在的。1917年之后,这种复杂的政体结构从未稳定过。权力、边界和政策,包括那些有关种族和宗教问题的政策,被持续重新界定。
戈尔巴乔夫“重构”苏联的尝试迅速演变为重写规则的政治运动;叶利钦1990年8月在喀山国立大学发表申明,鼓励政治家们“尽力夺取主权”。这种诉诸联邦主义的最明显的例子是1991年12月独联体的成立。
另一种类型的联邦重构是在俄罗斯联邦内部进行的。1990年8月30日,鞑靼自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成立主权国家——鞑靼斯坦共和国。巩固这一主权有两种方法,其一是全民公投;其二是与俄罗斯联邦的“双边协定”。在实际中,则采用了双管齐下的方法。个人化政治、规则的持续博弈和最高统治者的个性再次发挥了作用。1992年3月21日的公投中,61.4%的投票者赞同鞑靼共和国成为主权国家。这也足以授权鞑靼的政治家们寻求第二种方法,在俄罗斯联邦重建初期的动荡岁月中,强硬地捍卫其共和国的很多权利,以司法途径解决鞑靼共和国的独立问题。他们拒绝了俄罗斯联邦1993年的宪法草案。1994年双方达成协议,鞑靼共和国在文化、经济和行政政策上享有统治权,能够与俄罗斯联邦其他地区以及外国签订协议。
普京上台后,在主权争夺中,莫斯科开始占上风。如其漫长的历史传统一样,争夺主权的双方都没有打出种族或宗教的旗帜。2002年,俄罗斯联邦议会批准了《鞑靼斯坦共和国宪法的修正和补充》。鞑靼斯坦人是“俄罗斯联邦鞑靼斯坦共和国的公民”。2003年之后,鞑靼斯坦是俄罗斯联邦中唯一一个其国家地位不是由俄罗斯联邦宪法而是由双边协议来确定的成员国。2007年,经过双方几轮激烈协商,鞑靼斯坦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个条约被批准,1994年协议所授予的许多文化和政治权利得到保留。
持续进行的、多变的、从法律上对可分割权力的重新分配在帝国体制和苏维埃体制下都是俄国统治的支柱。当普京声称总统权力高于州长和市长时,他能够与可预测的、训练有素的中间人签订条约,而不受统一性的限制,并避免难以预料的俄罗斯杜马中的争论。
简·伯班克(Jane Burbank)
纽约大学历史系俄罗斯和斯拉夫研究教授,研究领域为俄罗斯历史、法律文化、帝国与农民等。著有《知识界与革命》(Intelligentsia and Revolutionn:Russian Views of Bolshevism,1917-1922)、《俄罗斯农民上法庭》(Russian Peasants Go to Court:LegalCulture in the Countryside,1905-1917)等。她与库珀合著的《历史上的帝国》(Empiresin World History:PowerandthePoliticsofDifference)获得2011年世界历史协会图书奖。
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非洲、世界历史上的帝国、殖民化与去殖民化等。
著有《去殖民化与非洲社会》(Decolonization and African Society:TheLabor Question in French andBritish Africa)、《存疑的殖民主义》(Colonialism in Question:Theory,Knowledge,History)等。库珀教授2001年入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