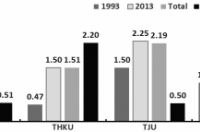五年前,当欧元危机爆发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预测强加给希腊和其他危机国的紧缩措施将以失败告终。紧缩将扼杀增长、增加失业——甚至无法降低债务-GDP比率。其他人——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一些大学中的人——大谈扩张性收缩(expansionary contractions)。但即使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指出,收缩——比如政府支出的缩减——只能是收缩性的。
我们不需要其他验证了。紧缩一再失败,从美国总统胡佛的早期尝试(将股市崩盘变成了大萧条),到近几十年来IMF给东亚和拉美制定的“计划”莫不如此。而当希腊陷入麻烦时,我们又一次祭出了紧缩。
希腊在遵循“三驾马车”(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IMF)所制定的政策方面相当成功:其初级预算已从赤字转为盈余。但政府支出的收缩不出意料地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失业率高达25%,GDP从2009年以来减少22%,债务-GDP比率增加35%。而如今,随着反紧缩的左翼联盟(Syriza)在大选中赢得压倒性胜利,希腊选民终于表示他们受够了。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需要搞清楚,如果它是唯一一个三级马车的药方遭遇惨败的国家,那么它的麻烦完全是咎由自取。但西班牙在危机前存在盈余和低债务比率,而如今它也陷入了萧条。现在,与其说需要在希腊和西班牙内部采取结构改革,不如说欧元区的设计需要结构改革,并且还需要反思导致这一货币联盟表现如此拙劣的政策框架。
希腊也再次提醒我们有多么需要债务重组框架。过度负债不但导致了2008年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亚危机和80年代的拉美危机也是拜过度负债所赐。过度负债还在继续造成美国难以名状的痛苦,数百万屋主失去了房子,而数百万波兰和其他国家背负着瑞士法郎贷款的人目前也是危如累卵。
过度负债呆滞的痛苦是如此巨大,我们应该好好问问为何个人和国家一再放任自己陷入这一局面。毕竟,这些债务都是契约——也就是说,是自愿签订的协议——因此债权人的责任并不小于与债务人。事实上,债权人理应承担更大的责任:通常它们是成熟的金融机构,而借款人常常不太适应市场的变幻莫测以及与不同契约安排有关的风险。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银行实际上在利用借款人缺乏金融知识而掠夺他们。
所有(发达)国家都认识到,让资本主义正常运转需要能够让个人重新开始。十九世纪的债务人监狱是一场失败——既不人道,也没有帮助确保偿还。确实有帮助的是通过让债权人为它们的决定的后果承担更大责任来提供优质贷款的激励。
在国际层面,我们尚未建立让国家重新开始的有序过程。2008年前,联合国在几乎所有发展中和新兴国家的支持下,已经开始寻求建立这一框架。但美国一直顽固反对;也许它是想给债务国官员重建债务人监狱(果真如此的话,大概会建在关塔那摩吧)。
重建债务人监狱的思想也许有些牵强附会,但它与目前关于道德风险和问责的讨论异曲同工。有人担心,如果允许希腊重组其债务,它将再一次陷入麻烦,其他国家亦然。
这纯熟无稽之谈。如果你脑子正常过,你认为会有国家愿意让自己走希腊的老路,只是为了从债权人那里获得免费的午餐?如果存在道德风险,也是在反复得到援助的贷款人这一侧——特别是私人部门。如果欧洲允许这些债务从私人部门转移到公共部门——过去半个世纪都是这么做的——那么是欧洲而不是希腊应该承受后果。事实上,希腊目前的窘境,包括债务比率的大幅上升,主要是三驾马车对它试驾了错误的措施导致的。
因此,不是债务重组,而是缺少债务重组,才是“不道德”的。目前希腊所面临的困境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许多国家都面临过类似的情景。让希腊问题更加难以解决的是欧元区的结构:货币联盟意味着成员国无法通过贬值摆脱困境,补偿这一政策灵活度损失只需要些许欧洲团结精神,但这一精神却不存在。
七十年前,二战刚刚结束时,盟国认识到德国需要被允许重新开始。它们明白,希特勒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与一战结束时向德国施加更多债务所导致的失业(而不是通胀)有关。盟国没有考虑导致债务累积的愚蠢政策,也没有讨论德国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多大的代价。相反,它们不但豁免了债务;事实上还提供了援助,驻扎在德国的盟军提供了进一步的财政刺激。
当公司破产时,债务-股本交换是一个公平高效的解决方案。希腊也可以采取类似办法:将其现有债券转换为GDP挂钩债券。如果希腊表现出色,其债权人可以获得更多的钱;否则只能获得更少的钱。这样,双方都有追求亲增长政策的强大激励。
民主选举很少能像希腊的例子那样给出如此明确的信号。如果欧洲对希腊选民改变政策的要求说“不”,就无异于表示民主毫无重要性可言,至少在经济上毫无重要性。为何不干脆取消民主,就像纽芬兰在二战前进入破产接管时所作的一样?
我们希望理解债务和紧缩经济学,并且相信民主和人道价值的人能够胜出。是否会如此,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