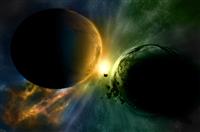县域经济是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解决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键。金融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县域经济需要县域金融提供资金聚集、价格发现、风险管理和成本管理,以实现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提升县域经济增长的活力。
在过去近30年的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我国金融业形成了中央金融高度垄断、地方正规金融高度压抑、民间金融高度脆弱的发展格局,而县域金融改革始终遵循了外生供给型的发展路径。这种外生供给型金融制度安排必然导致基层金融机构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监管能力等方面存在严重不足,造成内生需求型县域金融高度压抑,难以满足县域经济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风险控制优先的金融监管压制了县域经济内生型金融需求。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对非公经济认识的突破,农村合作基金、钱庄、典当、抬会、排会等民间金融形式先后恢复出现,为非公经济发展提供多样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1984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指出:“允许农民和集体的资金自由地或有组织地流动,不受地域限制。”1996年年底,全国已有2.1万个乡级和2.4万个村级农村合作基金会,融资规模大约为1500亿元。(温铁军:“三农合作基金会的兴衰史”,《中国改革》,2008年第8期)由于农村合作基金开始向非会员以外区域扩张,资金出现非农化现象,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基于对金融风险控制考虑,通过强制性手段关闭各种民间金融机构。1998年,国务院发布《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取缔了一系列游离于正规体制之外的金融机构,私人钱庄逐渐地下化。1999年,国务院发布3号文件,正式宣布全国统一取缔农村合作基金会。2002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再次颁布《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专门取缔农村地区高利借贷现象突出的私人钱庄。
中央金融监管部门再次禁止农村民间金融的发展,这实际上主要是由于我国高度集中、高度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所造成,而地方政府没有任何金融管理权限。中央金融监管部门主要对垄断金融机构实施监管,由于垄断金融机构主要分布在地(市)以上城市以及经济比较发达地区,这就造成中央金融监管部门重心上移、上行,主要集中分布在中央、省(市)、地(市)三级行政区,而县级及其以下行政区普遍成为金融监管弱化空白区域。在农村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面对数量众多、监管成本较大的基层民间金融机构,中央金融管理部门由于监管链条过长,受到农村金融监管信息、监管成本等方面制约,很难对农村基层金融发展实施有效监管。在金融风险控制与金融发展二重博弈中,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坚持了风险控制优先的原则,片面忽视了县域经济发展内生性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强制性行政干预禁止、取缔各种民间金融活动,导致各种民间金融只能转入地下,走向灰色发展,间接成为影子银行、地下银行。2006年以来,我国对民间金融发展限制有所放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和小贷公司,但同样遵循了风险控制优先的监管原则,对民间投资市场准入设立了严格限制条件。我国农村地区新型金融机构发展比较缓慢,截至2012年6月,全国成立村镇银行共有1101家(冯娜娜:“村镇银行几何级数扩
张,国家贫困县却鲜有分布”,21世纪网,http://news.10jqka.com.cn,2012年),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人民网:央行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5267家, http://finance.people.com.cn,2012),并且主要分布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对于全国37334个乡镇金融需求无异于杯水车薪。结果,为了控制风险,宁肯不发展,为了金融安全,宁愿不允许发展县域、农村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所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也是极端残酷的。
姓“国”姓“民”体制障碍束缚了县域民间金融发展。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并不具备农业现代化生产条件,传统小农经济占据主导地位,需要小额、分散、灵活的金融服务。土地是农民的主要资产,但农民只有土地经营权,没有土地所有权,这种制度安排限制了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同时也不能以土地经营权担保向外来正规金融机构获得信贷支持。相比之下,建立在血缘、地缘基础之上的各种民间金融,是一种基于借款人私人信息的一种无抵押、无担保的小额信用融资,较好满足了农村地区差异化金融服务需求,消除了借贷双方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起的信贷配给,民间金融因此成为我国县域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80至90年代,民间金融为三农经济、乡镇企业提供了大量金融服务,对县域正规金融发展形成较大竞争压力和冲击力。但是基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所形成的认识,难以突破姓“公”姓“私”、姓“国”姓“民”的思想束缚以及考虑到风险因素,金融管理部门严格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在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国际化背景下,我国民间金融却不能真正地享受国民待遇,实现阳光化、透明化经营,而县域正规金融形成高度金融压抑,难以满足县域经济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服务需求,这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分业垂直体制导致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一直以来遵循机构改革范式,四大国有专业银行先后从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独立出来,并通过分支式组织结构在全国各县市形成基层金融服务体系。分支式组织结构较快解决了县域金融服务主体缺乏问题,但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进,商业化经营逐渐成为国有银行的主要追求目标。在利润最大化驱动下,四大国有银行分支式组织结构为县域信用资金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提供了便利,导致贴近基层、贴近三农和贴近项目信用资金普遍缺乏,加剧了县域金融资源稀缺。
30年金融体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银行经历了金融垄断到金融市场化、国际化改革的路径。但从总体上看,主要是进行横断层面的改革,并没有在纵向层面进行放权让利。无论是商业性或者管理性金融机构都是垂直型分支式的组织结构,不受地方政府管辖,只对上级行负责,造成了县域正规金融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利润最大化和监管风险最小化双重驱动下,必然导致县域金融脱离县域经济发展,县级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很难获得特色化、差异化的金融支持,严重剥夺了县域金融对实体经济配置的活力。
农村信用社准国有化制度安排导致脱农进城趋势。1979年,中央政府决定恢复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地位,办理三农各项金融业务,执行国家金融部门的职能任务,县联社归农业银行管理。农村信用合作社已经不是农民自愿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而是大部分出资来自国家,农民出资只占很少部分的准国有银行,已经失去了基层农户合作的性质,是中央政府推动的自上而下的外来型金融组织。这实际上限制了民间资本进入正规金融合作服务领域,压制了民间金融的发展。
2003年,国务院进行以产权制度和管理体制为核心的信用社改革,推动农村信用社组建成为省级联社、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把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权移交给省政府,退出对信用联社的管理。省政府成为农村信用社出资人,成立省联社对全省农村信用社实施有效管理。省联社作为独立法人县联社的联合体,其产权属于省级政府,通过统一的人事制度、财务制度和信用资金计划对县联社实施管理和控制。县联社彻底失去了名义上合作性质独立法人地位,间接成为省联社下属准分支机构,成为三农资金向地级市和省会城市集中的抽水机。省联社的行政管理职能进一步强化,而三农服务职能进一步弱化,这与县域和三农金融服务体系强化与创新趋势不相一致。
外生型三农金融服务难以平衡商业性与政策性。我国三农金融体制改革始终没有跳出外来机构范式这一模式,即:重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存在,而不重视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持与服务。农业发展银行作为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银行,主要任务是落实好国家宏观调控和强农惠农政策,具有很浓的计划经济色彩,并不对三农经济提供小额、分散的金融服务。农业银行作为服务三农经济的商业性银行,2007年,中央对农业银行确立了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改革原则,要求农业银行强化三农市场定位和责任。2009年,中国银监会要求农业银行建立适应三农金融服务的事业部管理机制。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要求农业银行稳步推进三农金融事业部制改革。农业银行商业化经营与中央金融管理部门三农金融服务行政化目标相冲突,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并没有强化对三农金融服务的支持,而是对大部分乡镇营业网点进行大规模撤并,造成三农金融服务主体缺失加剧。邮政储蓄银行主要对三农地区提供汇兑业务,只提供有限的农业贷款。农村信用社作为一个商业化运作金融机构,既要承担国家政策性农贷制度的职能,又要实行市场化运营,始终游离于政策性与商业性之间。
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都是从外部降临在县域和三农的金融组织,这种外来金融机构与当地县域经济并无多大联系,难以对三农经济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王军:《县域经济创新发展的体制支撑》,人民出版
社2011年版,第264—265页),结果造成县域金融与县域经济发展错位、错配,难以支撑县域经济发展。我国县域金融薄弱的现实状况既需要商业性金融机构提供资源配置,也需要政策性金融机构对县域经济进行培育和开发,弥补市场失灵,推动市场制度建设。外生供给型金融机构支农惠农政策大多数是基于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而不是通过长期农业发展战略促进三农经济开发,这意味着很难在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之间寻求到平衡点,国家出台的三农金融政策难以贯彻落实,形同虚设。三农金融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只能是三农金融服务主体再一次出现供给性抑制,县域正规金融出现高度压抑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