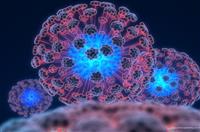在大量的主流公共财政文献中,征税权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征税限制的传统研究很少将这些限制与国家能力联系在一起,而是主要聚焦于激励约束机制带来的限制,而激励约束机制与信息不对称或者政治及政治制度有关。但是,仅激励约束机制并不能解释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税收水平的巨大差异。低收入国家的税收一般占GDP的10%-20%,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在40%左右。
从本质上讲,我们对这些特征的看法和100年前约瑟夫·熊彼特的观点类似。他指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财政史首先是整个国家或民族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国家命运的巨大影响源自国家运行必需的经济血液(税收),以及对其(税收)运用所带来的结果。”为了充分理解税收、经济发展以及这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需要考虑驱动发展进程的动力。贫穷国家因为某些特定的原因而贫穷,同时这些原因也有助于解释它们在增加税收方面的软弱无能。
我们首先分析税收占GDP份额如何随一国人均收入和税基宽度的变化而变化。我们就一国税收占GDP份额的决定因素,构建了一个基准模型。和许多经济学基准模型一样,该模型很有用,不是因为它能直接应用于真实的世界,而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系统地思考能从模型中得出哪些有意义的东西。然后我们回到最初的焦点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税收那么少?我们先考察与这些经济体的经济结构相关的因素,但是我们认为政治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脆弱的制度、支离破碎的政体以及由于新闻媒体软弱而导致的信息透明度缺乏。另外,社会和文化因素,比如国家认同感弱、缺乏对规范的遵从,也可能遏制税收的征集。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建议采用一种动态的研究方法,来考察这些政治、社会、文化因素和经济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
当然,对低收入国家税收的研究也让我们了解了促使税收水平高低的一般性动力,但并不止于此。税收权的演进不仅对国家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很关键,而且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服务和支撑市场经济的能力也至关重要。另外,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往往携手同行,因为参与式政治体制的公民要求对不断增加的公共资源进行合理管理。因此,征税权远不止于增加税收,它是国家发展的核心。(①非经济学家关于税收和经济发展的讨论经常关注这一主题(比如,Br.utigam、Fjeldstad and Moore,2008;Levi,1988)。)
经验性特征
现有的一些事实材料有助于开启我们的讨论。我们将通篇考虑国家层面的税收,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层面的税收。图1根据米切尔(Mitchell,2007)的研究数据绘制而成,显示了税收水平和结构(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在20世纪的18个样本国家(②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丹麦、芬兰、爱尔兰、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中是如何演变的。对于其中的15个国家而言,图1还显示了从工资中直接扣缴所得税的情况,这是利用企业征集税收从而提升所得税的一项重要技术创新。
图中阴影部分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数据,这些数据显示了政府扩张的一般性趋势。可以说,20世纪见证了历史上国家能力最大幅度的扩张,至少在增加税收能力方面。图1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每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都会大幅增加;还有一个显著之处在于,“二战”期间采取直接扣缴所得税的国家数量翻了一番。财政社会学一直认为战争在增强财政能力方面很重要,特别是辛兹(Hintze,1906)和梯利 (Tilly,1990)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
注:图1显示了20世纪18个样本国家中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和所得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是如何演变的。对这些样本国家,我们从理论上假定可以进行跨国和跨时期的比较。我们给出了18个国家未加权的平均数。数据中包括了直接扣缴所得税的情况,其中,芬兰、新西兰和挪威的数据缺失。阴影部分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数据。我们只考虑国家层面的税收,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税收。
资料来源:根据Mitchell(2007)的研究数据绘制
注释和资料来源:图2描绘了税收占GDP的份额(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2005)与人均GDP对数(来自Penn World Table)的关系,都是2000年左右的数据。处于右下角的三个离散值是石油国家巴林、科威特和阿曼。
图2提供了一个进一步观察税收份额和人均GDP之间关系的窗口。它描绘了总税收占GDP的份额(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2005)和人均GDP(来自Penn World Table)的关系,都是2000年左右的数据。根据收入水平,样本国家被分为三组。根据图中显示,税收份额和收入呈现正相关。处于图中右下角的三个离散值是石油国家巴林、科威特和阿曼。
图3描绘了18个样本国家在整个20世纪不同时期 5年移动平均税收份额(来源于Mitchell,2007)和国民收入(来源于Maddison,2001)的关系。这里,不同时期的观察值不同。图中显示,横截面和时间序列显示的趋势相似。今天高收入国家的税收要比低收入国家的税收高,同时今天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的份额和发达国家一个世纪前的情况非常相似。
资料来源和注释:和图1中的18个样本国家一样,图3描绘了20世纪税收份额5年平均数和国民收入的对照情况。这里,不同时期的观察值不同。
图1 和图3显示了财政史的演变路径,这有助于说明图2中当前国家的情况。许多文献都阐释了随着时间推移政府不断扩张的趋势,但实际上在低税收国家中,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走向繁荣。尽管和其他高收入国家相比,美国和瑞士在一定程度上税收水平要低一些,但和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是高不少。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期走过的路也差不多,都伴随着国家权力和征税能力的扩张。我们认为这种发展路径对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增长以及支撑市场经济和提供非市场产品的国家能力的成长具有重要的启示。这并不是说大政府(一个花掉公民三分之一甚至更多收入的政府)就一定好。但是,我们认为,创建必要的制度来支持和维护市场经济,不仅能使公民受益,也会带来寻求高水平税收的激励。实际上,高税收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
我们也可以考察税收形式的结构性差异。贸易税和所得税代表着对行政管理能力的两种极端要求。征收贸易税只需观察边境的贸易流动情况,但征收所得税则需要一个包括监测、执行和遵从等内容的更为复杂的系统。说明这种差别的一种方式是观察任何税收水平下,贸易税和所得税分别占财政收入的份额。下面两个图描述了这种差异:图4是2000年的横截面数据,图5是20世纪的时间序列数据(资料来源同图2和图3)。在这两个图中,我们把
所得税的份额作为纵轴,贸易税的份额作为横轴。从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两种税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同时分别与整个收入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更多地依赖于所得税,很少采用贸易税的形式。而中等收入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更多地采用贸易税。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大量和收入无关的异质性。图5表明从贸易税转向所得税是税收历史上的显著特征。当和图2、图3比较时,我们发现图4和图5中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显示出相似的特征。
图4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所得税与贸易税的情况
注:该图描绘了2000年分别在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中所得税占GDP份额和贸易税占GDP份额的情况。
资料来源:Baunsgaard and Keen (2005) 以及Penn World Tables
图6用另一种方法说明了为什么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低收入国家有着不同和较窄的税基:它描绘了1990年代67个样本国家最高法定所得税率(Gordon and Lee,2005)与所得税占GDP份额的情况(Baunsgaard and Keen,2005)。图中显示,不同组国家之间的最高法定所得税率(纵轴)大致相同,表明不同的税收收入(横轴)主要取决于不同的税基。该图表明,拓宽税基而不是改变税率,才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增加税收收入的关键。
图520个时间段内18个样本国家的所得税占比和贸易税占比
注:对于图1中的18个样本国家而言,该图描绘了全球所得税在世界总收入中的份额(纵轴)和贸易税在世界总收入中份额(横轴)的5年平均值的对比情况。
资料来源:同图2和图3
注释和资料来源:图6描绘了1990年代67个样本国家的最高法定所得税率(Gordon and Lee,2005)和1999年不同收入国家的所得税占GDP比重(Baunsgaard and Keen,2005)。
表1对因变量“税收占GDP份额”的描述性回归
注释和资料来源:因变量为税收占GDP的份额。“高收入”为虚拟变量:当一国在2000年时人均收入处于前三分之一时,它取值为1;“低收入”也是虚拟变量,当一国收入处于底部三分之一时,取值为1。战争的平均年数是自1816年(或者独立日)到2000年间发生外部战争的年份所占的比例,采用战争相关数据库中的国内战争和国家间战争这两种办法进行测量。民族分裂来自Fearon(2003)的研究。行政制约测量了自1800年(或者独立日)到2000年之间的平均值。腐败指数是对2006年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中每国所有得分进行标准化后的值(0代表着高腐败,1代表着低腐败),用标准差来划分。产权保护指数用1997年国际风险指南7分制来衡量。括号中是稳健标准差。*,**和 *** 分别代表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这些粗线条的数据比较展示了一些有用的共同特征,但也展示了大量的异质性,这表明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们将对这种共同性和异质性做进一步分析。为了开展这一讨论,我们通过对横截面数据的回归分析,提炼出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经验规律。这些回归分析有助于描述性分析,但对因果关系分析没有多大意义。原因一方面在于聚类问题,也就是说,在某一方面做得好的国家往往在其他方面也做得很好;另一方面在于变量问题,有些变量可能被认为是“控制”变量,但实际上影响了最终结果的决定。尽管如此,观察这些数据仍然是一个有益的开端,同时提供了一些有助于思考因果机制的指南。
在表1中,因变量是税收占GDP的份额。第1列以不同方式再现了图2中的核心发现。它显示,就税收占GDP的份额而言,那些在全球收入分布中处于前三分之一的国家要比处于中间三分之一的国家平均高13个百分点,而比低收入国家要高17.5个百分点。
在第2列中,我们主要考察一个历史变量和一个社会文化变量。历史变量是战争年份在一国历史中所占的年份比例[用战争相关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 database)记录的开始年份或者国家定义的独立日]。我们发现过去的战争和税收之间呈正相关。社会文化变量是来自费伦(Fearon,2003)的民族分裂。民族构成越多,税收越低。
第3列显示了与表示政治制度的常用指标即行政制约(来自Polity IV数据库)的相关性。当我们测算一个国家自进入数据库或者独立以来行政制约的历史平均值时,我们发现它和税收份额有着显著的正相关性。
第4列探讨了衡量政府有效性的两个指标:透明国际腐败认知指数,值越低意味着腐败程度越高,值越高意味着腐败程度越低;以及用国际国家风险指南衡量的产权保护指标。这两个指标都和税收收入有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存在一些决定政府有效性的共同因素。
最后,在第5列中,我们同时考察了所有变量。此时,人均收入变量变得不再显著,但是与行政制约和产权保护的相关性仍然很强。当然,在解释数据特征方面,这并不是要赋予这种强相关性任何特殊地位,而且这种有条件的收入相关性并不能排除反向因果关系的存在或者某些关键因素的共同决定作用。理解这些发现,需要对导致这些变量间相互作用的经济和政治机制进行讨论。
一个基准模型
为了思考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税收这么低,我们从一个简单的基准模型入手。假定政策制定由一小群公民控制。这些在位集团拥有一系列税收工具来提高财政收入,用于转移支付项目或者提供商品和服务。于是,我们预期税收将被提高到某个点,在这个点上,统治集团增加更多税收用于政府开支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增加更多税收带来的边际成本,而边际成本取决于税基的弹性。税基的弹性包括导致净损失的标准因素,以及避税和逃税产生的漏损效应。
这方面最著名的模型来自梅尔泽和理查德(Meltzer and Richards,1981)的开创性论文[也可以参见Romer(1975)和Roberts(1977)的前沿论文]。这些作者假定增加税收的动力是再分配(唯一的税基是收入,没有逃税和避税问题)并且由中位选民控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的边际收益取决于平均收入(决定了财政收入在多大程度上随税收增加而增加)和中位收入(决定了在提高税收时,作为核心集团的选民失去收入的比率)之间的差异。边际成本取决于总的劳动力供给弹性,这是净损失的唯一来源。在这种背景下,不平等程度更大的国家(用中位收入和平均收入之间的差距来定义)收税将会更多。
使用基准模型的意义在于,澄清产生某种结果所隐含的具体假设条件,帮助我们系统地思考这些假设条件是否真正适用或者需要进一步的修正。举例而言,在思考美国政府的规模方面,这一基准模型是不是有意义的出发点,还非常值得商榷。美国中位家庭收入在5万美元左右,平均收入在7万美元左右,在这种情况下,由税收再分配和中位选民驱动的模型表明,美国税收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应该是高收入国家中最高的,而不是最低的。因此,尽管税收的再分配动机仍然很重要,但似乎还需要一个更加复杂的方法来理解这种动机的影响。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研究框架中的核心假定甚至存在更多的问题。首先,政策制定可能并不代表中位选民的利益,尤其是很多低收入国家压根儿就没有民主制度。第二,出于政治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再分配可能并不是将资源从富裕人群转移到低收入人群或者中产阶级,资源可能会被转移到关键的政治集团手中,而这些人实际上并不是最低收入人群。第三,如果不考虑税收的非再分配动力--特别是优先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开支--可能会扭曲这一模型的结果。第四,正如之前提到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相对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第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逃税和避税的活动空间是关键因素。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说明这五个问题提供了理解发展中国家低税收的一种方法。
在发展中国家掌权的动力远远超过税收决策的能力。另外,统治集团很少受到制衡机制的约束,有极大的自由度和方法去扩展自己或者亲信的权力。事实上,建立在税收再分配基础上的发达国家的政治类型要比在典型的低税收环境下政府干预类型的破坏力低得多。这从指标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如产权保护和税收呈正相关,腐败程度和税收呈负相关。财政再分配的真义在于它提倡一个相对公开的过程,在该过程中,实行的是法治,同时政策不是选择性适用或任意适用。
最后,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的框架本质上是静态的,它建立在给定的税收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之上。相反,正如前面提到的,熊彼特的观点则强调税收嵌入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制度之中,并且与它们相互作用。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些制度机制。
经济结构
低收入国家一般都有一个很大的非正规部门和许多小规模的企业。这些国家也极有可能依赖于少数自然资源或大宗商品并接受外国援助。这一系列因素经常促使低收入国家实行低水平的税收和窄税基。
非正规和小规模的公司
贫穷经济体中,对大规模非正规部门很难征税(La Porta and Shleifer,2014,他们讨论了非正规部门有着强烈的避税动机)。考虑到小规模非正规企业的数量优势,例如发展中国家到处可见的街边小贩或者村里的商店,这些非正规企业及其业主的收入很难衡量,在缺乏正规交易记录的情况下,对他们的交易进行征税基本上也不太可能。从跨国分析来看,非正规部门的规模和税收收入有着强烈的负相关关系。图7说明了这一点,它显示了非正规经济的规模(Schneider,2002)与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比重(Baunsgaard and Keen,2005)之间的对比关系,两个变量数据都来源于2000年左右以来的75个国家。
图7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与非正规经济规模的关系
注释和资料来源:图7比较了非正规经济的规模与所得税占总税收收入比重之间的关系,两个变量的资料来源为2000年以来的75个国家的数据。
拥有大量的非正规部门使拓宽税基变得不大可能。它也意味着和税收水平相关的应税收入的弹性要比其他国家高,也就是说,当一个拥有大规模非正规部门的国家的政府试图增加税收时,报告给政府的应税收入实质上可能会下降。
因此,扩大正规部门的规模是一国发展过程中增加税收的关键。尽管随着经济增长,非正规部门的相对规模会逐步萎缩,但经济增长不会自动导致更多的正规部门,因为政府行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逐步构建一个功能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增强企业在正规经济下运作的吸引力,并且如果这些企业希望受益于正式的法律体系,它们就不能避税或逃税。另外,信用体系的建立、旨在保护产权的土地登记和合同的有效执行会将经济活动纳入税收当局的视野范围。这一点在地籍调查(表明所有权和土地的价值)中特别明显,地
籍调查开始也是出于税收目的。例如,现代瑞典的地籍调查可以追溯到1530年,当时的国王古斯塔夫·瓦萨为了征税引入了这一手段。斯科特(Scott,1998)强调了土地确权在欧洲税收史上的重要性。
非正规企业一般都比较小:在不依赖正式法律体系的前提下,它很难发挥出规模经济的优势,难以出口或者成为大公司,或者最终成为跨国公司。正规企业可以作为增加税收的基础,原因在于这些企业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运作(它们拥有银行账户或者外部投资者要求它们具备财务透明度)同时税收当局可以利用它们来扣缴员工所得税。正像克莱文等人(Kleven、Kreiner and Saez,2009)所强调的,扣缴所得税也有利于对个人和企业的税收记录进行交叉核查。
外国援助和资源依赖
在税收决策的标准框架中,政府只负责对其开支融资。贫穷国家税收低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许多国家接受了大量的外国援助,这些援助在GDP中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常常比国内税收还要多。另外,流向最贫穷国家的外来援助更多。例如,根据世界发展指数,1962-2006年间,外来援助占低收入国家总收入的平均份额大约在10%左右。获得外来援助降低了这些国家采取措施增加国内税收的激励。
这一观点在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国家的税收可以采取使用费的方式。2000年,在低收入国家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国家石油出口收入超过了GDP的20%。在经济严重依赖于初级产品的国家,外援的比重仍然很大。
对于那些有大量其他收入来源的国家,来源于宽税基(比如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税收要比其他国家低。为了支持这一观点,詹森(Jensen,2011)的研究表明,在政府总收入中,自然资源租金每增加1%,税收占GDP的份额就会降低1.4%。尽管我们知道这些研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但是大量的外国援助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完全有可能弱化从国内征税的激励。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稳定项目的主要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财政事务部积极鼓励各国政府按照法律要求和能够保留记录的方式进行投资,这有助于增强这些国家的财政能力。如果对援助的依赖事实上减少了来自国内的税收,从其负面效果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行动最多只能算是次优政策选择。
政府行动的失败
综合起来,这些经济因素表明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较低:非正规经济、来自自然资源或者特殊商品的收入、外来援助等因素共同导致许多低收入国家的税收占GDP比重较低,税基较窄。随着经济增长,政府面临着重构和扩大税基的挑战。
即使经济增长对扩大税收网络和税基很重要,但它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征集较高的税收。例如,皮凯蒂和钱楠筠(Piketty and Qian,2009)认为,自1986年以来,在印度,不断增加的税收豁免导致所得税收入一直停留在GDP的0.5%左右。如果要通过拓宽税基来增加税收,例如采取所得税和增值税的方式,需要有意识地改变税收体系和征缴机制,以反映更广泛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税收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收入,在1978-1994年间不断下降,因为政府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国有企业的收入,而这些国企的相对规模不断萎缩。然而,中国的税收收入在1994年税制改革后又开始逐步增加(参见世界银行2012年报告第三章)
要利用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优势,需要政府在改善税收体系方面进行投资。图1给出了一个重大财政创新的例子,即从工资中扣缴所得税。实现这一步,需要政府改变相应的政策以及确保能够有效遵从。没有这方面的措施,所得税可能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显著增加。通过增加营业税或者引入增值税来拓宽税基,也需要直接的政策改变,这些都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动出现。
也就是说,结构性变化和正规市场、正规企业规模的增加会减少这类投资的成本。经济发展带来了潜在的税收红利,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实际上逐步进入纳税范围。但是,这种变化能否真正带来更多的税收,还取决于政府的决策。这些决策反映了当地的政治制度,接下来我们将对此加以讨论。
有些结构性改变也可能会带来政府收入的减少。例如,那些试图控制通货膨胀的政府,可能会失去铸币税。试图放松管制或实行经济私有化,也会降低政府之前拥有的隐性税收,特别是当工资和价格实行自由化之后。在那些从社会主义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中,这是非常突出的问题。可以说,中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逐步使用营业税的现代税收体制,逐步摆脱将土地租赁作为增加国家收入的手段。当转型伴随着经济增长时,这些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被掩盖起来。但最终,需要通过有意识的改革构建一个有效的税收体制。
政治制度
从表面上看,在投资基础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低收入国家的需求明显要比高收入国家高。事实上,“二战”以来的国际援助运动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另外,成立世界银行和区域性开发银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向这些发展中国家提供投资公共项目的资源。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发展中国家为了投资基础服务而增加税收的动机应该很强烈。
但是,增加的税收是否用来满足最有需求的人群取决于政治均衡。反过来说,这取决于当地的政治制度如何决定取得政权的统治集团怎样制定政策,以及统治者面临的约束。谁拥有政治控制权直接影响着税收水平和税收种类方面的决策,这些决策取决于统治集团所认为的政治成本和收益。另外,政治也对税收如何分配产生影响,这反过来又影响对高税收的政治支持率。
权力的低竞争度
尽管我们应该防止一概而论,但在许多低收入国家,富裕的精英阶层控制着政治是事实。这些精英群体受到各种制度机制的保护,包括权力的继承、军事政府和政党的精英控制。在这些精英群体的治下,政策会更多地迎合中位收入以上的群体,这降低了征收累进税的激励。精英群体控制的政府也影响着财政收入如何使用。正如梅尔泽和理查德所建议的,以及赫斯特得和肯尼(Husted and Kenny,2007)的实证研究所支持的那样,如果对权力的竞争变得更公开,我们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再分配性累进税。根据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Acemoglu and Robinson,2006)的研究,历史上扩大选举权的改革反映了富有的精英统治集团害怕革命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
梅尔泽和理查德(1981)的基准模型假定税收收入是平均分配的,但实际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选择性再分配。例如,高等教育支出更加向精英群体及其家庭倾斜,但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有可能用于穷人。在某种程度上,富裕的统治集团更喜欢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对使用财政体制进行再分配的需求减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预期精英控制政治往往会导致更少的公共支出。
薄弱的制衡机制
对现任统治集团的制衡有助于推动政府开支更加偏好公共利益。一个强大的立法机关往往会寻求广泛的联盟,从而抵消行政机关的狭隘性。独立的司法也可以借助法定的服务提供义务或者运用基于权利的主张和裁决来扩大公共服务的可及性。然而,许多低收入国家在权力竞争方面受到极大限制,既包括对选举权的限制,也包括对谁来执政等方面的限制。低收入国家在对行政机关的制衡方面也比较弱。例如,根据经常使用的政体IV指数,2000年,就政治制度对行政机关的制约而言,在人均GDP最低的三分之一国家组中只有7%的国家得分比较高,而人均GDP较高的三分之二国家组中有40%的国家得分比较高。
虽然经济学家们总是用成本-收益分析来论证投资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等普惠型公共支出项目是值得的,但是在许多低收入国家确定这类公共支出项目的必要性并不是什么问题;问题主要来自公共服务的提供过程。公共服务的提供反映出低效率和腐败的双重问题。大量的宏观事实表明,在国家层面对行政权力的制约越多,腐败的程度也就越低。当然,这种相关性并不存在有充分说服力的因果解释,但存在直接的逻辑支撑。制衡机制应该通过对公共开支决策进行审查和建立必要的审计系统,为消除腐败提供强有力的基础。因此,不难发现在低腐败和税收水平之间存在强烈的正相关性,正如表1和图8(较高的清廉指数对应着较低的腐败认知)所显示的。这种相关性部分是由于当腐败的政府增税时,会面临较大的抵制。然而,它也从多个维度反映出政府效能的一些共同决定因素,在我们2011年的文章中,我们称之为“发展集群”。政府不同方面的能力协同演化,既是因为政府总体能力的提升,也是因为一些潜在的共同因素,比如制度。
图8腐败和财政能力
注释和资料来源:我们利用透明国际2006年的腐败认知指数,0代表着高腐败,10代表着低腐败。税收份额数据来自Baunsgaard and Keen (2005)。
越来越多的微观经济研究开始关注低收入国家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是否可以减少腐败并提升服务质量。得出的结果莫衷一是。在这些研究中,奥肯(Olken,2007)从一个随机的现场实验中找出了一些减少腐败方法的证据,这个实验是对印度尼西亚的600多条公路项目,计算官方运作成本和独立工程师估计的成本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奥肯的研究显示,社区监督机制看似并不起作用。然而,雷尼卡和斯文森(Reinikka and Svensson,2005)研究了乌干达的报纸运动,该运动旨在通过向父母提供信息以监控当地政府如何分配教育补助金,从而实现减少公共资金被侵吞的目标。这个研究发现,通过社区监督,学生入学率和学习成绩都有显著提升。这些微观研究表明一国制度的细节和具体方法对反腐至关重要。
对于腐败的受益者,特别是那些寻租的官员和公共服务提供者,并不喜欢“漏损”少的公共支出项目。一些公民也会从带来腐败的公共服务特权过程中获益。尽管,这种受益的可能是少数,他们也会抵制旨在减少腐败的改革。伴随无处不在的腐败,一般公民可能不会支持较高的税收政策以及很好地遵从现有的税收政策。下一部分将研究能够具备支持税收意愿的文化和规范。
文化、规范和身份认同
在税收遵从方面,除了自阿林厄姆和桑德姆(Allingham and sandmo,1972)的开创性论文所强调的成本-收益分析外,纳税的内在动机和对法律的遵从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不同社会科学的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讨论了纳税的伦理价值,比如,戈登(1989)提到了个人道德,科威尔(Cowell,1990)提到耻辱,埃拉尔等(Erard and Feinstein,1994)提到了罪恶和羞耻感,波斯纳(Posner,2000)提到税收遵从方面的规范,托尔格勒(Torgler,2007)提到税收道德规范。把这些主张统一起来的一种观点是,创建一种善于遵从的文化可能是增加税收的关键。因此,低收入国家税收水平低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些国家的纳税伦理规范要比高收入国家差。缺乏强有力的遵从规范,意味着任一法定税率水平下所带来的财政收入要比预期的少。
然而,对这些观点及其经验分析上的重要性,还没有达成很强的共识,特别是在低收入国家。举例而言,高度腐败或者感觉某种税收体制不公平,可能会阻碍遵从规范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深层次的问题是腐败和不公平,而不是社会规范。有意义的是规范一旦建立,可以成为个人遵从决策的策略性补充。特别是,如果规范的产生是基于纳税是一种道德行为的信念,这可能会成为遵从的转折点。这种乘数效应可能会反过来促进对改善法律规则、强调正规企业重要性、加强税收监控和产权登记等方面的投资。
要正确地评估这些可能性,需要更多地研究纳税的个人物质动机和社会动机间的相互作用,但迄今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为了从经验层面考察社会规范对税收的重要性,还需要开发出一个能够做出清晰预测的模型,特别是纳税的个人动机和社会动机间的相互作用。
梯若尔等人(Benabou and Tirole,2011)提供了一个一般性模型,在该模型中,与规范相联系的社会动机(来源于对获得社会声誉的渴望)可以加强(挤入)或者削弱(挤出)与法律相联系的强烈的个人动机。贝斯利、詹森和佩尔松(2014)对这一模型进行了动态拓展,并将它应用于分析英国地方产权税的遵从。通过在总体层面和地方层面的现场实验,我们发现有证据表明在税收遵从方面存在相当多的社会规范,同时个人动机与社会规范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
税收遵从规范的出现也可能部分来源于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在许多羸弱的国家,民众的国家认同感也相对较弱。这为理解辛兹(1906)和 梯利(1990)关于税收和战争相联系的经典观点提供了一种视角。这与财政收入和战争年份之间的正相关性也相一致。图1显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税收显著增加,这一点在战后并没有改变。在一些国家,战争一直被认为是共同利益的来源之一,包括劝说公民接受高税收以及建立一种缴税的规范(例如,Feldman and Slemrod,2009)。如果税收遵从规范能够长期存在,财政收入的效应会持续到战争结束之后。图1表明了这种规范具有持久性,而不是两次战争期间的短暂现象。
类似的观点也适用于解释民族分裂和税收收入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这反映在著名的观点中,即非洲殖民政权所人为设计的国家边境导致了民族分裂政策,产生了不良的发展后果(例如,Easterly and Levine,1997)。但是分裂并不是不可改变的,所以和政策相关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随着时间推移改变民族认同感。贝茨(Bates,1974)认为,非洲后殖民国家的独立驱动着强烈的民族认同感,伴随着先前存在的民族对国家赞助的争夺。当民族间矛盾紧张到要爆发内战时,会增加族群间的仇恨,并减少国家认同感。
国家建设
对于低收入国家而言,拓宽税基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前瞻性的制度投资。政府决定采取什么样的税基以及实行什么样的行政和遵从结构。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引入工资扣缴所得税,这对于拓宽税基很关键(就像图1所显示的那样)。另一个比较好的例子是投资于税务当局的组织建设和培训。 因为这些政策有着长期影响,我们(2009,2001)称之为财政能力投资。
按照这种动态的观点,当前关于引入或修正税收体制的决策将影响未来的税收水平。旨在减少因税基扩大导致的所得税“漏损效应”的投资,将会提高未来的财政收入,同时也会改变未来政府利用所得税来增加收入的激励机制。这种情况表明,可以把财政能力投资作为战略性和前瞻性的举措。
税收和弱政府
税收在国家发展中曾经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贯穿整个历史,财政收入方面的斗争一直是国家权力斗争的核心。在现代宪政政府的纲领性文献英国《大宪章》中,拥有增加税收的权力是其核心。它使那个时代的政府走向税收设置的中央集权制,议会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法国财政国家(fiscal sfata)发展演变的历史解释(Dincecco,2011)认为,税收设定的中央集权是更为晚近的现象。这种观点认为,税收是国家强制权的关键方面。因此,它和一个国家范围内法律和秩序的建立紧密联系。
那些在提升财政收入比重方面失败的国家,往往也不能有效地保护产权(如表1所示)。税收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基于规则的财政征收方式。市场关系是财政的基础。因此,渴望获得税收的政府,也有激励去建立支撑正规市场运作的制度。例如,建立一个正规的金融市场将有效增加企业和个人税收。因为法治的建立有助于提升市场的功能,财政能力的建设是从其他维度提升政府效能的补充方式。
最终,税收不仅和国家强制权的构建有关,而且改变了执行国家强制权的方式。国家过去带有更多伤害性去攫取财政资源的方式,被基于规则和更加友善的征税方式所取代。
但是,在现代高收入国家中,税收占GDP比重很高,这不仅仅是因为强制权。在这些国家,政府面临许多法律和实践约束,包括被选下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规范逐渐演变成支持广税基和相当大程度的税收遵从。那些希望政府税收能够被合理花费的公民,要求政府更加可问责和更加透明。
对于现代低收入国家而言,增加更多的税收收入,并不仅仅是拥有技术专长的问题。政府制度和税收体制协同演进,税收可能会反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发展(Levi,1988)。软弱和不可问责的政府不可能有强大的动力去构建财政能力,他们的民众也不可能很好地遵从规范。这是一个典型的正反馈问题,既可以产生好的均衡路径,也可以产生坏的均衡路径。
国家建设的顺序
许多组织向那些希望提升税务当局运作水平的国家提供技术支持。基于随机干预的证据很容易说明政策的某些特点。例如,在卡恩等人(Khan、Khwaja and Olken,2014)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财产税务部门的合作中,将财产税单位分成一个具有三类绩效的支付体系或控制组。他们发现,受到激励的单位平均税收比控制组高9个百分点。随机控制实验的更多证据表明,一个关键问题在于政府看到这些实证数据后,是否愿意改变。
最后,最重要的观察还是本文开头所强调的基本事实:从税收占GDP的比重和税收结构看,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和当时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高收入国家没有太大不同。这一事实表明,低税收可能反映了一系列的因素,这些因素也有助于解释这些国家为什么贫穷。从这个方面看,最重要的挑战在于采取措施去鼓励发展,而不是仅仅关注如何改善税收体制。
参考文献:
Acemoglu Daron,and James Robinson.2006.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llingham,Michael G.,and Agnar Sandmo.1972.“Income Tax Evasion:A Theoret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3 4):323 38.
Bates,Robert H.1974.“Ethnic Competition and Moder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6(4):457 84.
Baunsgaard,Thomas,and Michael Keen.2005.“Tax Revenue and (or?) Trade Liberalization.” Mimeo,IMF.
Benabou,Roland,and Jean Tirole.2011.“Laws and Norms.” NBER Working Paper 17579.
Besley,Timothy,Anders Jensen,and Torsten Persson.2014.“Norms,Enforcement and Tax Evasion.” http://people.su.se/~tpers/papers /Draft_140302.pdf.
Besley,Timothy,and Torsten Persson.2009.“The Origins of State Capacity:Property Rights,Taxation,and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9(4):1218 44.
Besley,Timothy,and Torsten Persson.2011.Pillars of Prosperity:The Political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luste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utigam,Deborah A.,Odd Helge Fjeldstad,and Mick Moore,eds.2008.Taxation and State Build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Capacity and Consen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owell,Frank Alan.1990.Cheating the Government:The Economics of Evasion.Cambridge,MA:MIT Press.
Dincecco,Mark.2011.Political Transformations and Public Finances:Europe,1650 1913.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asterly,William,and Ross Levine.1997.“Africa’s Growth Tragedy:Policies and Ethnic Division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1203 50.
Erard,Brian,and Jonathan Feinstein.1994.“The Role of Moral Sentiments and Audit Perceptions on Tax Compliance.”Public Finance 49(Special Issue on Public Finance and Irregular Activities):70 89.
Fearon,James D.2003.“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by Country.”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8(2):195 222.
Feldman,Naomi E.,and JoelSlemrod.2009.“War and Taxation:When Does Patriotism Overcome the Free Rider Impulse?” Chap.8 in The New Fiscal Sociology:Taxation in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ited by I.W.Martin,A.K.Mehrotra,and M.Prasa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ordon,James P.F.1989.“Individual Morality and Reputation Costs as Deterrents to Tax Evasion.”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3(4):797 804.
Gordon,Roger,and Young Lee.2005.“Tax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5 6):1027 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