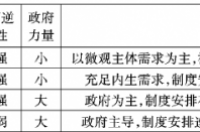2008年金融与经济危机以来,地球生态退化的危机凸显。不同于具有周期性特点的经济和金融危机,生态危机具有不可逆性,其危害一旦造成难以弥补。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停滞的西方国家和增长相对强劲的后起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内部,围绕地球生态退化和本国发展优先性(权利)的矛盾,在危机以后的秩序重构里面,以生态干预的形式激凸。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为解构这些复杂现象提供了分析的工具。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股左翼思潮,也是一股新的社会主义思潮。20世纪70年代西方绿色运动的兴起,促使生态社会主义思潮伴随着人们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而兴起;20世纪8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特征凸显,注重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认为异化消费是社会生态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开始关注生态社会主义模式的构想;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引发了社会主义是否能取代资本主义的大讨论,生态社会主义因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而受重视。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主要来自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理论,生态学、系统论和未来学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将生态危机的社会根源指向了资本主义制度,强调生态社会主义是绿色社会、人与自然全面发展的社会。
2008年以来围绕生态社会主义的研究,仍然主要在两个传统领域里面耕耘:生态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和生态社会主义对生产的重新定义。前一方面的进展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的可兼容假说,从资本主义进入对抗自然的帝国主义阶段,以及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生态角度定义为破坏生态的单调生产,指出这种生产方式有着不可治愈的内在矛盾与“代谢断层”,提出相反的不可兼容的假说。后一方面的进展主要是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和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
1.可兼容的假说:非社会主义的观点。
在解决生态危机的三大阵营中,生态现代化和生态自足占有一席之地,两者均认为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具备兼容性。一种立场是“生态现代化”,其假定了一种新的生态敏感的资本主义是可达到的。另一种立场是“生态自足”,其与生态充分性相结合,并要求社会处于生态限制中。
“生态现代化”由约瑟夫·胡贝尔(Joseph Huber)和亚瑟·摩尔(Arthur Mol)提出,假定当满足生态框架时资本主义增长模式是能够维持的。他们将资本主义定义为无限可塑造的,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利润的生产是可持续的,积累可以与生态退化不挂钩,资本主义增长能够为生态服务,而不是生态可持续的障碍,增长成为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动机。就生态现代化者来说,“生态领跑者”正是高收入、高增长的工业化国家,他们领导了生态现代化道路。[1]另有“生态现代化”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可以促进环境改革,不需要现代体系的根本改变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生态现代化”的视角建立在了进步主义的假定之上,它需要解释现代化具有一个向环境可持续的趋势,而不是环境改善的偶然情况。[2]
“生态自足”拥护者将资本主义视为生产物质产品、存在一个特殊生态影响的特定实体,同样也被视为一个由生态系统法则控制的特定实体。根据詹姆斯·古德曼(James Goodman,2009),[1]生态自足迫使减少增长并遏制资本主义,考虑到任何种类的生产都受到生态影响,重要的是缩小消费。最终的目标是在一个低消费的生态社会寻找范例,以生态限制开始,要求社会与生态限制共存。衡量生态充足的国际水平最清晰地反映在1998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创立的地球生命力指数(Living Planet Index,LPI),这是一种衡量地球生态状况的指数概念,借助物种丰富度变化的表述衡量地球的生态状况,它计算了全球的再生产能力,及多久将被全球消费所超过。
2.不可兼容性假说: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
与生态现代性和生态自足的立场相左,生态社会主义者对资本主义与生态可持续性不可兼容的论断建立在对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增长的批判的基础之上。其基本理由基于如下三个方面。
(1)资本主义进入对抗自然的帝国主义阶段。
佐佐木力(Chikara Sasaki,2011)从日本2011年3月10日的大地震引发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爆炸事件开始阐发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对抗自然的帝国主义”阶段。从“殖民帝国主义”向“对抗自然帝国主义”的过渡,科学技术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中期以前,科学技术被用于地理扩张和购买殖民地,二战以后殖民地国家和不发达地区开始出现政治独立,地理扩张开始饱和。科技被用来对抗自然并导致环境恶化,森林被推平用于种植出口的小麦,山丘被破坏用来挖煤矿,河流被工业废料污染。[3]
日本承受着永久的自然资源短缺,其帝国主义的目的正是为了从邻国获得稳定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廉价劳动力,日本战前的殖民主义模式反映的是“大东亚共荣圈”。战后的代表性科学技术是核技术,其所包含的历史负担是在广岛和长崎第一次被用于大屠杀的武器,美国的原子弹轰炸是美日帝国主义野蛮冲突的表现。这项科技并没有因为其用于“和平的”电力而改变,因为仍不存在有效的方式来控制和消除核能的放射。全球环境问题和自然资源是目前公认的人类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这与一种生产方式如何对待科学技术有关。[3]
(2)破坏生态的单调生产、不可治愈的内在矛盾与“代谢断层”。
“单调生产”(Treadmill of Production)这一概念由史奈伯格(Schnaiberg)于1980年首次提出,一是源自20世纪后半段生产过程对生态影响的重大改变,二是源自社会和政治对于生产过程的反应。[4]单调生产理论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增加资源消费和废物排放使环境问题恶化从根本上说是一般趋势,并不是经济中的特殊体系。资本主义的价值生产产生了将自然条件单一化和简单化的趋势,若没有全球政治经济的巨变,现代化只能使自然环境进一步恶化。[2]全球化的生态影响分析仍应考虑“单调逻辑”。奈海德·康纳克(Nahide Konak,2008)强调资本主义经济表现得像一个“单调生产”,单调生产与经济危机直接联系,经济增长和积累要求自然资源的开采,这就导致了污染。“单调生产”理论认为资本密集型的扩张内生于资本主义,存在着朝着环境退化的内在趋势。通过不断增加的生产率和消费率的自我强化机制连续不断地破坏生态。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原则是利润最大化和竞争,这推动了人类社会不断开采资源并回收,积累了废弃物和副产品。同时,国家和官员更倾向于经济增长,这既确保税收收入,又保证了再次竞选的可能。全球化的影响意味着“跨国单调”的出现,“单调生产”理论者认为,“跨国的单调市场主体”支配了“单一民族国家的国家机构和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允许了资本和技术运动,也允许了社会和环境成本向非西方国家社会转移,全球化加强了单调生产,从而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5]
奥康纳(O""Connor)曾指出资本主义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资本和自然两个矛盾的基础之上,反映在商品形式中则是一个社会(人与人)和代谢(人与自然)的关系。伯克特(Burkett,P.)和福斯特(Foster,J.)运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对社会和代谢的关系进行了说明。马克思强调自然和人类劳动都为创造全部使用价值作出了贡献,商品的物理部分由自然提供的原料和劳动构成。没有使用价值将不存在价值。商品若无用,其包含的劳动也同样无用,劳动不计为抽象劳动,那就不创造价值。因此,商品是自然和劳动的产物,劳动本身是其与自然之间的交互关系,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既是一个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个代谢(人与自然)的关系。[6]
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使用新陈代谢的概念说明通过社会生产而形成的人类一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福斯特利用“代谢断层”说明资本主义激励的逻辑无情地制造了社会与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基本进程——单调生产、生产和分配的阶级不公平破坏了人类经济发展最终依赖的自然条件,代谢断层下出现了生态可持续的问题。[7]
詹姆斯·古德曼从资本积累的实质指出,不存在没有生态危机的资本积累。从这一角度来说,气候变化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副作用,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心对自然系统开发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自然处于结构性的矛盾之中。[8]
生态社会主义者公认资本主义制度是全球危机产生的根源,这已经成为这一学派的一个理论标志。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发生机制多从增长问题、技术问题和消费问题三个方面描述。靳晓春的观点比较有总结性,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追求利润和资本积累最大化的生产方式。资本积累导致短时期内污染物的排放量超出了生态容量。靳晓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态危机的逻辑必然性的解释是,资本主义生产以价值生产为基础。价值在质上的同一性带来了价值在量上的可分性,这就产生了对自然的分割与碎片化,忽略了生态系统内部不同自然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资本的专业化生产强化了这一点。分工带来的城乡分离运动使物质循环产生了断裂。国家内部、不同国家之间商品和劳动力的流动加强了人们在处理其与自然的关系时的短时性。以剩余价值生产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与自然条件的再生产相矛盾,这就产生了生态问题发生的可能性。资本积累则引致生态问题的必然性。资本的积累意味着价值的积累,而价值必须体现在使用价值之中。因此,资本积累意味着对原料需求的增长,对自然界限的不断超越。[9]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成为了资本家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科技越发达自然破坏也越严重。[10]资本家作为主导者,为了高额利润不断扩大生产和消费导致生态关系失衡。[1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导致“成本外在化”,表现为新的土地、资源的剥削和空气、水、土地等的污染。发达国家将污染行业转向发展中国家的过程给其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并承受不合理的环境负担。[12]
更激进的观点,如萨卡认为,资本主义是生态危机的切近根源,但是生态危机的最终根源不仅是资本主义,而且是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生态社会的市场经济”和“工业社会的生态重组”的概念存在两种幻想:一是幻想科学技术能克服生态危机,既能拯救工业社会,同时又能使南方国家得到持续发展;二是幻想资本主义自身依靠局部经济革新可以解决生态危机。[13]一个例子是为自然定价、建立污染排放权交易市场,日益被作为应对生态危机的政策调整,体现了资本对自然条件的控制权,重建资本理性对自然资源的私有产权。目的为私人财富的增加,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生态领域的深化。[9]萨卡认为生态资本主义必将破产。
二、生态社会主义对生产的重新定义
(一)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
1.绿色经济与关怀经济。
克里斯塔·维特里希(Christa Wichterich)认为,以下概念在推动经济政治制度生态化方面被论述得较为充分,包括有绿色经济、关怀经济。当前全球的金融、能源和气候的三重危机需要通过绿色投资来改变,政治需超越经济、政策和政党来协助市场。例如在可再生能源和节能建设领域实施绿色创新,创造绿色职业。绿色新政强调的是包括全部社会群体在内的调控和限制金融市场以及公共部门投资。关怀经济在南半球被称为生存经济或民生经济,它代表了整个经济的完全转变,从投机活动转变为供给,目标是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和自然关系之中,并且将全球社会公正与环境和性别公平结合起来。关怀经济的第一步就是在现实政治和替代性经济之间创造一个联结,创造与自然全新的关系。[14]
2.运用“生态社会主义”视角指导生产。
生态社会主义者并不主张资本主义下的低经济增长,认为其反而意味着不公正,“更加紧缩甚至更多的向上集中的财富和权力分配”。[8]福斯特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由人类劳动及其在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来调节。解决资本主义生态破坏的唯一办法是改变我们的生产关系,新陈代谢的恢复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的彻底决裂。福斯特认为新陈代谢的概念在马克思关于生产者联合的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起中心作用。通过工业和农业的结合、人口的分散以及恢复人与土地之间的新陈代谢,在新社会里联合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这需要计划、对人类和自然革命性的转变。[7]
(1)集中管理和去生长的过程。穆勒(Muller)和帕斯克斯(Passakis)总结道,生态社会主义者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了规划和公共管理,并且它必须是一个“集中管理、去生长的公正的过程”。他们以实证为例论证了生态排放量显著减少的过程。一是东方集团国家的崩溃时期,苏维埃GDP下降40%是与排放量大概下降40%相一致的;二是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2009年9月21日《金融时报》引用了国际能源机构报告,指出来自“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已发生显著下降,超过过去40年中任何一年,下降的工业产出是二氧化碳下降的缘由”。[15]
(2)生产关系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中人的地位和产品分配三个方面的内容。詹姆斯·古德曼认为,取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是为需求而非利益的生产社会主义系统,且被生态中心化所定义。与消费主义相反,自由结合的劳动者为普通人生产“高效的使用价值”。[1]“本地共有”具有参考意义。“本地共有(Commons)”指一切劳动加工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对社会全部成员都是可利用的,包括自然资源如空气、水和适于居住的地球。这些资源是共有的,不归私人所有,本地社区自行组织和集体行动。维克托·沃利斯(Victor Wallis)认为,人类能够从具有大规模激进环境意识的土著民族中获得启示,模范般敬畏自然,做到材料的自给自足,抛弃个人财产权利,尊崇平均主义,具有共同的责任感。[16]
女性主义观点同样指出必须弱化剥削的逻辑,改变生产、贸易和消费的结构。跳出由资源开采、生产和消费形成的增长的恶性循环,其具体途径包括精简北半球工业,避免生产过剩;改变破坏性的、多余的工业,例如将武器制造业改造成低耗能、低排放的工厂或回收工业;废除过度消费和全球中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社会需要超越市场、效率和酬劳来重新定义劳动和价值创造,评估劳动时承认社会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劳动,以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来促进社会再生产。[14]
(3)以不支配自然的方式重新定义技术和使用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曾经怀疑科技是否能解决环境问题,奥康纳从工业资本的历史中也指出,科技是以其对成本和销售的作用为基础的,并非自然。[5]詹姆斯·古德曼认为,如果自由联合的劳动力是用来生产“高效的使用价值”,那么这种使用价值就必须生态化地嵌入。真实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需求是满足生态系统的,并非与之对抗。生态社会主义者只能使用促进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技术和使用价值。[8]
生态社会主义者的理想模式是“更少的生产,更好的生活”。这种制度下人们的生产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新的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对资源能源的精心安排,更好的生产才能带来更好的生活,也有益于社会公平。[17]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用生态理性替代经济理性:“经济合理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对经济生产率最大化的追求在于,以尽可能高的利润,以最大化的效率生产尽可能大量的物品进行销售,而这一切要求消费和需要的最大化。“生态合理性”是指以尽可能好的方式,尽可能少的、有高使用价值和耐用性的物品满足物质需求,并以最小化的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来实现这一点。它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我们在其中生活得更好、然而劳动和消费更少的社会。[18]未来经济将是基于生态法则,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的。[19]
自然规律的作用决定了维持生态平衡与自然物质可持续的循环,需要人类在生产中合理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循环,不仅要考虑单一自然因素在不同生产领域、不同地域之间的新陈代谢,还要考虑不同生产要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一点只有通过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自然生产条件的控制才可能实现。社会化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9]
总的来说,生态社会主义描述的未来社会是一个全新的人与自然比较和谐且符合生态原则的绿色社会,它克服了人与自然的矛盾,主张实现自然的解放,以最终实现人类的解放。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和理论主题,生态社会主义者并没有将生态问题归咎为人口过剩、工业方式或者人的欲望等,既不能为强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而取消人的特殊利益,也不能因人的特殊利益而破坏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二者是一致的。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类协调好自然的工具价值和生态价值,将人类对物欲的追求转变为对生态和谐的追求,为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创造有利的物质条件,将生态意识融入到人们日常生活中。[20]
(二)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路径
政治制度层面。一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社会公正。[11]佩珀认为消除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在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走以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本主义为特征的生态社会主义路径,生物中心对人类来说同样是不可能实现的;[12]二是民主建设,推动真正的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应实现自我管理,工人应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决定权,重视工人自己的计划和给予权利。[21]
经济发展层面。一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按需而不是按利润进行资源的开发和分配,改变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代之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11]以使用价值代替交换价值,使交换价值从属于使用价值,使抽象劳动从属于具体劳动,凸显使用价值和具体劳动的重要性,按照需要而不是按照利润进行生产。[22]二是用宏观经济规划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混乱无序状态,就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能源和资源需求如何分配等达成共识。三是工业经济必须萎缩到一定的稳定状态,收缩意味着人们承受比今天低的生活水平但幸福指数不会下降。[13]
最后是社会发展层面,以关爱为基础,使关爱成为社会运行最重要的价值;实行无核化,制作和运用核武器就是环境污染过程。[20]
生态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是从根本上改变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目标是实现自然和人类的共同解放。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在改变资本主义为利润而生产的动机基础上,生产动机的改变必然导致现有生产水平的主观缩减,这样一个过程不仅依赖国家的统筹规划,也依赖着实际生活和生产过程中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配合,如何培养公众的生态意识是关键。公众的生态意识逐渐强化,一旦涉及具体经济利益的分配时是否依然能坚持非利润化的生产和分配动机,外在强制并不能保证始终起作用,这需要培养起全体公民自身内生的生态社会主义立场,所以建立生态社会主义的前提之一是人的角色,如何实现作为生产者、管理者和消费者的公众都坚定地支持生态社会主义立场是一大难题。
三、资本主义的全球联合干预及其效果
生态环境的破坏,之前是被当做繁荣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副产品对待。2008年危机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契机,生态危机作为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的一个方面被重新检视。或者说,这一次的危机较之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大不同是,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业已濒临极限,这为危机蒙上了另一层浓重的阴影。
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霸权国家内部、它们与新兴发展中经济体之间,围绕发展优先权的竞争和地球环境责任的推诿展开角力。地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与本国发展的优先性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国家间的重大利益冲突,共同利益的均衡点难以把握。抑制他国发展、维护本国对地球生态消耗的霸权,成为本轮危机以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存在一个“伞型集团”,指的是欧盟以外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一直以来,伞型集团国家企图扼杀《京都议定书》。如伞型国家代表澳大利亚于2011年宣布二氧化碳削减计划延期执行。
即使在欧盟内部,2013年6月欧盟曾决定2020年起在欧盟国家执行每公里95g二氧化碳的小汽车排放标准,汽车工业是德国的支柱产业,德国总理默克尔及其所属保守党支持德国的汽车制造商,认为这将降低就业并损害高端汽车制造商,最终欧盟推迟了减排决议。
世界气候大会围绕全球气候变化的后果与治理展开激烈的争论,纠缠着富裕国家与落后国家的利益纠纷,以及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
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会议准备拟定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的全球框架,目标是发达国家在2020年大幅度削减排放,发展中国家需采取措施抑制本国碳排放,同时富国资助穷国。但经济衰退的现实使得富国更不愿意向新兴国家提供资助。受这次会议影响,碳排放价格下降,企业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动力降低。
2010年坎昆世界气候大会。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指出,《哥本哈根协议》不能保证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不超过2摄氏度。会议开始一个月前的美国中期选举,气候政策较为保守的共和党在两院选举中胜出。坎昆会议上美国鲜有发声,发展中国家减排的“透明度”成为了美国提供任何资金和技术的前提条件。在哥本哈根和其他会议中各国达成的“气候资金”共识也由于美国的“透明度”缘由未有进展。
2011年德班世界气候大会,美国表示不愿支持具有法律效力的协定,印度等其他主要新兴国家也表示反对类似的全球协定。美国成为全球气候谈判的障碍。奥巴马2007年就职演讲时曾表示“我们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帮助将世界带入一个进行气候变化的新时代”,而就职后的三年内美国在谈判进程和气候融资上的消极立场威胁了全球的气候变化合作。
2012年多哈世界气候大会,新一轮的气候谈判走向破裂,各国就富国到底应如何资助穷国而陷入僵局。
2013年华沙世界气候大会,强调签署长期的全球性协议的必要性,所有国家就碳排放达成协议,各国都征税,发达国家专注研发新技术,而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国家以低成本获得这些技术,但如此乐观的事情很难发生。本次大会上,日本内阁通过的新减排目标实质上增加了其排放量,日本的“减排”引来责备。
2014年11月美中第三次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美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减排计划:美国采取计量表述形式,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球减排目标,并努力减排28%;中国划定了碳排放封顶期限,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这份声明为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谈判增添了动力。然而,《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表当天,美国众议院院长、共和党众议员约翰·博纳(John Boehner)声明此举将严重影响美国人民的就业,拉高清洁能源价格,其价格的上升影响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即将出任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表示经济无法承受奥巴马总统对煤炭发起的意识形态战争,矿工们将失去工作,中产阶级负担增加,他呼吁美国民众反对奥巴马的此项计划,并将利用共和党在参众两院的控制权推翻奥巴马的减排计划。早在2010年,以博纳为代表的共和党就反对奥巴马政府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其身后代表了美国传统化石能源产业利益。
伞型集团和欧盟对生态退化的干预,以及全球气候会议,其思想基础是资本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可兼容性,是试图利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协调和再平衡实现对地球生态和自然环境的保护。
随着公众环保意识提高、地球生态恶化严峻,政党候选人为赢得选票或改善国际形象时纷纷打出环保旗帜。选举胜利后,若遇政治与经济形势变动会轻易地放弃兑现选举时的承诺。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案例正是其选举文明的一种体现,德国的游说案例更是体现了选举政治下经济、政治和环境利益三者的冲突。
发达国家由于产业优化和技术先进,温室气体排放总体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上升期,技术落后,温室气体排放总体趋于增加。发达国家支持本国的减排任务建立在以未来排放量和总量的基础上,而发展中国家支持本国的减排任务建立在历史排放量和人均的基础上。各国在减排指标与时间表方面的矛盾与分歧长期存在。发达国家就到底应以何种方式资助发展中国家互相展开辩论。美国游离在《京都议定书》之外,拒绝提供资金援助,要求各国承担自己的责任。美欧认为其因牺牲GDP而减排的量还不如金砖国家每年增加的量多,担心落后国家成为新兴国家后威胁其经济利益。落后国家由于缺乏资金和技术,发展途中无法完全承担环境责任。富国对穷国的援助常常建立在对其经济和政治的控制之下,承诺的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会因“知识产权保护”或“经济衰退”等各种理由而拒绝兑现。落后国家与富裕国家之间、富裕国家内部就谁应当为减排承担更多责任争执不下。步履维艰的历届气候大会传达出全球合作的难度高、进展慢、效率低等的困境。由西方世界主导的干预地球生态和自然环境退化方面的停滞,恰恰用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和生态可持续性的不可兼容性,源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与以地球自然生态为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生产方式的内在悖论。
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和自然处在结构性矛盾之中,并且资本与自然的代谢断层在资本主义框架下仍然是依赖资本主义积累的传递作用来治愈。这种“治愈”是不可能持续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积累在治愈代谢断层,重要表现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模式仍得以维持着并创造生产力,先进的技术文明对生产和生活环境的改良造福了人类。“生态现代化”与“生态自足”即是这一类的资本主义制度自信的表现。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积累创造了更大的代谢断层,这无法依赖更长期的资本主义积累来解决。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后,并未改变其经济增长与生态可持续之间的矛盾,科技继续被用于对抗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机与追逐经济利益的生产、消费目标不改变,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的矛盾。向着生态退化线性积累的“单调生产”模式是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科技继续被用于对抗自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机与追逐经济利益的生产、消费目标不改变,不可能解决经济发展与生态可持续的矛盾。向着生态退化线性积累的“单调生产”模式是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的体现,它试图依靠对现实环境问题的预防和治理而实现“生态资本主义”,但却不承认环境问题正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义积累规律的体现,它试图依靠对现实环境问题的预防和治理而实现“生态资本主义”,但却不承认环境问题正内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不只是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
四、结论
环境问题的改善与根治无法在一国内部实现,也无法通过全球范围的凯恩斯主义的联合生态干预来实现。生态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实现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革新,借力全球化趋势,实现全球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变。生态社会主义者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独立行动,呼吁社会化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的物质变换,集体地规划和管理,根本地改变物质生产的指导思想,主张过度发展的经济的适当萎缩。生态社会主义对生产的重新定义与现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完全不同,生产和消费的目标是需求而非经济利益,“消费主义”将被取代。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是同时满足生态系统和人类需求的,故商品的使用价值是高效并生态化嵌入的。人类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决定了技术是否成为破坏自然环境的重要因素,科技的运用也应以自然保护为基础。理想的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着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不同的内涵与形式,维持自然的可持续必须要与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决裂,将生态意识真正融入生产与生活之中,并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才是生态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完整体现。
参考文献:
[1]James Goodman.Runaway Capitalism:Ecological Modernization,Ecological Sufficiency,Ecological Socialism[J].Theologies and Cultures,Vol.VI,No 1,June 2009.
[2]Richard York.The Treadmill of (Diversifying) Production[J].Organization Environment,Vol.17,No.3, September 2004.
[3]Chikara Sasaki.The great East Japan earthquake disaster and ecological socialism[J].International Critical Thought,2011,1(4).
[4]Schnaiberg,A,Pellow,DN,Weinberg,A.The treadmill of production and the environmental state[J].Institute for Policy Research,Evanston,IL,2000.
[5]Nahide Konak.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Eco-Marxist Perspectives:Globalization and Gold Mining Development in Turkey,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EB/OL].Published online: http://dx.doi.org/10.1080/10455750802571264,2008.
[6]Burkett,P,and Foster,J.Metabolism,energy,and entropy in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J].Theory and Society,2006,[53].
[7]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的破坏[J].国外理论动态,2008,(6).
[8]James Goodman.Responding to Climate Crisis:Modernization,Limits,Socialism[J].Journal of Australian Political Economy,No 66,2010.
[9]靳晓春.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实质及启示[J].经济纵横,2014,(8).
[10]刘付春.近年来生态社会主义研究综述[J].求实,2008,(9).
[11]王真.论构建生态社会主义[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S3).
[12]崔永杰.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佩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探析[J].东岳论丛,2009,(1).
[13]姜佑福.生态社会主义的两种基本面相及其内在理论张力[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14]Christa Wichterich.The Future We Want:A Feminist Perspective[M].Volume 21(English edition).Publication Series on Ecology,2012.
[15]Mueller and Passakis.Green Capitalism and the Climate:It""s Economic Growth Stupid![J].Critical Currents,No.6,2009.
[16]Victor Wallis.Beyond Green Capitalism[J].Monthly Review,Vol.61,No.9,February 2009.
[17]唐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从资本主义到生态社会主义——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启示[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18]周穗明.生态重建与生态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国学者高兹论生态社会主义[J].新视野,1996,(6).
[19]祝士明.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J].广东社会科学,2008,(4).
[20]刘秦民.生态社会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反思[J].山东社会科学,2012,[12].
[21]蔡华杰.生态社会主义的全球视野与国际向度——德里克·沃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述评[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
[22]解保军.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如何可能?——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探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