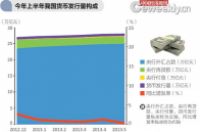——读《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
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从西北黄土高原带着满身的“黄土味”,还带着黄军帽,穿着家兄淘汰下来的黄军褂,乘着绿皮老式火车,从西安坐硬座40个小时之余,来到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前沿—广州。抬头一看广州火车站上的大幅标语“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八个大字,心中马上感觉到这和西北的“土味”完全不一样,进入到一个“海防”前线、毗邻港澳的“海味”十足的沿海大都市。到了中山大学校园里,我被南国的草木花卉所打动,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争奇斗艳、朴实无华的亚热带植物。当我进入到作为中大现校园第一古建筑、人类学系所在的“马丁堂”,进行研究生面试时,我又被这座既充满西方建筑气息,又有文化沉淀和厚度的建筑所吸引,真正感受到了想象中的“洋味”。也就是这栋楼,她和我结缘至今。它让我离开十几年后,又回到了熟悉而又陌生的空间。而在这个学术殿堂里,诸多朋友、同学给了很多的启迪和支持,而吴重庆兄是我从踏上这个校园开始,一直到今天联系互动、交流最多的几位老友之一。我们一起在中山大学80年代学生时期做过辩论队的教练、前后主编过当时很有青春激情的《中大青年》。我离开中大,不管在北京还是东京,我们一直保持着辩论队时的那种激情,一见面就是彻夜聊天,有聊不完的话题。并不时地听他讲到他家乡的变迁,尽管他对于家乡的表述很多已经成文,但听他所讲的家乡的故事,是从文字中难以感受到的那种复杂的情怀。由于有他多年来的讲述前提,当我看到他的大作时,似乎能把话语记忆中的人与事,非常有感觉、有体验地和他书中的故事有机地对接起来,能通过重庆兄的身心感受,体味、认识他说写的家乡的故事。这个地点虽然不是沿海的都市—广州,但是她是沿海的乡村,一个叫孙村的地方。在这个村里所透露出来的气息和所发生的故事,与我刚来广州时感受到的味道居然有跨越时空的同样感知,即“土味”、“海味”、“洋味”俱全,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三味一体”。这“三味”背后,着实体现了山海之间的一个中国东南沿海乡村的变化轨迹,也可以称为“大转折”背后的乡村“秘径”。
这一“秘径”的叙事,是以乡土为起点、以人地关系为背景,给我们展示了这一“土气”“土味”十足的乡土社会中的人物、事件、关系、情感、生计、信仰等画面。如何在“小生境”这一生态格局下,维持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同时,在对接“土气”这一乡土文化资源传统的同时,他们又不囿于传统,“破土而出”,进行“传统”的再造。从在同一乡土空间下的“离土不离乡”的农工相辅模式,到超越固有的乡土空间,进入到跨区域、跨网络的“离土不离乡”的“同乡同业”模式,如果以很多地方的经验来看,似乎是一种二元背反的行动模式。就像是接力比赛,这个接力棒一个一个传递下去,一直到最后的终点。然而,孙村的人们并没有按照“接力模式”持续他们的生活与生计;相反,他们的“接力棒”最后还是要传回到他们的家乡,用作者的话为一种“反向运动”,其实也是一种循环式的“反哺模式”,即重新回到“土”的范畴。我们还是回到本书,看看作者是如何来“动土”的。
一,“根深叶茂”与社会延续
中国东南沿海社会的研究,传统上以家族和宗族为切入点,来看区域社会的变迁轨迹。而福建的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的研究,宗族的研究更是经典之经典。不管是林耀华先生的《义序宗族》、还是弗里德曼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以及历史学家傅衣凌及其弟子们的研究,都给福建的民间社会的研究,刻上了“宗族”的烙印。似乎提到福建的社会研究,言必谈“宗族”。当我知道吴重庆教授关于他福建老家的书出版时,我脑子里第一浮现的形象,就是这里的“宗族”如何呢?然而,当我看到此书时,我一下呆住了。此书的写作方式已经大大有别于传统的人类学、历史学关于福建乡村社会的研究风格,完全独辟蹊径,简明扼要,没有兜来兜去,直奔主题,显得格外特别,让人为之一动。虽说其书写风格有其独特的个性,然其立论和所描述之社会文化诸项,又完全在人类学的学术脉络里展开讨论和对话。尽管作者没有把“宗族”作为社会结构研究的第一前提,但对于婚姻、家庭和亲属网络的研究,是其开宗明义的切入点。我们知道从人类学产生以来,这一研究是人类学的看家领域,就像RobinFox所归纳的那样:“亲属对于人类学就如同逻辑对于哲学、裸体对于艺术一样,是学科的基本训练。”特别是在汉人社会的研究中,亲属关系的研究是重中之重。我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末费孝通先生和李亦园教授的对话中,费孝通先生谈到“中国社会的活力在什么地方,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一个人不觉得自己多么重要,要紧的是光宗耀祖,是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看来继承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继承性这么强的。继承性背后有个东西也许就是kinship,亲亲而仁民。”[1]从中看出,费先生在强调文化的继承性问题,而能延续此种继承性的要素kinship(亲属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在中国汉人社会的亲属关系,主要通过家的文化观念和其社会性的结构和功能体现出来。
通婚圈正是亲属关系与社会空间研究的具体反映。作者把孙村的通婚地域大体划分为“核心”、“中围”和“外围”,在对于另外两个空间概念“祭祀圈”和“市场圈”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水利圈”的概念,并认为“水利圈”是直接影响通婚地域的重要因素,而前两个圈则不那么明显。在对婚姻方式的研究中,我们看到当地在上个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还存在很多特殊的形式,如换婚和买卖婚、“黑婚”(指未到法定婚龄不经结婚登记就暗中形成事实婚姻),与之相对应的称为“红婚”、计划生育和通婚地域、媒人与婚姻以及经济活动与通婚圈的关系等,都有非常到位的描述和分析。在通婚圈的基础上提出本村的姻亲圈,讨论婚姻及姻亲关系中的“例”行与“例”变。作者解释到,孙村所谓的“例”,乃是民间事关敬神拜祖、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的成规。在孙村的婚礼之“例”中,保留非常传统的“例”。即使连毛泽东时代,行古“例”以守护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如其婚礼过程从“亲迎”、“彩礼”、“成人”与“新妇”等一系列“走仪”(姻亲关系的维系,需要一系列有来有往的仪式表达,孙村人称为“走仪”。)。其“走仪”的核心目的并非我们今天城里人说的“合两人之好”,而是“合两姓之好”。作者引用当地“乡老”一句话,道出了传统农村社会婚姻缔结的真相。“‘长老’说,人家将女儿嫁过来,等于是给你家里“做一个祖”,能不感激人家吗?”。(本书29页)“长老”说的“做个祖”其内涵非常丰富,其核心是延续香火。其实,在中国的传统社会结构中,婚姻的结合并非是一平等的结合,婚姻本身的终极目的是男性通过这一结合繁衍自己的生命体,具有一种“借女生子”的男性霸权的意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把人生的意义和血缘的延续紧密地联系起来,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把祖宗的“香火”延续下去。作者在接下来对于姻亲关系互动过程中“送礼”与“还礼”、“恩与报”、“互惠与交换”等进行了讨论,认为““走仪”之“例”,之所以在毛泽东时代照样风行,乃因中国家庭及婚姻的核心价值并未受到冲击。作者在此强调的是传统的延续,而不赞成有的学者提出的“社会主义实践已经摧毁并以政治功能取代了传统仪式的主要社会基础”(本书33页)。然而,传统的延续并非一如既往,改革后所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孙村家庭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庭的分离与核心家庭的离土离乡,导致传统的“例”大打折扣,发生变异。特别是“黑婚”者,都转入了地下。对于当下孙村的婚姻与姻亲的讨论,作者超越结构与功能的分析,从变迁的视角进行了归纳,认为孙村姻亲关系进一步朝实用化、工具化的方向建构,可谓“其根深深”。作者在此埋下伏笔,提出孙村的年轻一辈却更期待“其根深深”---尽可能培育、利用、挖掘、建构姻亲的根系网络、期望小家庭“根深叶茂”----发家致富!(本书42页)。
二,人应还是灵应:民间宗教与社会结构
孙村的空间概念反映了村落社会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祖先及神灵的有机联系。而对于人与祖先和神灵,作者在书中用“阴阳界”为题展开论述。并以“共时态社区”概念来表述,鬼神分别作为“过去时”和“超现时”的社区成员,与现时的人一道,参与乡村事务。即“阳界”与“阴界”合二为一,是一个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大陆的民间宗教是否形成“新传统”?这些讨论的出发点,主要是把民间宗教置于社会与文化之中,来展开研究。民间宗教在一定意义上是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孙村这样的村落,村落之为社会,民间宗教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在探讨中国社会结构时,大多侧重于从经济或政治层面去研究,人类学则更注重从民间宗教的活动来认识社会结构。作者对于阴阳界的讨论,正好说明了这一观点。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一批卓越的人类学家,非常关注“文化”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对于民间信仰如祖先祭祀等,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把其置于社会结构中予以把握。如杨堃的博士论文《祖先祭祀》、林耀华的《义序宗族》与《金翼》、费孝通的《生育制度》,许烺光的《祖荫之下》等。之后的海外学者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如主要涉及的是民间宗教是否是一种宗教、民间宗教与“大传统”的关系、民间宗教与社会和文化的揉合以及民间宗教与现代化等问题。作者在书中,对于欧美人类学者沃尔夫(Wolf Athur P.)、王斯福(Feuchtwang Stephan)等提出的民间宗教的“神、祖先和鬼”的内容及其象征意义,结合自己的田野做了很好的拓展。其论述始终没有脱离民间宗教与社会的有机联系。
作者以差序与圈层的概念为基础,集中讨论人际关系与神际关系之关联。我们知道汉人社会民间宗教的神格体系与社会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我们的文化中,对玉皇大帝及天庭的想像和建构,与现实社会的等级体系相比照在一起。神圣世界的结构和秩序与世俗社会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书中通过对鬼、祖先、神明系统、童乩的神灵附体、神人沟通的灵媒、神明出游线路的规划、卜杯等阴阳互动的分析,得出在孙村“神际关系是由人际关系决定的,神明并不可能超越世俗的关系”(58页)的结论。以此为基础,人与神、阴阳两界、人鬼之间的交往方式有何特点呢?作者认为,孙村的人与神的交往方式,体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即“以阳间的子孙为中心点,鬼作崇于人的严重程度与其同中心点之间的距离成正比。”(62页)
对于阴阳两界的信息沟通是需要凭借神明的法力的。特别是孙村人在不断闯市场的背景下,男性大多外出,村里的中老年女性比例升高,导致连接阴阳两界的神明基本上都为女性。作者也认为女童乩与女信徒之间更可能发展出一种长远的友谊甚至是拟亲关系。并提出神明的女性化自是社会结构、社会心理投射到宗教信仰的反映。作者用“灵力资本”来解释“有灵”,所谓“有求必应”,并把“灵力”作为社会性的概念来把握。如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童乩灵力辐射范围变迁的规律,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童乩的灵力辐射半径由近及远。在空间上,童乩灵力的覆盖面并非呈圆形或扇形区域,而是呈圈层结构;在时间上,童乩灵力只有在内圈层的辐射力衰退之后才进而辐射到外圈层。”(81页)正如王斯福所言“‘灵’是一个由社会制造出来的概念,就像声望这个概念一样,它是外在于个人动机活动之外的”[2]。
从其研究中,我们感受到,民间宗教的研究本身涉及到个人、群体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我们看到随着孙村的变迁,社会结构中个体化行为与需求多样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当地民间宗教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迪尔凯姆很早就提到,就人们相信自己存在并调整自己的行为适应信仰的程度而言,信仰具有社会真实性。[3]因此,孙村人的民间宗教的目的多半在于解释日常生活,而且确实是通过与非同寻常之事的比较才使之成为寻常。民间宗教信仰使社会关系象征化并寄托着当地人对于未来的希望。所以,从迪尔凯姆到布朗、福特斯,再到约翰斯通的《社会中的宗教》,所呈现出的一个理念就是“宗教在社会之中”。约翰斯通认为:“宗教是对个人需要和群体需要的一种回应。在一个特定社会中,宗教信仰和解释的典型形式,是由这个社会的模式即相互关系的类型和复杂性从根本上决定的。”[4]而中国汉族的民间宗教特别是孙村的个案集中反映了民间宗教的社会特性。即民间宗教的运行逻辑,也反映了东南汉族社会的结构特点----差序性与圈层性的有机统一。
最后,作者超越民间宗教的社会性的讨论,通过“牵马人”这一底层社会的研究,引入生态学上“小生境”的概念,梳理了“牵马人”世界观的复合特点,建立了马、人以及神明之间的“均衡理性”,这一理性应该包含了个体、社会、自然以及超个体、超自然力量的中国传统儒家所谓的“天地人”系统。(参见本书109到110页)接下来,“小生境”概念的提出,对于如何发掘、提升民间宗教的研究,可以说提出了很好的参照体系。
三,民间权威与“借神行道”
人类学对于基层社会政治的研究,常常是从文化的角度看待政治过程,并把其置于社会整体中来分析,着重讨论与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家族组织等的关系。常涉及的一些概念有公共领域、社会整合、公共性、权力与权威等。与行为理论学派所强调的集中研究追求权力斗争的“政治人”的行为不同,人类学的研究更加侧重于人们的象征形式和行为,研究对象可以称为“仪式人”。作者对于民间权威的研究,通过筑路、“借神行道”,把修路过程引出的各种权力及利益要素的交错协调的过程,作者把其视为杜赞奇所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
这一“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其核心正是强调象征形式和行为,认为文化象征符号就是类似于习惯法一样的各种关系与组织中的规范[5]。他使用“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来说明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他的权力的文化网络中包括市场、宗族、宗教以及水利控制类等级组织以及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之间的非正式相互关系网。而乡绅则通过祭祀活动表现其领导地位,乡村的祭礼将地方精英及国家政权联络到一个政治体系之中。而孙村的民间权威在筑路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如何借助乡土文化资源,树立自己的权威性本身,就具有传统乡村社会的“乡绅”传统。然而,与很多传统乡村不同的是,孙村在1949年前的社会,由于土匪武装的猖獗,控制了村落社会的基层组织,如保甲制中的保长和甲长的产生,与民间权威的提名和支持与否毫无关系。用作者的话就是“民间权威授权来源的缺乏及其力量的弱化”(114页),而乡村社会逐渐的开放性,与外界的互动关系,似乎成为民间权威的新的授权来源。
1949年后,由于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成为一体的关系,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单位,为以集体为标签的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所取代。从土改到人民公社,乡村社会的组织运行完全依靠由上而下的政治整合力量,与个人的能力、民间权威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特点在大部分中国农村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学术界对于民间权威的研究,大多以此为开始。然而,在孙村,让我们打开眼界的是,这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很多生产队长,面对温饱都难以解决的现实,冒着“政治风险”,暗中组织村人“分田到户”。期间,他们为了顺应民意,利用神异资源,与神权联手,进一步树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居然,在那个特殊的时代,1977年神庙在孙村落成,一些民间权威具备了“神授”的公共身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一些民间权威有过威望顶峰的时期,但之后,当个人出现道德污点时,其权威受到挑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村民对于民间权威考察的道德诉求与功利取向。而在1985年之后,民间权威如“乡老”等,利用乡土资源中的宗教性特点,“借神行道”,建立起了威望。作者把这一现象总结为“正好可以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具有国家经纪人体制特征的基层政权所利用,而‘乡老’也因此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活动空间。”最后作者通过乡村公共事务以及“乡老”发起重修村道到村道修通的分析,对于国家经纪与民间权威的互动进行了讨论,弥补了杜赞奇“权力的文化网络”概念中,对该网络内各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未加确切阐述的不足,特别是以孙村为个案,勾画出了完整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示意图(见139页),对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孙村的社会文化网络特点做了很好的总结。在这里作者的网络概念,已经超越了单一的文化传统为基础的网络概念,而把社会传统和社会结构,有机地融合在对网络的重新建构中,形成了以社会为本体,以文化为参照的新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的解释框架。简言之,作者是以乡村社会的社会运行机制为基础,来审视“权力的文化网络”。
四,“出社会”与“内发型发展”
传统的孙村社会,不像我们一般理解的中国传统社会那种“男耕女织”、封闭式、自循环的乡村,其开放程度用作者的话说“超乎常人之想象”。本村的“男商女耕”和“男匠女耕”有着很悠久的流动型兼业传统。所以,孙村人把靠手艺外出谋生的“匠人”称为“出社会”。正因为有如此厚实的传统资源,进入到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出现了“打金”的手工业,进入到80年代后,逐渐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发财致富的支柱产业,并形成了“同乡同业”的亲缘地缘业缘网络。作者在讨论这一现象时也用费孝通先生提出的“离土不离乡”和“离土又离乡”来解释这一现象,并对“离乡”之乡提出了新的解释,即“‘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孙村‘离土’在外的‘打金’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乡’”。
在费先生的研究框架中,他特别强调社会和文化的延续性问题。而在该书中,作者从头到尾一直强调这一研究传统,但同时又有延伸。即既要回到“乡土范畴”,同时还要“破土而出”。破土就是“出社会”,而“出社会”需要社会资本,其基础就是乡土的社会资源。“打金”的孙村人创造出的经济形态,正是“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的相互嵌入”。(153页)这一有别于市场经济的这种经济形态,这种运行的模式是典型的非正规经济的表现,也是“内发型发展论”的具体表现形式之一。
上世纪70年代末,日本著名发展社会学家鹤见和子反思西方现代性时,提出了“内发型发展论”,她在很多著作和论文中明确指出其“内发型发展论”的原型来源有两个:一个是中国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另一个是日本的思想家、民俗学家柳田国男。而且费孝通先生开创的小城镇和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也是她构筑内发型发展论的实践事例。1989年,鹤见和子在执教20年的上智大学进行了最后一次讲演,题为“内发型发展的三个事例”,对于内发型发展的特点她表述为:内发型的发展是“适应于不同地域的生态体系,植根于文化遗产,按照历史的条件,参照外来的知识、技术、制度等,进行自律性的创造。[6]同时她进一步分层论述,她认为内发的发展,文化遗产以及广泛意义上的传统的不断再造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所谓传统主要指在某些地域或集团中,经过代代相传的被继承的结构或类型。她强调的是“为特定集团的传统中,体现出来的集团智慧的累积”。而孙村的“同乡同业”的发展模式,正是植根于当地的传统而体现出来的集团的智慧。进而作者提出“同乡同业”经济活动的生命力,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总之,本书对于孙村的讨论,在我看来把人类学的“社会研究传统”和“文化研究传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其背后有个文化传承的维度,特别是儒家思想和文化如何投射到孙村社会的过去和现在。这就是作者强调孙村社会的延续性的同时,也把这种延续性与中国文化的传承性联系在一起进行思考。
此外,在书中,空间的维度,也是理解孙村社会与文化的不可或缺的视角。作者把孙村看成是一个社会的空间,其变迁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空间的生产过程。正如齐美尔在其论文《空间的社会学》中所言,空间正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事实上,如果空间离开了社会的维度,也就没有其具体的研究对象。如作者对婚姻、亲属网络以及“离土又离乡”的“出社会”的立论,首先是从空间及其社会生产的角度予以展开。孙村人的通婚圈正是亲属关系与社会空间研究的具体反映。而“同乡同业”与孙村人的“出社会”,所借助的乡土资源与通婚圈、姻亲圈等密切相关。同时,固有的乡土空间通过“出社会”的“打金”群体,已与跨区域的空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空间对接结构,让我们感到从孙村出来的这一群体似乎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一个跨区域的孙村社会已经形成。
(附记:我想补充说的是,本书附录中的“乡土社会的‘小写历史’:革命前及革命时期的孙村”一章,是本书中非常精彩的部分,这里详细记录了作者的父亲对于孙村的口述历史,是我们了解孙村社会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作者把当地的民间概念,活灵活现地应用到村落历史的描述中,给我们做同类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个案。限于篇幅,我不能展开讨论。)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吴重庆著,法律出版社,2014年6月)
注释:
[1]《费孝通文集》第14卷,第387-388,群言出版社
[2]王斯福:《帝国的隐喻》,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8页。
[3]参见彼得·贝格尔:《神圣的帷幕》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罗纳德·L·约翰斯通著,尹今黎、张蕾译,袁亚愚校:《社会中的宗教——一种宗教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5-56页。
[5](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6]鹤见和子著《内发的发展论的展开》,筑摩书房,第9页,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