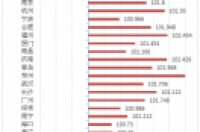7年来,由政府出台的非比寻常的刺激计划为世界经济提供了支持。如今,世界需要摆脱对非常规货币政策的依赖,致力于实现私营部门主导的增长。美联储加息犹如吹响了号角。中国市场遭受的重创突显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也说明有必要采取新举措。2016年或许可以从三个主要方面入手来促进增长。
首先,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警告,由于全球需求不足,世界存在“长期性增长停滞”的危险。他还将已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化趋势放在上世纪30年代末兴起的一种理论之下来阐述。萨默斯担心,新兴市场将面临全球需求低迷、资本流出、投资前景变差以及汇率贬值。在缺乏新需求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将拖累发达国家,这反过来将进一步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
根据这种理论,作为世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增长来源,中国正面临艰难转型,即从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重心的经济。在全球经济状况不佳的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将通过货币贬值,以吸引有限的需求,这将引发其他国家采取保护主义的对抗措施。解决办法是大规模政府支出,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通过以极低利率借款融资。
在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看来,全球经济正处于债务“超级周期”的较晚期阶段。他提供了第二种视角。罗格夫教授所教的历史课表明,随着金融过度行为(financial excess)所造成的负担逐渐减轻,增长将复苏,不过会相当缓慢。系统性市场危机——一股全球性风暴,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的住房市场崩盘、欧元区债务危机,以及中国和新兴市场的金融动荡——已经惩罚了全球经济,并判了很长的缓刑期。
如果罗格夫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萨默斯提出的大规模政府支出只会拖延这种债务顽疾。相反,罗格夫教授会着眼于减轻债务人的困境,具体做法包括将利率保持在低位或者负值,并重组债务,同时为生产性投资创造条件。他也看到了基础设施投资的好处,不过他对浪费性政府项目感到担心。
第三个增长方案是将政策重点重新放在提高生产率和增长潜力,特别是在私营部门。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和前美联储理事凯文•瓦尔许(Kevin Warsh)等供应学派担心,非常规政策会扭曲私营部门对投资、利润、税收、估值和未来政府行为的预期。他们强调,会推动私人资本投资(从而推动薪资和利润的增长)的需求是预期的未来需求。相比之下,旨在促进短期需求的政策实际上在未来可能会抑制企业信心;它们可能会依赖合并、收购和股票回购,而非长期巨额投资。
同样,其他人呼吁通过税收和监管政策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和就业。此外,开放贸易政策、旨在提高劳动参与率的鼓励政策(包括针对女性和残疾人)、合法移民以及更有效的教育和培训可能也会提高潜在经济增速。创建鼓励科技进步的科学、教育和创业环境将创造机会。问题是,事实证明,这种结构性增长改革在政治上很难实施。在民粹主义者和本土主义者的崛起使政治领导人受到震撼的情况下,依赖政府支出或央行会更加容易。
2016年最重要的问题是,各国是否会勇敢地推行关键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和很多其他新兴市场而言,这些改革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之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需要射出他的“第三只箭”,包括引入竞争、加强公司治理以及鼓励更多女性就业。对于欧元区而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工作和投资激励以及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对于美国而言,问题是公众是否会选出将携手重燃私营部门活力的总统和国会。
如果在2016年没有出现从货币政策向增长政策的转变,那么萨默斯和罗格夫所设想的未来成真的可能性更大:增长乏力;汇率冲突;以及民粹政治和分配斗争——由于举步维艰的经济停滞不前,还可能不时爆发小规模危机。政治领导人要么现在努力塑造本国的命运,要么等着十年经济试验的秋后算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