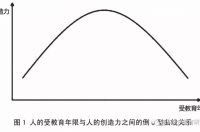2.7亿的中国流动人口中绝大部分是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受制于内在的经济因素、社会资本以及外在的公共政策,他们在社会流动的过程中会针对是否携带子女入城就学作出不同的家庭决策,进而产生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问题。
到2015年,中国共有流动儿童约3600万,占全国儿童的13%,留守儿童约6100万,占全国儿童的22%。教育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201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为1.38亿,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和农村留守儿童数已分别达1294.73万和2075.42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总数已占到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一个规模极为庞大的群体,他们的父母加入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自发的劳动力迁徙大潮,使中国这个庞大的落后农业国家,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成为制造业和数字化的世界性大国,GDP增长幅度全球第一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难以忽视的是:近1亿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所孤独承担的情感负债和社会软肋。
近年来,诸如“流浪儿垃圾箱死亡”“乡村留守儿童集体自杀”“校车事故伤亡惨重”“留守儿童弑杀乡校老师”“留守女童被性侵”“乡村孩子组建帮派形成类‘黑社会’”等一系列屡屡刺激社会敏感神经的公共事件频频发生,并引发社会舆论对这1亿子代展开集体反思。然而在反思的背后,却只能展开技术性的修补和改善——作为经济高速推进中不可避免的制度性衍生,可以预见他们将引发的社会问题,将在中国版图上长期持续存在。
各级各类政府对于城市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不可谓不重视,自上而下,层层分解实施,并督导强化落实的各级政府关爱服务项目和关爱服务社会购买项目不可谓不丰富,关爱指标也不可谓不细致,然而,关爱效果却总是不够理想。
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5CSH012)持续深入底层乡校,试图把脉和反思这套关爱体系的脉络,探寻西部寄宿制学校中底层孩子们的日常微观生活世界。
随着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全国农村寄宿生群体规模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农村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的承载主体。根据教育部规划司2011年统计数据: 2011年全国农村初中生总体寄宿率达到52.88%,16个省初中生寄宿率超过了50%,6个省超过60%,西部12省区明显高于全国,整个西部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寄宿率达到34.30%,其中,初中学生整体寄宿率达到62.36%,小学生寄宿率达到19.65%。
寄宿制学校是如何占据了农村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关系紧密。新世纪以来,中国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一、中央——地方政府“双强”撤并阶段(2000年到2005年)
在该阶段中,一方面,为加速推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中央政府在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基础上,以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3年)等系列文件的颁布为标志,作为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的重点工作,大规模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开;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此处尤指“县级政府”)在“以县为主”的新义务教育管理体制下,加速推进本县域内大规模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
从内部动因来看,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缺位和人员编制紧张的双重困局,倒逼县级政府不得不加快压缩教育行政管理幅度和节约教育行政成本,进而将有限的教育资源集约化整合以求形成可视化的教育规模初步效应;从外部动因来看,国家层面设立的“中小学布局调整专项资金”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专项资金”,进一步刺激县级政府加速推进农村学校布局结构的大规模调整。
在中央——地方政府“双强”撤并阶段,全国小学数从2000年的55.36万所锐减至2005年的36.62万所,小学在校生数从13013.25万人减至10864.07万人,专任小学教师数从586.03万减至559.25万;全国初中数从6.39万所减至6.24万所,初中在校生数从6256.29万人减至6214.94万人,全国初中专任教师从349.21万人减至328.69万人。
中央——地方政府“双强”撤并阶段中,在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为17.28%的前提下,小学数减幅高达33.86%,而小学专任教师数减幅仅4.6%;在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幅仅为0.67%的前提下,初中数减幅为2.3%,而初中专任教师数减幅则达到了5.9%。
中央和地方政府“双强”撤并阶段中,以“撤点并校”为核心的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主要来自于“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的被撤并,其绝对主体是小学。
二、中央——地方政府“中——强”撤并阶段(2006年到2012年)
在该阶段,过去由中央——地方政府“双强”撤并所带来的弊端已日益凸显:
一方面,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的推进,使中央政府对地方实施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提供了现实的奖励、支持和考核依据,省级政府得以迅速制定量化的硬文件指标,短期内迅速出台指标式撤并计划,从根本上使县级政府有强大动力展开锦标赛式的政绩竞争,这种竞争往往使具体治理主体在结果主义的目标驱动下,越过利益相关人的集体同意而单向度制定利己的撤并标准,一刀切和运动式的撤并,往往以村落社区和当事人或“不知情”或“精英动员”或“质量承诺”等方式推进,很难做到因地制宜和实事求是。
另一方面,农村学校撤并后一系列具体的现实弊端注定要日渐被直接当事人——学生、家长、教师、村民等普通个体、家庭所承担和吸收,如过度撤并的后果是使无法住宿的学生“上学距离过远”,从而直接增加其日常负担,且蕴含较高的安全与辍学风险、增加家长的额外开支、增大学校教师的风险责任和管理幅度等;对于能够提供住宿的寄宿制学校而言,因教师和生活教师编制不够,规训化、惩戒式的日常教育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使住宿学生面临情感、心理、安全、营养与暴力等多重威胁,且他们多半为留守儿童。另外,撤并动员时政府、村委、能人、亲属等多重主体在村庄共同体中所作的教育承诺,在移居新学校就学后却发现往往见效缓慢或毫不见效——老师依然是以前的老师,教学依然是以前的教学,再加上现实村落社会中大量底层孩子在城乡一体化的教育筛选轨道中,被结构性的过早抛入社会,进而使村落农户家庭因承诺而膨胀的教育乌托邦想象不断被击碎。
2006年后,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逐步成为改革的主流,中央政府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将“单向度撤并”导向调整为适度“保留”和“建设”导向,教育部明确要求各地要改变“大撤大并”的过激方式,“方便入学”被作为布局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而被强调。事实上,通过政策文本分析,明显发现2006年后中央政府几乎再无对学校撤并的任何文本表述。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国家政策的核心精神是在适应城乡社会发展和学龄人口客观变化的基础上,以优先方便学生“就近入学”为前提,合理布局农村学校,防止一刀切的简单“撤点并校”,规范布局调整程序,听取人民群众意见,避免因布局调整引发新的矛盾。
可见,中央政府对撤点并校的动力源已经由强减弱,这是“效率”导向到“民生”导向的治理思路转型,但这种转型并不意味着对农村学校撤并的彻底叫停,中央政府依然保留了“中等”强度的撤并动力。尽管中央政府明确要保留并加强建设必要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但“必要”的认定标准却一直十分模糊,且对于“必要”的“认定权”和“具体标准”都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县级政府决断,没有建立起一套能够有效相互制衡的撤并程序和治理结构。
因此,尽管中央政府的撤并动力已经由强转中,但囿于地方政府现实的财力、管理和政绩考量,地方政府依然具有强大的撤并动力,在整个“中——强”撤并阶段的7年间,几乎无任何地方政府出台叫停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政策文件。
2006到2012年数据显示,全国小学数从2006年的34.16万所锐减至2012年的22.86万所,小学在校生数从10711.53万人减至9695.90万人,专任小学教师数从558.76万人减至558.55万;全国初中数从6.09万所减至5.32万所,初中在校生数从5957.95万人减至4763.06万人,全国初中专任教师从347.5万人增加到350.44万人。在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仅为9.5%的前提下,小学数减幅高达33.07%,而小学专任教师数减幅仅0.04%;在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幅为20.05%的前提下,初中数减幅为12.6%,而初中专任教师数则增加了0.8%。
与上一个阶段相比,尽管中央政策在这一阶段从宏观上减弱了撤并动力,并为“撤点并校”持续降温,但实际上在地方治理实践中,撤并问题最突出的依然是小学为主体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甚至其撤并激烈程度远远高于以前。
三、中央——地方政府“弱——中”撤并阶段(2012年至今)
尽管全国各地围绕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而发生的各种事件日渐频发,但真正促使全社会舆论集体反思,并加速中央政府下大力度彻底叫停全国大规模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则是发生在2011年末的几起校车安全事故。公共社会舆论在对校车安全性展开集体追问的过程中,逐步将反思矛头上升到对“撤点并校”本身的质疑。中央政府颁布更为严厉的政策,以叫停地方大面积的学校撤并热潮。
2012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农村中小学要因地制宜,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就近入学的关系。
而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教育部2012年工作要点》首提要“审慎”推进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坚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
2012年3月,针对直接的校车安全事件,国务院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
2012年8月,国务院再次出台《关于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意见》,首次从中央政府的角度,确定寄宿制和非寄宿制学校的比例。
2012年9月7日,国务院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正式出台了对于后来彻底叫停农村学校撤并起到重要作用的文件——《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随后一系列更为细致的配套性政策文件出台。这些具体的政策文本更是清晰传递了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就近入学”的原则反对地方膨胀过度以至于早已偏离合理轨道的大规模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通过经费保障、学校改造、师资倾斜、信息工程、督导检查等方法措施,长期保留并办好一定数量的村小学和教学点。
这真正标志着中国学校布局结构调整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具有明显的弱动力去开展新一轮大规模的“撤点并校”。
校车安全事故发生后,社会公共舆论也促使地方,特别是省级和市级政府采取措施急刹车。事实上,省级和市级政府在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中的工作职责和利益结构,使其可以相对较快地进行正常政策调整。
县级政府事实上是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的最终决定者,并负有主要责任:县级政府需要将调整优化的中小学布局规划,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统一规划,在此基础上制定调整优化布局结构的工作方案;县(市、区)制定的规划和方案要具体到学校、年级和班,严格按人口出生率变化控制年级数、班级数和班额;审批管理辖区范围内初中、小学的设置和调整。
事实上,对于县级政府而言,即便是在中央、省、市各级政府大力叫停乡校撤并的政策出台后,也具有内在复杂的强撤并动力:
一、从内部来看,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教育统筹等一系列如火如荼的中国教育改革和政策实践,使县级政府不得不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采取一石二鸟的办法,一方面以减少学校、教师、运行成本作为直接目的,撤并农村小规模学校可直接节约地方财力开支;另一方面将集中的地方财力用于兴建教育园区或教育新城,此举不仅可以节约地方财力,还能推进实现本县域内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发展,达至城乡教育一体化和城乡教育统筹,实现教育绩效;
二、从外部来看,撤并农村学校作为县级政府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的柔性手段日益有效。教育园区或教育新城致“学校进城”的背后,是人和资本的向城性流动与集聚。作为拉动城镇化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撤并显然承载了县级政府更多的非教育意义。故在中央政府强力叫停,地市级政府着手恢复农村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的前提下,县级政府依然保有中度的撤并动力。尤其是中国西部人口大县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县,他们之前就因财力和人口等因素,推进农村大规模的学校撤并相对滞后,在城镇化作为地方重要发展指标的当下,撤并往往只能用隐性的方式来推进。
2012到2014年数据显示,全国小学数从2012年22.86万所锐减至2014年的20.14万所,小学在校生数从9695.90万人减至9451.07万人,专任小学教师数从558.55万人增至563.39万人;全国初中数从5.32万所减至5.26万所,初中在校生数4763.06万人减至4384.63万人,全国初中专任教师从350.44万人减至348.84万人。在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幅为2.5%的情况下,全国小学数的减幅为11.9%,小学专任教师量则有0.9%的增幅;在初中在校生人数减幅为7.9%的情况下,全国初中校数的减幅为1.1%,初中专任教师的减幅为0.5%。
由此可见,尽管关于撤并的急刹车迄今仅实施了4年,但从已公开的3年数据来看,相比前两个阶段,小学校数量减幅确实有所下降,初中的撤并减幅也远低于上一个阶段。持续10余年之久的大规模撤点并校确实得到了部分有效遏制。
四、农村寄宿制学校中的关爱体系正在发生核心困难
在如火如荼地多重类型加速推进的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这些留守儿童注定要脱离乡土,成为城市工业文明分工体系链中的下一代劳动者。他们不得不在寄宿制学校中,有意无意地提前学会在未来的世界工厂中如何做工并达成理所当然的自我认同,由此,寄宿制恰恰提供了这样一套减少未来心理震荡的公共空间。
事实上,来自成人世界的关爱体系,目前正主要发生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中:寄宿制学校。
在这个基础上的关爱体制注定产生两项核心困难:
一、关爱体系建构并不真正建立在对留守儿童日常行为长期田野观察和深度研究的主体需要上,关爱者“中心化”“粗放式”“随意性”的关爱较为普遍,很难展开更为精细的个体化和分层分类关爱项目实施,相反,关爱体系科学建构的经验信息,多来自于被媒介公开描摹而被话语定型化的部分留守极端个案,这些个案极容易被过分渲染而给整个留守儿童群体贴上恶意的社会标签。
例如,在笔者的大量田野调查中,发现随着心理叛逆期和个体社会化的提前,底层乡校三年级以上、与父母分离持续半年以上的绝大多数男孩,并不太愿意见到父母,同辈群体给他们提供了另一层温暖,这种温暖与来自父辈和学校的关爱不应冲突,但现实却是平级的关爱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解构了自上而下的关爱。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个体心理保护,还是一种无意掩饰的真实社会心理状态?暂时不得而知,这显然需要研究者深入中国底层村落,做科学严谨的实验观察,方可提供科学有效的关爱体系,从而打破目前关爱体系动不动就是毫无检视而一成不变的“父母亲情”“临时妈妈”等项目逻辑;
二、关爱与现实的学校规训彼此混淆,不是通过恢复留守儿童在校园里的“主体性”和“自由空间”,而是用无数的“禁止”和“规训”去弥补教师,尤其是生活教师的不足,而单向度只能依靠“控制网”去减少留守儿童违规的现实,“保证安全即是给予关爱”的潜在逻辑,恰恰偏离了关爱体系建构最为核心的精髓:在劳动力大量外出的现实下,如何让学校成为留守儿童真正喜欢的地方。
由此,在这套成人世界关爱体系南辕北辙的持续性实践下,中国西部地区寄宿制学校中的留守儿童往往可能陷入越被关爱却越规训和抗争的痛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