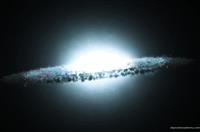一、缘起
最近,笔者出席了在韩国成均馆大学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①],因为在韩国儒家的话语中,“儒教”(??)与“儒学”(??)在用法上通常没有什么根本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此次会议的主题其实就是“生活儒学”。对此,笔者感到非常亲切,因为笔者十多年来建构的儒学理论正是“生活儒学”[②]。
但是,在其它地方,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儒教”与“儒学”却是涵义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③] 所以,成中英先生在会议开幕的主题演讲中明确区分了“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④] 笔者本人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也特别强调了“儒学”与“儒教”的区别。[⑤] 不过,此次会议本身并没有“生活儒教”和“生活儒学”的区分;韩国儒教学会会长金圣基教授在会议最后的致辞中,用汉语称笔者为“‘生活儒学’的先行者”,他所说的“生活儒学”就是指的会议主题“生活儒教”。
此次会议另外一处未加区分的地方,则是两种不同意义的“生活儒学”。这是本文将要详加辨析的两个概念。众所周知,“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其中,台湾地区的代表是龚鹏程教授,大陆地区的代表就是笔者本人。[⑥] 此次会议以“生活儒学”为主题,标志着中国学者所提出的“生活儒学”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或者说正在国际化。不知是否出于主办方的有意安排,在这次会议上,龚鹏程教授做了会议开始的主题发言,而笔者做了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
成中英先生在其提交的论文中提到“山东有学者提出‘生活儒学’的概念”[⑦],即是指的笔者本人的“生活儒学”;但笔者的“生活儒学”远不仅仅是提出概念,而是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生活存在论”或“生活本源论”;[⑧] 作为形上学的“变易本体论”;[⑨] 属于形下学的“中国正义论”[⑩]、以及“国民政治儒学”[11];等等。正因为如此,笔者的“生活儒学”被列为“新世纪大陆新儒家”六家之一[12]、“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十家之一[13]。
本文之所以要辨析两种不同涵义的“生活儒学”,是因为两者的意义是截然不同的。为此,本文称龚鹏程教授的生活儒学为“生活的儒学”(Confucianism of Life)(这也是龚鹏程教授自己的叫法)[14](此次韩国会议的主题“?????”汉译为“生活中的儒教”亦属此类),以区别于笔者的“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15]。
龚鹏程教授“生活的儒学”的基本宗旨,是“主张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16]。这显然是对20世纪以来的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批评,认为他们仅仅将儒学视为“生命的学问”[17],而忽略了“生活”。而“生活的儒学”则主张:
扩大儒学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而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除了讲德行美之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修六礼、齐八政、养耆老而恤孤独、恢复古儒家治平之学,让儒学在社会生活中全面复活起来…… [18]
显然,这样的“生活的儒学”是指的既有的儒学在现代生活实践中的应用,就是把现成的儒学运用到当下的生活实践中。此次会议的论文,大部分都是这样的“生活的儒学”或“生活中的儒学”,并表达为这样一些措辞:“活用”、“现代活用”、“激活”、“活性化”等。
1、这里所谓“儒学”,究竟是指的怎样的儒学?那是孔孟的原典儒学,还是帝国时代的儒学,或是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19],或是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20]?
众所周知,儒学从来不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的:自从孔子之后“儒分为八”[21],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之儒学,而同一时代亦有不同学派之儒学。因此,所谓“儒学”岂能一概而论?如果承认儒学乃是“周孔之道”而从周公算起,那么,历史上存在过宗族王权时代的儒学、第一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尤其是孔孟荀的儒学)、家族皇权时代或者帝国时代的儒学、第二次社会大转型时期的儒学(包括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22]
那么,面对儒学的这些不同的历史形态,我们究竟应该“活用”哪一家、哪一派呢?是程朱理学、还是陆王心学?是宋明理学、还是汉代经学?更根本的问题是:选择的标准何在?这些问题,都是“生活的儒学”无法回答的。
2、既然儒学需要“激活”、“复活”、“恢复”,那显然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也就是宗族时代(王权时代)或家族时代(皇权时代)的儒学。然而,这样的儒学能够照搬到今天来吗?
他们所谓“儒学”正是指的前现代的儒学,因为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21世纪的大陆新儒学是无所谓“激活”、“复活”、“恢复”的。但是,这样的前现代的传统儒学,今天能够、或者应当“激活”、“复活”、“恢复”吗?下面简要加以分析:
我们知道,秦汉以来的帝国时代的儒学,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建构一套形上学,来为一套形下学奠基。这其实是古今中外所有哲学形而上学的共同的基本架构:设定一个唯一绝对的“形而上者”,用以阐明众多相对的“形而下者”何以可能。且以宋明理学为例,其形而上者就是心性天理,其形而下者就是帝国时代的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这样的传统儒学,可称之为“帝国儒学”。
(1)帝国儒学的形下学,其基本内容是皇权时代的一套伦理政治规范及其制度,其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试问:今天的中国还应“激活”、“复活”、“恢复”这样的东西吗?
不幸的是,今天确有一部分儒者在做这样的事情。他们试图“激活”“三纲”[23]:
他们“活用”“君为臣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皇权、专制主义。他们试图重新抬出一位君主、或者某种变相的君主。为此,他们反对自由、民主,鼓吹某种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在国际问题上,他们借传统儒学“家国天下”的话语来鼓吹某种帝国主义。
他们“活用”“父为子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父权、家族主义。为此,他们鼓吹所谓“孝道”,号召诵读《孝经》。不仅如此,他们还将这种伦理性的“孝道”政治化,大讲所谓“国父”[24]、“国母”。他们有意无意地鼓吹《孝经》的主题“移孝为忠”[25],忘记了原典儒学的原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26]。“孝”本是子女对于父母的一种本真的情感,却被伦理政治化;“移孝为忠”乃是家族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原则,所以专制君主总喜欢侈谈“以孝治天下”。“激活”这样的传统,意图何在?
他们“活用”“夫为妻纲”,试图为现代中国人“恢复”夫权、男权主义。他们反对男女平等、女性独立自主,试图以这种传统儒学来“安顿”现代女性。[27]
以上分析并不是说传统儒学的所有内容都过时了,而是说传统儒学的形下学、伦理政治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已经过时了。所谓“过时”是说:这种帝国儒学曾经适应于前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却绝不适用于现代性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2)帝国儒学的形上学,历经帝国前期的汉唐儒学、帝国后期的宋明儒学两大阶段,后者尤其“精致”,不论程朱的“性即理”[28]、还是陆王的“心即理”[29],都是将“心性”与“天理”合起来,视为“形而上者”,用以解释万事万物、特别是论证帝国时代的伦理政治何以是必然而且当然的。这样的“性理→伦理”的关系,也是“形上→形下”的奠基关系。
但是,这样的先验论的“性善”人性论,不仅并不被现代人接受,而且即便古代儒家也未必认同,例如著名的荀子“性恶”论、王夫之“性日生日成”论。尤其是后者,认为“‘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30],更接近于人性的真相,也更接近于笔者“生活儒学”的观念:现实的人性并非什么先验的或先天的东西,而是在生活中形成的。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现代中国、当今世界来说,帝国儒学整体上是颇成问题。这样一来,我们面临这样一种严峻的问题:这样的传统儒学,难道应当加以“激活”、“复活”、“恢复”吗?我相信,今天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女性,绝大多数会持否定的态度。这也表明:“生活的儒学”的致思进路根本上是站不住脚的。
这里更根本的问题是: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儒学”?上文谈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中,儒学开始建构自己的形上学,以此为其形下学奠基;自那时以来,传统儒学就是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大块构成的,由此形成了“形上-形下”的基本架构,而表述为“本-末”、“体-用”、“性-情”等等。这种“形上-形下”的架构其实也是中外普遍的现象,西方哲学亦然。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势必面临这样一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假如全部儒学就是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大部分构成的,而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两大部分都是成问题的,那就意味着:中国人如果选择现代化,那就必须彻底抛弃儒学。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所持的就是这样的态度。
假如中国人坚持这种传统儒学,那就意味着:中国人就别无选择,只能拒绝现代化。我们注意到,这正是今天某些“原教旨主义儒家”的选择:他们拒绝现代化,拒绝现代文明价值。
但是,以上这种“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是有一个观念前提的,那就是:全部儒学不外乎形上学(心性本体论)、形下学(伦理政治学)两大部分、或者说是两个观念层级。然而这个前提已经遭到了20世纪以来的思想前沿的解构:两千年来的哲学,包括帝国儒学,遗忘了、或者说是遮蔽了某种比“形而上者→形而下者”更本源的存在观念——“生活”的观念。
“生活的儒学”亦然:他们所谓“生活”是针对的现代人的生活,然而他们所谓“儒学”却是既有的、亦即前现代的儒学。用前现代的儒学来指导现代性的生活,岂不吊诡?这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不论是前现代的生活,还是现代性的生活,都不过是生活的某种具体的显现样式而已。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的儒学”并不理解生活。
笔者的“生活儒学”正是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假如儒学就是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观念层级构成的,那我们今天就必须从整体上抛弃儒学;反之,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儒学的某种传统,同时要选择现代化,那就意味着:儒学绝不仅仅由形上学和形下学这么两个观念层级构成,它必定还具有某种更为本源的观念层级。笔者相信:这种被遮蔽或被遗忘了的观念正是孔孟原典儒学固有的观念。
因此,“生活儒学”的宗旨,首先是重新发现和揭示这样的“大本大源”。这就是“生活本源论”(Theory of Life as the Source)或“生活存在论”(Theory of Life as Being)。[31] 在这样的本源上,才能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建构儒家的“变易本体论”[32])、形下学(建构儒家的“中国正义论”[33]、“国民政治儒学”[34]),从而有效地展开既是儒家的、又是现代的社会生活,也才能避免陷入原教旨主义的危险。
为此,“生活儒学”采取了当今世界思想前沿的发问方式“存在者何以可能”,即追问:“形而下者”何以可能?“形而上者”何以可能?这是因为:不论是“形而下者”、还是“形而上者”,都是存在者(存在着的东西)(beings)。这些存在者,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中谓之“物”:要么是作为形而上者的“道之为物”[35],要么是作为形而下者的“万物”[36]。而原典儒学要追问:物是何以可能的?
关于这个问题,儒家经典《中庸》指出:“不诚无物”;“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37] 这就是说:诚本来不是任何意义的物;然而如果没有诚,那就没有任何物的存在;是诚生成了万物——作为主体性存在者的“己”、作为对象性存在者的“物”。由此也就给出了“主-客”架构,于是才可能有形下学层级上的知识论、伦理学以及政治哲学的建构。
那么,“诚”是什么意思?“不诚无物”的命题意味着:诚不是物,即不是任何意义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诚即存在。然而在儒家的话语中,“诚”其实就是说的真诚的、本真的情感:仁爱。儒家所说的“诚”或“仁爱”,有时被视为作为形而上者的天道,即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有时又被视为作为形而下者的人道,即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38] 但“诚”本来是指的作为自然情感的仁爱:“樊迟问仁。子曰:‘爱人。’”[39] 这就是说,“仁”就是“爱”的情感。
这样的仁爱情感是生活中的自然情感,而归属于生活,所以谓之“生活情感”[40];在这样的生活情感中,生成一种“生活领悟”[41],这是一切物、存在者的观念的本源所在。[42] 但须注意,在原典儒学的观念中,这样的生活情感并不是指的通常所谓“人”或“主体”所具有的情感,因为人或主体反倒恰恰是由这样的生活情感生成的,这就是上引《中庸》所说的“成己”、“成物”:既生成主体性的存在者(己),也生成对象性的存在者(物);既生成形而下者(万物),也生成形而上者(道之为物)。惟其如此,诚或仁爱情感才是万事万物的“大本大源”。在古今中外的思想观念中,唯有原典儒学才有这样的观念。
这样的诚或仁爱情感,其实就是存在、就是生活,或者说是生活存在的原初显现。但此所谓“生活”并不是说的某种具体的“生活方式”,因为生活方式只是生活的具体显现样式;而此所谓“存在”也不是说的某种具体的存在者之存在、具体的物或人之存在,因为一切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给出的。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即存在,存在即生活。正是这样的生活存在,生成了一切存在者、物,给出了一切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如图)
综上所述,在原典儒学的观念中,爱即存在,存在即爱;爱即生活,生活即爱。打个比方:生活存在、生活情感、仁爱情感的地位,犹如创造世界的上帝。当然,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因为在儒家的观念中,上帝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者,仍然是由生活情感、生活领悟给出的。假如没有基督徒那样的生活方式,就不可能有基督教的上帝观念。
这也意味着: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的重建由此得以成为可能。换句话说,这就可以保证:尽管我们解构了帝国儒学的那套形上学、形下学,但我们所建构的却仍然是货真价实的儒学。
上文谈到,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下学主要是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哲学,其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父为子纲”的家族主义、“夫为妻纲”的男权主义。这一套东西不能适用于现代社会。但这并不是指的儒家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一般原理,恰恰相反,这套一般原理是适用于任何历史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因此才会出现不同历史时代的儒家伦理体系及其政治设计,包括宗族王权时代(夏商周)、家族皇权时代(秦至清)、个体民权时代(现代)。当今儒学界之所以出现种种偏差,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一套原理,而固执于皇权时代或王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哲学,从而陷入原教旨主义。因此,生活儒学的形下学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儒家伦理学及政治哲学的一般原理,这就是“中国正义论”[43]。简述如下:
(一)礼:伦理规范
儒家最关注的是群体生存秩序问题,生活儒学亦然。群体生存秩序在观念领域中的反映,即所谓“人伦”或广义的“伦理”(ethics),其实就是一套社会规范(social norms)及其制度(institutions)。这套制度规范,儒家称之为“礼”。换句话说,所谓“礼”即是指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例如一部《周礼》[44],其实就是一整套社会规范建构和制度安排。[45]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作为“群学”[46],乃是“礼学”。
说到儒家的“礼”,我们发现,不仅社会上、而且儒学界内部都存在着认识上的严重误区,这导致当前儒学复兴中普遍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往往以前现代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来评判现代性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现代人的行为方式。这是由于人们未能明白,在周孔孟荀的原典儒学中,作为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礼”有两个层面的意义:
1、礼的普遍性和永恒性:克己复礼
确实,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任何社会群体都需要一套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即都需要一套礼;就此而论,礼是普遍的、永恒的。所以,孔子指出:“无礼则乱。”[47] 荀子讲得更为具体: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48]
为此,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49],即克制个体的情欲、而遵守社会群体的规范及其制度;否则,“不学礼,无以立”[50],即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必定为这个群体所不容。这一点直到现代自由社会依然是成立的,因为自由的保障是法治(rule of law),而法治意味着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及其制度成为社会的最高规则,即没有任何人或组织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如果仅仅这样理解“礼”或社会规范及其制度,那还是偏颇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因为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生活方式需要不同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例如宗族社会的王权制度、家族社会的皇权制度、现代社会的民权制度。这就意味着:
2、礼的特殊性和变动性:礼有损益
据《论语》载: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51]
孔子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有所不同;可以预料,周代之后的若干代,其礼也必定是有所不同的。确实,中国社会的制度规范经过三个最大的历史形态:宗族王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家族皇权社会的制度规范、个体民权社会的制度规范。在这些大的社会形态中,还存在着许多具体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局部变革。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本质上是“革命”的。
我们将孔子的这个思想概括为“礼有损益”。对于现存既有的制度规范体系、即“礼”的系统来说,所谓“损”就是去掉一些旧的内容,所谓“益”就是增加一些新的内容,其结果就是一个新的伦理政治体系。而原教旨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得孔子所讲的“礼有损益”的道理。
于是,这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在选择或建构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的时候,所根据的价值尺度或价值原则是什么?这就是“义”,亦即所谓“正义原则”。
(二)义:正义原则
在这个问题上,孔子的表述是“义以为质,礼以行之”[52],意思是:义是礼的实质,而礼只是义的实行、实现形式。这其实就是孟子“仁义礼智”理论结构中的“义→礼”结构。这就是说,我们是根据正义原则(义)来进行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的建构或选择。
作为正义原则的“义”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正当、适宜。孟子说:“义,人之正路也。”[53] 这是“义”的“正当”含义。《中庸》说:“义者,宜也。”[54] 这是“义”的“适宜”含义。据此可以从“义”的基本语义中归纳出两条正义原则:
1、正当性原则
正当性原则是说: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是正当的。那么,何为正当?
所谓“正当”,在儒家话语中的涵义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出于仁爱的情感、仁爱的精神。这其实就是孟子“仁义礼智”理论结构中的“仁→义”结构。所以,孟子指出,儒学的根本不过“仁义而已”[55],这就叫做“居仁由义”[56]。按照儒家的观念,在进行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时,如果出于仁爱的动机,那就是正当的;否则,就是不正义的。由此就形成了“仁→义→礼”的理论结构:仁爱精神→正义原则→制度规范。
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是出于仁爱的情感,而这种仁爱情感作为基本的生活情感,是归属于生活的;换句话说,仁爱乃是作为存在的生活的情感显现。在这个意义上,正当性原则的存在本源是生活。
但是,在制度规范的建构中,仅有仁爱精神是不够的。这是因为:在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形态的不同生活方式下,仁爱精神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例如父爱的实现方式,在前现代社会是家长制,而在现代性社会则是监护人制度。所以,还需要:
2、适宜性原则
适宜性原则是说: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是适宜的。那么,何为适宜?
所谓“适宜”,是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必须适应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形态下的基本生活方式。例如基本政治制度,王权制度曾经适应于宗族社会的生活方式,皇权制度曾经适应于家族社会的生活方式,而民权制度适应于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任何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的看法都是不懂得适宜性原则的表现。
这种对于适宜性的考量,显然是出于群体关怀,即仍然是出于仁爱精神、仁爱动机的;换句话说,这里仍然是“仁→义→礼”的理论结构。所以,韩愈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57] 这就是说,博爱的仁爱精神的具体实行方式,需要考虑适宜与否的问题。
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适应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生活方式,而种种不同的具体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生活之流的显现样式。由此可见,适宜性原则的存在本源仍然是生活。
(三)仁:仁爱情感
综上所述,作为“生活儒学”的形下学部分的“中国正义论”,其核心是“仁→义→礼”的理论结构:仁爱情感→正义原则→制度规范。这其实是一套伦理学原理,由于它所关注的最终是制度规范问题,可称之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58];但它其实是一种广义伦理学的一般原理,可称之为“基础伦理学”[59]。
在这个理论结构中,“仁”或“仁爱”是其本源。但说到儒家的“仁”或“仁爱”观念,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存在着误解。儒家所说的“仁”,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涵义和用法,属于不同的观念层级:有时是说的形而下的道德情感、伦理规范;有时甚至是说的形而上的本体;[60] 有时是说的先验的人性;而有时则是说的自然的生活情感。但就其原始语义来看,“仁”或“仁爱”就是说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情感而已。
但即便是对于情感意义上的仁爱,人们也存在着误解。一种最常见的误解,是把儒家的“仁爱”仅仅理解为“差等之爱”。
1、差等之爱
所谓“差等之爱”,是说儒家的仁爱是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而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的,例如爱自己胜过爱他人,爱亲人胜过爱外人,爱人类胜过爱非人的东西。最典型的表述是孟子的说法:“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61] 他甚至说:“亲亲,仁也。”[62] 据此,他反对墨家讲的“爱无差等”[63]。荀子甚至更加明确地讲:仁爱是从“爱己”出发的,“爱己”是仁爱的最高境界。[64]
诚然,差等之爱乃是人类情感的一种实情,因而儒家的仁爱确实具有差等之爱的一面。但是,如果仅仅这样理解儒家的“仁爱”,就会导致严重的问题: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假如是根据亲疏关系的远近来进行的,这样的制度规范难道是正当的、正义的吗?显然不是。其实,儒家所讲的“仁爱”不仅有“差等之爱”一面,而且有“一体之仁”一面。
2、一体之仁:博爱
所谓“一体之仁”,就是成语所说的“一视同仁”。这是儒家一向的基本观念,王阳明讲得最明白: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小人之心既已分隔隘陋矣,而其一体之仁犹能不昧若此者,是其未动于欲,而未蔽于私之时也;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是故苟无私欲之蔽,则虽小人之心,而其一体之仁犹大人也;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65]
这种“一体之仁”,其实就是“博爱”。上引韩愈说“博爱之谓仁”,此所谓“博爱”不是西方人讲的“博爱”(fraternity)(兄弟情谊),而是指的一视同仁的普遍之爱(universal love)。
上文谈到的中国正义论的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出于仁爱的动机,其所谓“仁爱”绝不是说的差等之爱,而是说的一体之仁。所以,更准确地表述,正当性原则的要求是: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唯有这样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才是正当的、正义的。
总括全文,那种“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笔者的“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注释:
[①] 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由韩国儒教学会、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和儒教文化活性化事业团联合主办,于2016年5月19日至20日在首尔召开,主题为“生活儒敎、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
[②]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著述:《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③] 参见黄玉顺:《儒教问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④] 成中英:《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诚思、诚学、诚修、诚信、诚行》,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31-39页。
[⑤] 这种区别尤其体现在中国大陆关于“儒教”问题的历次论争当中。参见黄玉顺主编:《庚寅“儒教”问题争鸣录》,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⑥] 关于学界对黄玉顺“生活儒学”的评论,参见:崔发展、杜霞主编:《生活·仁爱·境界——评生活儒学》,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收录了32篇评论黄玉顺“生活儒学”的文章,其中包括著名学者李幼蒸、吴光、张志伟、郭沂、干春松、鞠曦等的评论文章。此外,尚可参见:杨生照:《生活儒学》,张岱年主编《孔子百科辞典》修订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周良发:《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黄玉顺的“生活儒学”》,《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09-10D151);[美国]安靖如(Stephen Angle):《作为一种综合儒学的生活儒学》,安靖如《走向进步儒学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美国]政治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7页(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olity Press 2012, pp10-17);李海超:《生活儒学多元开展之必要与可能——与黄玉顺先生商榷》,《当代儒学》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杨生照:《冯友兰中国哲学研究范式之赓续及其嬗变——现代中国哲学中的“清华传统”研究》,《当代儒学》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刘宏:《生活的儒者、儒者的生活——〈生活儒学讲录〉读后》,《当代儒学》第3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Chen Xin:Huang Yushun: Confucianism and Contemporary Life — Collected Essays on “Life Confucianism”, 美国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12) 11:393-397 [ISSN: 1540-3009]; DOI 10.1007/s11712-012-9287-9;杨虎:《别具一格的“非人的生活”——评生活儒学对“生活”与“人的生活”的区分》,《当代儒学》第4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周良发:《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二、2. 生活儒学,《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徐庆文:《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李海超:《情感观念比较:生活儒学与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张新:《当代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视域问题——以黄玉顺“生活儒学”为例》,《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孙铁骑:《从“生活儒学”到“修身儒学”》,《衡水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
[⑦] 成中英:《生活儒学与生活儒教:诚思、诚学、诚修、诚信、诚行》,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32页。
[⑧]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附论二:“生活本源论”。
[⑨] 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
[⑩]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 From The East: The Chinese Theory of Justice,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帕斯国际有限公司(Paths International Ltd)2016年版);《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11] 参见黄玉顺:《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东岳论丛》2015年第11期。
[12] 参见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六家为: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
[13] 参见郭沂:《开新——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十家为:杜维明、李泽厚、刘述先、成中英、牟钟鉴、安乐哲、张立文、林安梧、黄玉顺、郭沂。
[14]“生活的儒学”的叫法,见龚鹏程:《生活的儒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15] 笔者“生活儒学”的代表作《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其英文本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即将由美国Bridge 21 Publications出版,即是用的“Life Confucianism”。
[16] 龚鹏程:《生活儒学的开展》,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103页。
[17]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8] 龚鹏程:《生活儒学的开展》,见会议论文集《生活儒教、儒生精神、现代文明的对策》,第一册,第103页。
[19] 参见徐庆文:《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20]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4期。
[21]《韩非子·显学》。《韩非子》:《诸子集成》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版。
[22] 黄玉顺:《儒学当代复兴的思想视域问题——“儒学三期”新论》,《周易研究》2008年第1期。
[23] 方朝晖:《为“三纲”正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4] 刘小枫:《宪政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国父毛泽东》(“凤凰网读书会”2013年4月19日举办的第133期讲座),转自“观察者”网: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3_05_17_145259.shtml;《如何认识百年共和的历史含义》,《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
[25]《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李隆基注:“以孝事君则忠”;邢昺疏:“君子之事亲能孝者,故资孝为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又《士章》:“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李隆基注: “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矣。”《孝经》:《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
[26]《荀子·子道》。《荀子》:王先谦《荀子集解》,《新编诸子集成》本,中华书局1988年版。
[27] 蒋庆:《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澎湃新闻2015年8月13日),转自“腾讯文化”:http://cul.qq.com/a/20150813/010233.htm。齐义虎:《回归家庭是对女性最好的安顿》,儒家网:www.rujiazg.com/article/id/6887/。
[28]《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2页。
[29] 王守仁:《答顾东桥书》,见《王阳明全集》,吴光编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3页。
[30] 王夫之:《尚书引义·太甲二》。《尚书引义》:中华书局1976年版。
[31]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附论二、生活本源论。
[32] 参见黄玉顺论文:《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
[33] 参见黄玉顺著作:《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
[34] 参见黄玉顺论文:《国民政治儒学——儒家政治哲学的现代转型》。
[35]《老子》第二一章。《老子》:王弼本,《王弼集校释》,楼宇烈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
[36]《老子》第一、四、三四、三九、四十、四二、五一、六二章。
[37]《礼记·中庸》。《礼记》:《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38] 均见《礼记·中庸》。
[39]《论语·颜渊》。《论语》:《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40]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98-199、209-217页。
[41]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86-199、232-235页。
[42] 参见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生活儒学”问答》,见《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第60-73页。
[43]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
[44]《周礼》:《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45] 参见黄玉顺:《“周礼”现代价值究竟何在——〈周礼〉社会正义观念诠释》,《学术界》2011年第6期。
[46] 参见黄玉顺:《儒学的“社会”观念——荀子“群学”的解读》,《中州学刊》2015年第11期。
[47]《论语·泰伯》。
[48]《荀子·礼论》。
[49]《论语·颜渊》。
[50]《论语·季氏》。
[51]《论语·为政》。
[52]《论语·卫灵公》。
[53]《孟子·离娄上》。《孟子》:《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54]《礼记·中庸》。
[55]《孟子·梁惠王上》。
[56]《孟子·离娄上》、《孟子·尽心上》。
[57] 韩愈:《原道》,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58]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生活儒学的制度伦理学思考》,《文史哲》2011年第6期;《“中国正义论——中国古典制度伦理学”系列研究项目情况汇报》,见《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安徽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59] 参见黄玉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
[60] 如程颢说:“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其所谓“仁”作为“此理”乃是“天理”,即是“形而上者”。见程颢:《识仁篇》,载《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61]《孟子·尽心上》。
[62]《孟子·告子下》、《孟子·尽心上》。
[63]《孟子·滕文公上》。
[64]《荀子·子道》:“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君子矣。’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65] 王守仁:《大学问》,见《王阳明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