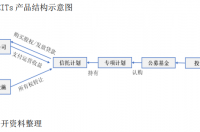一、德国选举制度的巧妙设计
正角评论:郑老师,昨天德国大选结束,默克尔毫无悬念地继续执政德国。这已经是她的第四任任期了。虽然这次大选德国的右翼政党获得了历史性突破,拿到13%议席,但是相比法国、英国,甚至美国这些西方国家,德国的政局依然显得相对稳定。不过德国实际也在不同程度上面临着法国等欧洲各国面临的社会问题,例如过度的福利、新移民与原籍国民的对立、反全球化思潮等。那么郑老师能分析下,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下,为什么英美法等国的政坛表现出了激烈的动荡,而德国却还能基本保持平稳呢?
郑永年:即使在选举期间,多数人也知道默克尔肯定当选。当然这个局面是德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要素综合效应所产生的。这些要素构成了德国的稳定,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和其它西方国家区分开来。
在讨论德国的政局相对其它几个主要西方国家为什么更稳定时,我们就要首先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究竟有什么不同。政局是否稳定往往和制度运作本身的逻辑有关。中国人看西方民主往往很笼统,就是选举,人们往往忽视各国民主的细节。正是这些制度细节,而不是挂在政治人物口头上的“民主自己”,决定了制度的有效性。我早就强调过,即使在西方,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民主,民主是“一国一模式”。
我们先谈英美的情况。英美等西方国家实施的民主选举制度,从选区与代表关系的角度,简单地说可以分为单名选区制和比例代表制。所谓单名选区制,是指一个选区只有一名代表;竞选者只需获得相对多数票而不一定过半数就能将其他竞争者的得票全部揽为己有并当选为本选区的代表。这种制度也被称为“多数代表制”或“赢者通吃”制度。
美国的总统大选,除了缅因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外,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果赢得了这个州的多数人投票,就算赢得了这个州所有的选举人票。这种“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制度,其实就是单名选区制的一个变种,二者精髓就在于,只有在选区内获得排名第一的候选人才能拿到这个选区的代表权。即使拿到与第一名很接近的第二名的票数,一点用处都没有。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会促使多个利益集团和政治团体结合为两个大的政党,极易形成两党体制。
因为在多党竞争而只有一个胜出的规则中,至少有两个失败的政党会认识到彼此联合对于下一次选举有利,另外的政党也会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迫联合。第三党虽然有时能够在这种制度下存在,但是没有多少获胜的机会。而“废票心理学”更一步侵蚀了第三党及其它弱小党的存在,因为他们的政党不可能赢得多数票而当选,所以为了至少能发挥出一部分影响,他们就会在大党中选择一个不太反对的政党进行支持。
英美两国最终形成两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形态,是他们都运行着单名选区制这样的选举制度的必然结果。单名选区制有一些优点,它所造就的主要大党往往会坚持在政治谱系的中心活动,从而遏制极端主义的成长。但这里有一个重要条件,那就是中产阶层的强大。在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里,这样的国家不管是两党中任意一党执政,都会因为要照顾到中产阶级的利益,而坚持类似的执政方针,这时政府的各类政策就会表现得相当稳定。这种稳定并不是制度本身带来的,而是社会政治生态的结果。
在过去数十年的全球化进程中,英美的中产阶级比例持续下跌。在美国原本占到选民80%左右的中产阶级人群,已经萎缩到了目前的50%左右(据目前统计,美国的中产阶级人群在50%上下徘徊)。在英国,很多统计表明英国中产阶级在社会人群中的所占比例仅为25%。所以英美的政治便不具备了稳定的前提。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也很容易看到,英美的这种制度有其明显的缺陷,就是议会中的这两个大党的出现其实有很大人为的色彩。首先,失败的政党在失败的选区哪怕获得49%的选民支持,也无法转化成有效得票,选举的胜利和失败都被人为的扩大了。其次,这种制度对新的第三党的产生更是有极大的遏制作用,让政治处于长期简单的两党制。法国的马克龙可以以一个新组建的政党直接赢得大选,而同样反传统的特朗普只能“借助”共和党,才能冲击总统位置。
这种制度在特殊情况下,还会出现实际获得选票多的一位总统候选人输给实际获得选票少的候选人的情况,当年小布什和戈尔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戈尔获得的选民投票实际多过小布什,但是由于赢者通吃的规则,小布什在一些州以微弱优势获胜,却拿走了那些州的全部选举人票,最终获得了胜利。这次,特朗普和克林顿的对决也是同样的情况。
美国名义上虽然是选举人制度,但是实际上选民是针对总统候选人投票,产生最高领导人,再由最高领导人组建内阁。所以候选人一旦成为了美国总统,他在组阁上便不受另一个党派的有效制约。当美国出现了中产阶级比例下降的情况后,共和党和民主党分别代表了社会上对立的两个大群体,两党领导人便出现了在政策上互相否决的情况,即大家看到的如“奥巴马医改”,“美国移民法案”等政治上激烈的“动荡”。英国虽然在政府组建上跟德国类似,但是由于议会选举跟美国一样实行的是单选区制度,两个政党轮流执政组阁,所以英国在例如脱欧等问题上,也出现了前后两个执政党互相否决对方政策的情况。
法国对这种单名选区制做了一个重大修正,就是两轮投票制。不管是全国性的总统选举还是代表地方选区的议员选举,都可以有两轮投票。议员当选规是,第一轮投票必须是超过半数的选民选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所在选区半数以上选票、且得票数达到所在选区登记选民数量至少25%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如无人达到此标准,则超过得票数12.5%的候选人均可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最高票获得者当选,如只有一人甚至无人获得12.5%以上选票,则第一轮得票最高的前两名候选人进入下一轮投票对决。总统选举也类似,法国总统选举是全民直选,第一轮必须得票50%以上才能直接当选,如果无人直接获得50%以上的选票,那么就由得票最高的前两名候选人参与第二轮投票对决。
这种制度表面上看,让小党有了独立表达自己主张并获得支持的空间。因为第一轮投票无需取得50%的选票,只需得票12.5%以上(甚至低于12.5%),就有机会进入下一轮选举;只要能进入第二轮选举,小党便有了和其它大党联合左右最终结果的实际影响力。所以中小党派可以长期独立存在,表达自己的主张,不用担心自已由于所占比例较小而发挥不出政治能量。这样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法国政党林立,而且容易滋生极端性政党。
在英美的制度下,小的政治势力或者极端的政治势力在选举时因为不能代表多数,属于必败无疑,所以平时就得不到有效的社会力量支持,他们很难生存,只能并入两个大党中的一个。法国这种制度则不同,只要不出现一党独大占有选区50%以上选票的情况,凡是得票12.5%以上的政党都可以稳稳的参与最终的第二轮竞争,小党就获得了在第二轮竞争中和大党博弈的资本(选择联合一个大党打击另一个)。
所以,任何一个可以有机会获得12.5%以上选区选票的政党,都有其不可忽略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都能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各个代表地方利益或者少数群体利益的甚至极端观念的政党都获得了相应的政治话语权。法国之所以这些年被称作撕裂的法国,跟其所运行的民主制度是分不开的。
德国的选举制度与英美和法国都不同,是一人两票的混合选举制。656个议席被平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328个席位由选民直接投票给候选人,每个选区一个议席,由得票最多的一人获得(不一定过半数),这是典型的单名多数制,称为第一票;另外的328个席位是选民投票给参加竞选的政党的。各政党按得票比例多少来分配这一部分席位并由政党自己决定进入议会的人员名单,这称为第二票。但在分配时,首先减去该党在第一票中已经当选的席位。
更为重要的是,出于防范极端主义政党和地方小党在议会泛滥,德国的《基本法》规定,政党必须获得5%的选票,才可以在第二票中获得席位的“门槛条款”。这样就跟法国的政治游戏规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法国,一个新的党派只要获得任意一个选区的12.5%的选票,就可以稳稳地获得一定的政治话语权,哪怕这个党在别的选区一点支持率都没有;而德国的新成立政党必须一次性获得全国范围内超过5%的支持,才能成为一个有资格分得议会选票的政党,成为“牌桌”上的一员,或者要在一个选区直接得票超过大党的候选人,才能获得一个宝贵议席。这就极大遏制了小党和新兴党派的生存空间。
美国和法国总统制,都是最高领导人顶多连任两届,而德国实行的是内阁制,法律不限制最高领导人任期,总理可以无限连任。这样的政治安排跟德国特殊的议会选举制结合在一起,非常利于大党稳定的长期执政,遏制了小党或者新兴政党崛起。
制度带来的稳定并不消解实际的社会矛盾,默克尔尽管连任,德国政治也面临着和其它欧洲国家一样的巨大挑战。
二、希特勒的教训与德国民主制度的完善
正角评论:看来,德国的政治稳定其实并不是其执政党相比英美法等西方国家更好的处理了社会问题,更多是德国的政治制度的人为安排的结果。那么为什么德国会产生这样有别与英法的制度呢?
郑永年:这基本上是由德国的历史决定的。德国的民主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而是在经历了惨痛的失败之后,学到了历史教训,经过改革和改造才演变成今天这个制度的。在西方民主中,德国可以说是“后来者”。早期德国人想实行甚至比欧美更民主的制度,但走向了失败。
希特勒上台前的德国处于魏玛共和国时期(一战后建立的德意志共和国因其宪法是在魏玛制定所以又称之为魏玛共和国),当时的德国采用的就是跟英美的单名选区制度相对应的另一个极端的选举制度,比例代表制。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的核心思想是,一个政党在全国大选中的得票比例,应最终与其在议会所获议席的比例相等,从而达到议席的分配情况真实,准确地反应选民中的舆论和忠诚分布状况的目标。
魏玛宪法将议会分为联邦国会和联邦参议院,联邦参议院的议员由各邦政府任命,在联邦国会的选举中,规定全国作为一个大选区,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按比例代表制竞争议席。
这就造成了比现在法国选举制度更加恶劣的政党极端分化的现象。在这种制度下,任一政党不管从地域上,或者种族上,甚至单一的社会阶层上,只要能获得高于议席门槛的投票,即6万张选民投票的选票,就可以获得一个议会席位。结果就是德国的政党泛滥,有多达100多个政党在20年间登上全国政治舞台。议会常驻政党都有20多个。在1918年到1928年十年间,魏玛共和国如走马灯般更换了10届政府,全国政治接近瘫痪,间接导致了1933年纳粹的上台。德国在战后产生的特殊政治选举制度,其实是对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极端状况的一种回应和重新设计。
三、难民危机与德国政局
正角评论:这次的大选,默克尔其实也是有危机的,去年的难民问题,德国人的“圣母”形象在全世界范围内其实都引起了极大的讨论与争议。欧洲各国呈现出了极大的反差,德国挺身而出迎接上百万的难民;相比之下,英国和法国仅仅接纳了2万左右的难民。民间对此有几种解释,左派高调歌颂德国政府和国民的道德水平,说德国此举是默克尔和德国人民道德高尚,崇尚西方人权价值观的体现;也有一部分人说,德国此举并非他们说的那么冠冕堂皇是出于人道主义,根本的原因在于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目前的德国处于老龄化阶段,国内劳动力匮乏,德国是想借此机会吸纳廉价劳动力。郑老师你能点评下这两种观点么?
郑永年:德国接纳难民的确有受政治正确的道德包袱影响。(关于为什么西方各国会形成人权高于主权的政治信条,大家可以阅读正角评论公众号之前的文章《恶之花》。)不过,对”政治上正确”,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一方面,“政治上正确”使得人们不去正视问题,掩盖了很多存在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最终还是会爆发出来。另一方面,在欧美,“政治上正确”也经常被视为是文明、进步的象征。的确,从理想上来说,“政治上正确”者所秉持的这些道德也好、价值观也好,人们并没有异议。问题在于,这些道德和价值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在欧美,因为社会成员一般受教育水平很高,社会多少都持有一些“政治上正确”观。尽管“虚伪”,但是这种“虚伪”也是文明的一部分。
德国吸纳难民来解决劳动力缺乏问题,即从经济意义来看待难民,则是很多媒体和学者用来论证这种移民政策正确的论据。很显然,有很多途径可以解决劳工短缺问题。例如,短期劳工短缺可以通过对中国等国的劳工发放工作准证来解决,长期改善人口结构可以通过引入高素质的技术移民来实现;这二者都不至于要靠引入难民来解决。
实际上,引入中东难民不仅不可能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相反还会结合德国福利制度的缺陷,给德国政治背负上严重的包袱。德国由于鼓励生育,一个孩子每月可以获得大约200欧元的补贴,这个补贴对于一个追求生活品质的德国中产阶级家庭并不具备吸引力,但是对于穆斯林移民来说,却可以成为生活的来源,所以穆斯林群体在德国的生育率远超平均水平。问题在于,这些日益庞大的穆斯林后裔很难融入德国社会,成为人口“红利”,而是与德国现有社会格格不入,成为了撕裂德国社会的根源。
年轻的穆斯林移民并不学习德语,也不尊重德国社会文化,而是在德国继续以穆斯林国家的方式生活。2016年年底,德国一位11岁的穆斯林小女孩拒绝参加学校的游泳课程,她认为这样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法则,即使自己在游泳课上穿的是“布基尼(burkini)”——可以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裹起来的泳衣。早在2013年,德国法兰克福(Frankfurt)一位13岁小女孩的父母就拒绝让自己的女儿参加游泳课。当时法官判决,小女孩可以穿布基尼上课。但是,许多穆斯林家长依然不依不饶,认为女童和男童在学校过于接近也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这样的事件其实层出不穷,这些穆斯林后裔要求德国社会按照穆斯林的文化运行。
四、默克尔的难民政策是如何考虑的
正角评论:中东难民在欧洲凭借强大的人口再生产能力,改变了当地人口结构乃至政治生态已经不是新闻。那么默克尔这种开发难民进入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如右派所说,是愚蠢的自掘坟墓呢?既然迎接难民不是解决劳工短缺和社会老龄化问题的手段,那么德国对难民的迎接除了自身政治正确的包袱所致外,有没有理性的成分呢?
郑永年:首先,默克尔并不愚蠢,她并不是像批判她的人所说的那样对穆斯林移民所造成的问题毫不在意,只一心一意做一个“圣母”,而是一直警惕着德国社会被穆斯林撕裂的问题。早在2010年时,默克尔就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的文化多元社会已经死亡,伊斯兰社区是德国的一部分,穆斯林移民需要学习德语,努力融入德国社会。以前“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的平等已经宣告终结。
2016年底,默克尔在所属基督教民主党(简称基民党)大会上表示,在德国穿全罩式的服饰“不太合适,这不属于我们。我们的法律优先于部落规范、荣誉守则和伊斯兰教法”。实际上不仅仅在德国,在对待穆斯林政策上因为宽容而饱受诟病的法国也在法律上限制了穆斯林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各国媒体在这类事情上其实高度极端化,在这类问题上往往选择性报道,造成了公众对这些政治领袖的很多误解。
默克尔的决定除了受上述“政治上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影响外,她自己的经历也对这位强政治人物产生了重要影响。她出身当时的东德,并在那里长大。她经历了当时东德的集权制度,对基本人权全然不顾的现象是有深刻的记忆的。保障基本人权也是她决策的重要一个变量。再者,在是否接受移民这个问题上,西方各国政府都没有否认接受难民的重要性,他们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实际政策方面。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西方开放型政权的特点。多元利益都可以得到表达,都可以反映到政治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之后再来做调整。就难民问题上,现在的情况是,既然已经发生了,那么就只能寻找方法来如何化解之。没有人知道,西方能否解决这个问题,但要回到封闭国家的时代则是不可能的。谁都知道,文化多元主义出现了问题,但奇怪的是大多数还是接受文化多元主义的价值。
不过,几个世纪以来,西方都是在这种矛盾过程中走过来的。就德国来说,我觉得至少默克尔本人很有信心来化解这场难民危机和解决问题。我们应当以开放的心态来观察未来的发展。对德国人来说,历史是他们的,但他们的历史则是开放的。几个世纪之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嘲讽中国没有历史,因为中国的历史是封闭的,一尘不变的。当黑格尔这样说的时候,他是拿西方(德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历史做比较。我想,今天的德国人仍然对历史抱开放的心态。
五、德国经济的未来
正角评论:在全世界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的今天德国经济在欧元区一支独秀,去年经济增长1.9%个百分点,是欧洲大国中经济和财政状况最高的。更重要的是,德国政府去年财政盈余237亿欧元,创两德统一后财政盈余最高值。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当时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欧洲各国期间他问默克尔,德国的经济如何?默克尔回答:“至少我们还在生产。”德国实际是09年金融危机过后,欧洲经济的中流砥柱。这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点,欧盟各国由于高福利的影响,制造业都已经萎靡不振,德国也以高福利著称,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却依然在全球范围内领先。郑老师能谈谈面对同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什么德国能达到这些成就么?郑老师您判断德国能够在未来持续这样的表现么?
郑永年:实际上,默克尔这次能够当选最主要的因素还是德国的比较好的经济状况。经济还是政治的基础。借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其竞选期间的话,就是“笨蛋,这是经济”。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经济形势,老百姓是否继续支持她就很难说了。尤其是当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都还在经历寒冬的时候,德国老百姓觉得继续支持默克尔,因为对老百姓来说,德国的“一枝独秀”是和默克尔相关的。
德国经济的坚韧性和德国的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有关。如果说德国经济是欧洲的中流抵柱,那么德国经济的中流抵柱,就是大约七千到一万家“隐形冠军”。所谓“隐形冠军”,就是著名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提出的,营业额在1亿到5亿欧元之间,在细分行业全球排位第一或第二但又不太为人所知的制造企业。去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参观了一家企业,叫“Phoenix”(凤凰)。这家企业是全球连接器的“隐形冠军”,几乎全球所有的连接器(运用在射频领域的工业产品)都是这家公司做的。
当一个企业处于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冠军的时候,不管金融危机多大,只要这个行业本身还存在,这家企业就不会倒掉。这些制造业之所以是不为大众所知的“隐形冠军”,其根源在于他们都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品牌和产品,而是在制造业中上游的理性部件产品。这样的产品面对的是下游制造业的生产者纯理性的购买。对于这样的理性购买型行业,金融危机带来的产能的缩减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一个制造业参与者,而是进行末位淘汰,所以这些企业抗金融危机的能力非常强。德国是一个8000万人口的国家,近万家这样的中小企业,对德国国民经济形成了非常有效的支撑。所以德国在金融危机中受的波及最小,德国的经济表现也最亮眼。
德国的制造业优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能持续。第一个原因在于,德国在制造业上的积累有强大的制度保障。我们先来谈福利制度。很多媒体人在诟病欧洲福利制度时,仅仅是从一些笼统的层面看欧洲的福利现状,所以让大家有一种错觉,就是欧洲国家的高福利仿佛是差不多的。实际上欧洲各国的福利制度及其成因都是差异极大的。
正如德国人大刀阔斧地对其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德国人在福利制度方面也有很多创新,避免了一般福利国家的通病。德国的福利制度关于员工失业救济的部分在2005年其实经历过一次重大改革。德国在2000年前后曾被称为“欧洲的病人”,当时的德国深受福利所累,就业率创历史低位,经济萎靡不振。前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执政的最后一届,大刀阔斧地改革了德国的福利制度,在2003年到2005年三年间先后通过了四套哈茨改革方案。
除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创建和发展外,最为人熟知的方案就是取消了与工资挂钩的无限期失业补贴,将失业救济与社会救济合二为一。自德国1927年失业保险制度建立以来,失业救济与社会救济分属不同的管理系统,也具有不同的支付标准。而“哈茨四”将原来的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合二为一,引入了由政府税收统一支付的“失业金II”,即所有具备就业能力(具备就业能力的定义是每日能力工作三小时的人)的救济金的领取人员不再有失业救济和社会救济的差别,而是统一领取“失业金II”,“失业金II”与失业前的收入没有关联,而是对领取者实施统一标准。
失业金额被设立在为失业者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的水平上,失业者必须积极努力进行再就业尝试,失业金领取人员必须接受职业中介机构为其介绍的任何一个合法工作,只要中介机构为失业者提供的工作机会不违背伦理道德,即使该工作与其既有的工作技能不符,失业者也必须接受该份工作(只有当具有劳动能力的失业者需要抚养3岁以下孩童时才会被免除再就业义务),否则将面临失业金连续3个月被扣减30%的处罚。改革前的德国社会,有很多懒人故意对工作挑三拣四,按照原有工资的60%左右无限期领取失业业金,合法的享受其它勤劳者的“供养”。
因为勤劳者要被征收重税去养活懒惰者,所以当时的德国各行各业的工作者都没有积极性,国家经济命脉的制造业也奄奄一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在推进法案时,说出了一句日后常被改革者引用的话“懒人没有权利”。从一定程度上说,德国的这次改革引入了我们东亚社会流行的“工作福利”,即把福利和工作联系起来。虽然这次改革成了时任总理施罗德政治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但是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和精神却被继任者默克尔继承至今,让德国免于成为了懒人的天堂,鼓励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成了德国社会经济,尤其是制造业的活力所在。
另一个重要制度保障是德国的教育制度。德国有着全世界其它大国都没有的特殊职业技能教育体系,也就是针对蓝领工人的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这些学校常被我国的媒体戏称为德国的蓝翔技校。但实际上德国的这些 “蓝翔技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育系统分支,而是由德国贸易部而不是德国教育部直接管理的国家战略级别的技术人才培育系统。他们为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不断输送最专业的工业生产技术人才。在去年的德国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一位德国的“隐形冠军”企业家就提到,他在中国的生产线比德国的先进,但是中国的次品率是德国的八到十倍。这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工人的素质。
德国有全世界最高素质的工业工人,加上他们众多“隐形冠军”让德国不仅成了制造业大国,更是制造业标准的大国。全球工业制成品中不到5万个标准,其中2万5千多个标准,是德国人制定的。而且每年德国还在新增大约1500多个制造业的标准。这让德国在工业制造业上相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它国家一步领先,步步领先。
总体而言,在当今很多国家的经济被金融和互联网等快速“虚拟化”的时候,当很多国家都用投机心态赚快钱的时候,德国人坚持着实体经济,用技术和手艺赚钱,并且成功了。德国的制造业优势,有着相当大的可持续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很难有国家能在工业制造上赶超德国。具有巨大投机性质的金融和互联网不可持续,但实体制造业则是可以持续的。这个观点对年轻人来说,可能太传统了,不过,从世界经济史来看,确实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