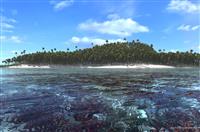中美关系的内在肌理和宏观环境正在发生重要变化,这种变化源自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两国摩擦因此趋于激烈,双边关系走向亦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给中国造成压力。美国对华政策的旧框架不再适用,新的框架尚待确立,双边关系走向何方取决于中美两国的选择。
改变早已开始
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中美关系,其演变与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即:敌对与冲突的二十年(1949~1969年)、缓慢缓和的十年(1969~1979年)、短暂的十年“蜜月期”(1979~1989年)、合作与摩擦并存的二十年(1989~2009年)、重新寻找方向感并艰难定位的十年(2009~2019年)。中美刚刚纪念了建交40年,双边关系目前的状态既算得上“四十不惑”,也可以说是“四十有惑”。当前“惑”与“不惑”也许并非关键,重要的是两国能否经历一番磨合后重新确立双边关系的新框架,以至“五十知天命”。
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 2009~2010年是重要转折点。2009年起中美围绕南海问题发生直接摩擦,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跃居全球第二,随后奥巴马政府提出“重返亚太”,后调整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领域,美国提出过“第三次抵消战略”“空海一体战”等概念,其重点关注对象国直指中国。2010年到2015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急剧复杂化,一系列热点事件接踵发生,包括中日在钓鱼岛的对峙、中菲在黄岩岛的摩擦以及随后菲律宾发起的所谓南海国际仲裁案、中美在南海问题上博弈升级,等等。2015年起美国国内战略学界开始进行范围非常广泛的对华政策讨论,至今没有形成完全的结论,但这是美国对华战略将要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奏。
也有人将美国对华战略变化追溯到2000年。那一年是美国大选年,后来成功当选的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发表了诸多涉华负面言论,其上台初期针对中国摆出的战略调整姿态与2017年特朗普刚就职时颇为相似,如果不是因为9·11事件迫使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转向反恐,美国可能早就将中国定位为“首要安全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的轮番下行也恐怕早就开始了。
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确并不始于特朗普政府,但特朗普总统本人特立独行的风格和对“美国优先”的政策偏好、对右翼的放纵利用的确让中美“战略竞争”成为一个我们不得不直面的现实。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其任内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多个方面指责中国的政策行为,认定中国是正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2018年10月初美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阐释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讲,非常突出价值对立因素。2018年11月胡佛研究所和亚洲协会联合发布题为《中国影响与美国利益》的研究报告,美方多数参与学者对中美关系做了严重消极的描述和总结,称中国正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来拓展影响力。同月,美前财长鲍尔森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论坛上发表演讲称,中美如果处理不好经贸争端,“经济铁幕”很快降临,世界也将因此走向分裂。
新认知
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源于认知的改变。驱动美国对华认知发生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是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即中国的快速崛起导致双方实力差距相对缩小;其次是力量变化导致运用力量的方式随之出现变化,此即美国所谓的“中国越来越具有进取性”;第三是叙事方式的变化,也就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到底应该发展什么样的关系,是通过建立“中美国”或“新型大国关系”实现超越?还是在“修昔底德陷阱”(一种预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有一战的理论概念)或“金德尔伯格陷阱”(一种预言崛起国不愿承担守成国无力负责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而使世界陷入领导力空缺、危机四起险境的理论概念)中苦苦挣扎?近年类似新词汇层出不穷也从侧面反映出中美关系高度复杂令人担忧的现实。
当前美国对华认知的改变是系统性的,反映了美方对中国“软实力”和“硬实力”运用能力增长的过度担忧,而此前美国通常更多强调中国“硬实力”增长形成的挑战。在中国的“硬实力”方面,美方判断中国迟早要在经济总量上追平美国,对外战略的“示强”一面势必更加明显,有可能将美国“挤出”西太平洋地区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另起炉灶”;在“软实力”方面,美国高度担忧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以及相伴的影响扩展,认为中国一直在利用这种交流向美国进行“渗透”,不仅“窃取”美国的高新技术,也开始影响美国的国内政治。美国国内政治精英、军方、国会、商界和媒体等各界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少,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强硬姿态和政策,对华强硬在华盛顿几乎成了“政治正确”。
还应注意到的一点是,虽然美国的对华认知或者判断正在发生系统性的改变,但美国对未来究竟该如何应对一个崛起的中国并无定论。到底是战略竞争、经济“脱钩”还是进入“新冷战”,或是在适度相互妥协中达成新的平衡,目前没有共识。白宫、国会、军方在不同领域针对不同问题的各自或协调行动正以“且走且看”的方式催生中美关系整体变化的既成事实。
未来变化
观念认知的改变必然带来行为方式的变化,也必然推动中美关系的整体变化。目前中美争端主要还是发生在经贸领域,总体上仍然可控,但争议激发的对立情绪逐步蔓延到军事、人文交流等领域,这种趋势还有升级、扩大甚至激化的风险。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对华封堵趋势日益明确,未来与此相关的人文交流势将受限,特别是在科技、工程、数学相关领域。美国也在加强对中国资本进入美国的限制,加强军民两用或高科技产品的对华出口管制。这些措施都在驱使中美战略竞争成为某种“常态”。
变化已在发生,未来可能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美关系运作的宏观环境之变。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一个建立者和维护者,陆续从一些国际组织、条约和合作安排中“退出”,不愿再为国际体系的运行承担更多责任、付出更多代价,同时也在自己的盟友圈内构筑新的合作标准和规则。现存国际体系的松动和重组可能给中国带来一些推进国际影响力和引导力的机遇,也会让中国面临较多压力,中国有可能成为这种体系松动的针对目标。
其二,美国传统决策方式之变。美国政府决策流程已因特朗普而发生改变,以前是各部门会商,最后形成一致的政策,现在却不是这样。特朗普用人有非常清楚的标准:不忠诚者没机会进入政府,政府内不听话者赶紧离开。现在特朗普的外交安全团队偏好强硬的、立竿见影的对外政策。这些强硬角色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贸易和制造业政策顾问纳瓦罗、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国务卿蓬佩奥,甚至财政部长姆努钦。此前被戏称为特朗普政府“三位成年人”的蒂勒森(国务卿)、马蒂斯(国防部长)和凯利(白宫幕僚长)均已离开。
第三,管控中美关系风险传统工具作用之变。既往,中美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有助于压制、缓解两国分歧,现在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丧失兴趣,在地区问题上采取更为强硬姿态,并且淡化双多边合作,导致过去管控中美关系复杂风险的那些行之有效工具的作用在弱化。而这种变化的背后,是美国和西方社会的整体右转和保守化,以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的式微,这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恐怕不是短期的,将来也不一定会随特朗普时代的终结而立刻告一段落。
第四,施压方式之变。特朗普本人擅长就事论事,但美国行政部门倾向于从战略视角看待中美关系。特朗普总统本人聚焦解决经贸争端,但行政部门注重系统性地应对中国崛起构成的“挑战”,两者从不同角度形成了对中国的共同压力,这是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的一个基本背景,这种压力格局如果被美精英阶层认定在促使中国让步方面比过去的对话协商方式更有效,将对美国处理涉华议题的行为方式产生长远影响。
在美国对华战略认知改变的情况下,旧的政策框架将不再适用,而新的框架尚未确立。这是一段高度不确定的时期,中国需要谨慎应对。但我们也要意识到,中美关系已不再如以前那样由美方主导塑造,中方的塑造力也在快速增长,双边关系的未来将取决于中美双方今天的行动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