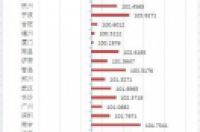中国经济增速自2007年达到新千年以来的高峰后就一路下滑,从当年的14·2%直落到去年的6·6%,而6·6%的速度,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年增速。2007年是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年,由于外需突然消失导致经济下行很好理解,但是在经历了以“四万亿”对冲外部需求萎缩的提振后,经济继续下行不止,这时又开始以为是经济增长阶段发生了转换,是进入了7~8%的中速增长期,但经济下行似乎并没有会停在中速增长水平的意思,而是继续下探到6%一线,从工业增速看,2015年甚至还一度出现了现价负增长。自去年以来在政府有关的正式文件中,也开始正式确认经济下行压力在不断加大。
那么这种持续下滑是外部因素所致么?当然有这个原因,但不是主因,因为2011~2017年世界出口毕竟还是增长了15·9%,中国出口增长了43·4%。有人说中美贸易战有负面影响,但去年中国企业抢出口,到10月的累计出口增幅高达14%,是几年来的最高增速。
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经济下行是内源性因素,但把眼光集中在周期性因素上面,因为经济的表观特征是总体过剩,所以主张应该采取总量宽松政策,甚至是激进的宽松政策,比如不要考虑赤字占GDP的水平而扩大国债购买量,央行可以直接买股买债等,利率也可以学日欧的负利率。总之只要没有通胀,怎么宽松都不过分。
但是自07危机以来,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不够宽松吗?M2从07危机前的40万亿元已经猛增到去年的超过180万亿元,折20万亿美元的货币增量已经比同期美日欧央行QE所增发的货币量还大,而中国经济规模到目前也还只是美日欧之和的1/3。到去年末中国的财政赤字已经占GDP的3%,如果包括地方债,广义赤字已经到10%左右,财政政策也不可谓不宽松了,但为什么总量宽松的反周期政策止不住经济下行?
很显然,外部性因素和周期性因素即使有,也不是经济持续下行的主因。那么是什么原因?
我觉得有两个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就是楼市和车市在去年以来所出现的突然反转。从楼市看,商品住宅现房销售面积2016年的增幅还高达23·3%,但是此后一路下滑到2017年12月的-2·2%,进入负增长,到去年11月,累计负增长已猛增到-26·8%,同时,根据有关统计,去年300个城市的土地成交金额首次出现负增长,自2017年以来土地流拍现象突然增多,去年已高达6%。在车市方面,2018年全国汽车销量为2808.06万辆,同比下降2.76%,为28年来首度出现下滑。
房车一体,有房的人才会买车,而有房有车是从小康生活进入现代化生活的标志。但是房车的突然滞销,是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已经迈入现代化阶段的标志吗?显然不是,因为从千人汽车拥有量看,美国是800台,德日是650台,中国到2017年末才刚140台,还差得远呢。房子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人不是不想买房,而是买不起房,80后、90后更是如此。
那么是什么原因?我的看法是,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是碰到了“二元结构”鸿沟,过不去了。
所谓“二元结构”,就是指中国有一部分先富人群,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高收入标准,但是人口的主要群体是低收入人口。更具体些,根据我的计算,中国目前约有3·3亿人口的人均GDP已经在2·5万美元以上,而有10·5亿人口的人均GDP在4500美元以下。根据联合国的划分标准,1·2万美元GDP就属于高收入人口了,而4500美元还处在中低收入水平。在这篇短文中我来不及介绍具体算法,但是看最近国家统计局长宁吉喆说,中国今年的“中等收入”人口将首次超过4亿,应该从一个侧面印证我的说法。
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结构是“金字塔”型,就是底部大越往上越小;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是“橄榄形”结构,就是两头小中间大,而中国这样的“二元结构”就是典型的“工字型”结构,是上面有一部分高收入人群,中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很小,下面是一个庞大的低收入人口主体。
这种二元结构社会,使中国的一部分先富人群在新千年初期就进入了有能力买房买车的时代,因此中国自新千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不仅得益于新全球化的外需拉动,也得益于先富人群的住房与汽车需求拉动。当07危机爆发后,虽然外需显著萎缩,但是由先富人群引发的房车需求尚未到达高峰,所以中国经济尚能保持住一定的增速,但是到2010年之后,先富人群的房车置业陆续完成,房车需求越来越接近“天花板”,终于量变积累到质变,就是去年发生的房车需求突然掉头向下的情况。我在前面说到,德日的千人汽车拥有量是650台,而到2017年中国是140台,是2亿台社会保有量,如果用2亿台对比3亿先富人群,就是千人660台的德日拥有率。
中国先富人群完成置业的时间在2010年以后,还可以从更多角度观察到,一个是汽车社会保有量的增速,在2000~2010年间是17·1%,2011年是19·9%,达到峰值,此后逐年回落,直到去年的10%。从全国住宅竣工面积看,2000~2010年间是年均5·3%,2011~2014年间是6·3%,还在提升,但是2015~2017年转为-2·4%。所以房车需求的回落都是发生在2011年以后。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先富人群在完成住宅置业后,由于房屋的投资和保值性质,就开始转向购买第二乃至多套房子,由此自2010年以后房产从刚需开始向投资性质转变,“炒房”和房价的高企,以及住房的空置率不断提升,都和先富人群对房屋的需求从刚需向投资的转变紧密相关,而政府房地产调控的失灵,也和先富人群对地产的投资需求有关,因为富人不怕房价高,而是怕不高。
但是在社会群体的另一端,是10亿庞大的低收入人口,如果让他们的收入达到2万美元,需要以9%的速度增长15年。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消费断层:在中国的人口主体有能力购买房车之前,中国已经形成的庞大产能将在很长时期内失去需求端的对象,这个问题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问题,是不可能用总量政策解决的。我们总说流动性不足问题,似乎只要央行肯于释放货币,东西就能卖出去。但是如果供给遇到了不可跨越的需求鸿沟,使商品失去了流动性,商品不流动,货币能流动吗?
由于3亿先富人群的“头部效应”消失,拉动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就相应消失了,所以如果我判断正确,楼市与车市的萧条都不会是短期,而且用什么短期的总量政策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因为10亿中低收入人口不可能在短期内形成房车购买力。住房和汽车从需求看是最大的消费品,从供给看最大的产业集群,所以房车需求走入的长期低迷,就必然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的长期下行压力。
看清楚问题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很显然,只有打破二元结构,重新沟通总量循环渠道,中国经济才能走出低谷。那么,这和城市化是什么关系呢?这是因为,中国低收入人口的主体是8亿农民,虽然统计上的城市人口已经超过8亿,农村人口还不到6亿,但是中国有接近3亿农民工,他们常年在城市劳动却没有城市户口,因此按常住人口计算他们是城市人,但是按户籍人口算他们是农民工,所以中国直到目前按户籍计算的城市人口才刚刚超过5亿,占总人口的比重是38%,这就是经常被提到的所谓“真实城市化率”。而这3亿农民工和5亿多他们留在农村的亲属,既是中国人口的主体,也是中国低收入人口的主体。1978年当处在改革开放起步点时,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3倍,到2017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扩大到2·7倍,有人说产能过剩必然与分配差距相联系,这很对,但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除了市场经济体制因素所造成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更主要的因素是城乡收入差距,有关研究表明,大约超过六成以上的收入差距,是由城乡收入差距造成的。
二元结构所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过积极作用,改革前的历史不说,就说改革后这四十年,如果没有低工资的优势,中国就不可能成长为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就没有领先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的结果。但是,今天的世界在变,07危机改变了新全球化的运行轨迹,特朗普所代表的美国,正在重振美国的实体经济,要用贸易战挡住他国进口,因此从未来长期看,冷战结束后近30年中的世界贸易超过世界经济增速的趋势,已经被改变了。所以,如果说二元结构以前作为一种增加储蓄的机制而存在,有利于中国在长期内保持贸易顺差,那么中国经济在未来长期内的增长,则必须顺应世界经济格局的转变,也转向内需引领增长,才能重振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这个内需增长的源泉,首先就是城市化,以使中国的主体人口具有从小康型消费转向富裕型消费的前景。
还有,即便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的人均GDP超过了1·2万美元,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但是14亿人口8亿是农民,怎么说中国也不是一个完成现代化的国家。
还需要指出的是,恰好在07危机前后,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进入了所谓“刘易斯”拐点,农民工的工资有了显著提升,城乡收入差距也从2007年3·3倍的峰值缩小到2017年的2·7倍,但是根据有关研究,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倾向平均只有60%,显著低于全国居民平均72%的比重,这说明,由于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就不能像城市居民那样生活和消费,所以即使提高了农民工的工资,二元结构仍然是一种储蓄因素,只不过是把以前的企业储蓄,转变成了农民工个人的储蓄。这就提示了只有城市化才能打开内需的道理。
此外,以前政府不鼓励农民进城落户还有一个宏观上的考虑,就是把农村当做缓冲城市经济波动的“海绵”,因为农民在农村有土地,城市经济遇到收缩期大量农民工失业后可以回家务农,所以长期以来无论经济好坏,政府所统计的“城市调查失业率”一直波动很小,就是因为农民工不是城市居民,不在失业统计口径内。但是随着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不断上升,以及政府对农村转移支付的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成为一个历史性拐点,当年农村居民来自城市的收入,包括工资和转移支付两项,首次超过了50%,到2017年已经上升到61·3%,按照这个增速,再过十年农民来自城市的收入就会占到80%以上。而当农民家庭来自城市的收入已经成为主源的时候,城市经济波动就对农民家庭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把农村和农民工作为“海绵”来吸收城市经济波动的意义,就越来越小了。
很多人担心如果大量农民进城转化为市民,他们的工作怎么安置,这个担心其实是没必要的,因为农民工在城市基本上都有工作,否则也不会出什么“刘易斯拐点”。现在要解决的是他们本人和家庭在城市定居的问题。
说到农民工进城定居,就必须解决好住房和社保这两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可以采取类似香港的“丁权”和重庆的“地票”方式,把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田按单位面积折算,用以交换农民工进城的廉租房和社保。目前农村“新土改”已经完成了土地确权工作,给这种“二换二”政策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中国目前有农村户籍人口8·6亿,按有关研究,以中国目前的农业机械化水平,有两亿农村人口已经足够了,因此如果到2035年前中国有7亿左右农村居民转换身份成为市民,是比较合理的水平。如此,届时中国真实城市化率将达到85%,就是一个真正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国家了。
以前城市化也喊了多年,但土地城市化的速度远远高于人的城市化,这次推进城市化的核心,则必须是人的城市化。因此,农民以土地换廉租房和社保,不是把土地带进城市,而是要留给村集体,好让中国的农业用地走向规模化经营,也利于农业机械化的进一步发展。导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长期巨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人多地少,农民靠少量土地搞农业生产富不起来,所以大量农村剩余人口进城,也是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按有关测算,安排一个农民工转换身份,包括住房和社保需要大约10万元,因此7亿农民进城需要70万亿元,为此可以发行30年期每年5万亿元的城市化专项国债,未来十七年就是大约85万亿元,足够了。年均进城的农民大约就是4千万人。起步阶段可以低一些,比如在3千万以下,高峰时可以安排5千万上下,国债的发行规模也可以随城市化推进速度而安排。
发展经济学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会有明显高出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就是因为人口主体处在从低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转变的过程中,因此城市化不仅可以带动中国经济走出低谷,而且可以继续保持较高速度增长。展望世界范围内,没有一个国家有类似中国这样的巨大城市化空间,而世界经济又正面临着将由美国资产泡沫破裂所引发的新危机,所以未来十五年内,只有中国能依靠城市化所创造的巨大内需实现较高经济增速,甚至再现高速度。
我在2009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论城市化是走出低谷的唯一通道”,今天写的这篇“再谈”,不仅是在延续以前的思考,更是突出了紧迫性。“二元结构”早就不单纯是个理论,而是已经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障碍,因此以城市化为纲,打破二元结构,引领中国经济从外需转向内需主导增长,就是既关系到在短期内制止经济下滑,又决定着到2035年能否实现现代化的最主要宏观政策与战略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