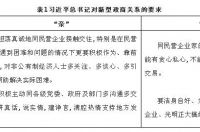每年一度的“亚洲安全峰会”(又称“香格里拉峰会”或 “香会”),是亚太地区安全趋势的风向标,对理解美国的亚太安全政策和亚太地区国家的安全观尤为重要。
同往年一样,在5月31日至6月2日举行的2019年度峰会上,美国国防部长(这次是代理国防部长)阐述美国政府的安全政策,地区国家代表(这次是新加坡)阐述地区观点,以国防部长魏凤和领衔的中国代表团阐述中方的安全政策,其他国家官员和学者各抒己见。
美国在这次峰会上阐述了印太战略的最新进展,地区国家则流露出对中美竞争的焦虑感的急剧上升。这一战略焦虑感对地区和国际安全局势的演变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预示了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形势下一个新的“中间地带”的形成。
美国的印太战略
在2017年的“香会”上,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发表特朗普政府的首个亚太安全政策演讲,重申美国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繁荣的“持久承诺”,并强调这一承诺基于战略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他的主要目的,是向亚太地区关心美国存在的国家做出战略担保:特朗普政府还是会延续美国历届政府对亚太秩序的承诺,而不会从亚太地区“撤出”或者把地区领导权让给中国。这一演讲的基调与前任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调如出一辙。特朗普政府还没有自己的亚太政策,马蒂斯没有使用“印太”概念,而是沿用了传统的“亚太”概念。
至于实施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战略承诺的具体措施,马蒂斯指出了三种渠道:加强同盟体系,开展与地区国家的防务合作并加强它们的国防力量,以及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但这三条都是奥巴马时期甚至更早的美国政府的传统政策,马蒂斯口头的战略担保不能消除地区国家对迷信单边主义的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怀疑。
2018年6月,马蒂斯重返“香会”讲坛,首次阐述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显然,在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美国安全政策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确定印太战略为新的地区战略,这在2017年底和2018年初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防务战略》这两个重要文件中都有明确体现。马蒂斯将印太战略概括为深化同盟与伙伴国关系,支持东盟中心性,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他指出这一战略的四大方面:加大海上力量建设,强化与盟国和伙伴国的军事协作,加强与伙伴国关系的法治与透明度,提倡市场引领的经济发展。在地域上则面面俱到: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大洋洲、太平洋岛国甚至英国、法国和加拿大都在其视野之内,大有把这一广阔地区的诸多国家进行串联之意。
美国副总统彭斯于2018年11月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演讲,是美国推进印太战略的又一重要步骤。这一演讲揭示反制中国的“一带一路”和构建印太地区安全与军事合作网络是美国印太战略的重点。彭斯强调美国将把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政策优先,已立法将国家发展援助金额翻倍到600亿美元,并在现有的美国海外私营投资公司下设立针对亚洲的新发展金融公司。彭斯还宣布美国将与澳大利亚合作建设巴新马努斯岛的隆布鲁海军基地,注资4亿多美元设立“印太地区透明度倡议”,与日本合作为印太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00亿美元,与澳日合作在2030年前为巴新70%人口供电。
可见,到2018年底,美国的印太战略已经渐露峥嵘。这一战略的目标是要维护美国的地区主导权,理念是提倡基于“自由与开放”等原则之上的“基于规则的秩序”,针对的主要对手是中国,领域从安全扩展到经济,手段是通过深化与地区盟友和伙伴国之间的关系来强化其在本地区的军事、外交和经济存在。
2019年“香会”,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把印太战略这一基本框架重申了一遍,但突出了三个重点。一是强调“盟友和伙伴国网络”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二是指出特朗普政府对这一战略的资源投入;三是对美中竞争的性质有所澄清。
沙纳汉说美国国防部正在进行一项“国防现代化”计划(似乎美国的军事力量已经落伍了一样),这一“现代化”工程“开启的技术、伙伴关系和态势的新时代将为印太盟友和伙伴国网络带来史无前例的机遇”。沙纳汉强调美国正在开发的新军事技术对应对未来的军事威胁极为关键。地区国家如果想要获取这些新技术,就需要加入到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网络”中来,与美国一起发展“联合行动能力”(interoperability)。
换句话说,美国要求与其志同道合的地区伙伴在安全与军事战略上与美国对接,一起构建制衡中国的地区安全网络。沙纳汉依次罗列了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泰国、印度、印尼、新加坡、蒙古、台湾及太平洋岛国为这一网络的核心伙伴。前五个国家是美国的传统盟友,其余则是安全伙伴。在海上安全领域,美国想要构建的安全网络不仅是地区的,还是全球的。在印太地区层面,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提供美国安全网络的南北轴辐,正在酝酿中的美国-东盟安全关系则相当于这一网络的内环(将于今年9月举行的美国-东盟联合海上军演是这一安全关系的一个进展),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相连通的印太地区由此成形。在全球层面,美国邀请法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西班牙等国参与印太地区事务(特别是针对南海和朝鲜),为美国的印太安全网络提供“外环”支持。
这是美国亚洲安全战略的“网络化”又一步骤。这种“网络化”从小布什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了。从沙纳汉的演讲看,特朗普政府“网络化”策略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求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做出更大的贡献,特别是资源投入上的贡献,帮助美国分担安全成本。这和特朗普政府的总体同盟政策是完全一致的。比如,在欧洲,特朗普已经多次要求北约盟国提高军费。
沙纳汉以“包容”和“共享”等原则为这种以美国为中心的地区安全秩序正名,同时批评中国的地区安全观是为了建立“排他性优势”。这一话语与中国的安全话语大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也强调包容与共享的地区安全秩序,同时批评美国的安全政策是为了谋求一己之私。中美之间的这种“镜像”式的认知与相互指责也许并不令人惊讶,更关键的问题是地区国家对中美安全政策的认知——这一问题将涉及下文讨论的“中间地带”问题。
特朗普政府显然了解地区国家对印太战略投入不够的批评。因此,沙纳汉强调印太战略不是文字游戏:“这一战略是国防部预算的根基并将推动资源使用。”在经济领域,他提到国会通过的600亿美元的国家发展援助金额。在安全领域,他强调“一个意义重大的现代化努力”。提交给国会的2020财年的国防预算,将有1040亿美元用于研发,为史上最高,同时还有1250亿美元用于作战准备和维持项目,而这些投入都将集中在印太地区,因为美军已经把这一地区作为“优先战区”。在问答环节,沙纳汉指出印太战略与之前美国政府的亚洲战略的最大不同之处,是“美国国会和总统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战略的根本资源投入与以往不同。过去我们有战略,但没有资源和资金。”现在国会和特朗普的支持意味着印太战略的资源将逐步到位。
美中竞争的性质
中国当然是美国把印太地区作为优先战区的原因,沙纳汉对此并不讳言。他影射中国的地区战略有一套“胁迫的工具箱”,包括把争议地区(即南沙岛礁)军事化、影响他国内政、掠夺性经济策略、偷窃他国军民技术等等。他明确美中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共存的关系。美国愿与中国在利益交汇时合作,包括通过两军对话管控风险、应对各类跨国威胁、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等等。但在必要的时候美国也要和中国竞争。他表示:“竞争并不意味着冲突”;“不用害怕竞争;只要大家都遵守国际上认可的规则,我们应该欢迎它。”这是美国高官首次对美中竞争的性质有所阐述。在问答环节,沙纳汉认为,“竞争意味着按规则行事”,竞争应在规范和规则的基础上进行。他因此提出美中两国通过沟通和合作建立竞争的规范和规则,美中可以发展一个建设性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具有建设性的竞争。在他看来,美中竞争应在规范、规则和沟通的基础上进行。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评论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竞争”的观点。
美国要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这种竞争的性质和形式如何,是一个重大问题。沙纳汉提出了美方对这一问题的初步认识。从他的话语看,美国军方并不认为竞争就是对抗或者冲突。他补充说,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不是要与中国对抗,而是希望与中方展开公开对话。美国军方希望开展美中两军对话,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合作。对话与合作的目的是避免误解与误判,美中关系尚未恶化到“搏斗”的程度。他举出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决议的例子作为美中合作的一个领域,认为中国可以阻止朝鲜在中国近海的船对船石油转运。
新“中间地带”
沙纳汉的讲话,一方面是重申美国对相关地区国家的战略承诺,一方面也有淡化美中竞争的对抗性的意思。但从地区国家对美中竞争的焦虑感来看,实现这一双重目标的难度非常大。沙纳汉的讲话,恐怕是加剧而不是减轻了地区国家的战略焦虑。沙纳汉极力强调同盟与伙伴国网络体系对美国印太战略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加入美国的安全网络是地区国家获取美国军事技术和资源的前提。放在美中竞争的背景下看,这无异于“拉帮结派”,让这些国家在美中两国之间选边站。
在这之前,2018年11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巴新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已经公开要求地区国家在美中之间做出选择——当然是选择美国。“要知道美国提供了一种更好的选择”,他说,“我们不会让我们的合作伙伴淹死在债务之海。我们不会胁迫或损害你们的独立。美国以公开、公平的方式行事。我们不会提供一个约束性的地带,或一条单向的道路。”
在沙纳汉演讲的前夜,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本次“香会”的主旨演讲。这是一篇中肯、理性的演讲,值得中美两国高度重视。它想要传达的核心信息,是美中竞争将“殃及鱼池”,迫使地区国家做出艰难的战略选择,严重破坏地区安全秩序。李显龙演讲的前三句开宗明义:“我们的世界正处于转折点。全球化正在受困。美中关系紧张态势正在加剧,和所有人一样,我们新加坡人忧心忡忡。”
谈到中美关系,李显龙希望中国认识到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2001年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中国;中国官方立场明确支持全球化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重要的是言行一致,中国应摒弃交易式和重商主义的经济策略,克制、合理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对美国,李显龙的期望是美国接受中国将持续发展的现实,并认识到遏制中国的发展既不可能也不明智。美国应该努力寻求一种能把中国的合理诉求融入到变化中的国际体系之内的方式。这需要美中两国——以及其他国家——一起合作来对当前的国际体系进行创新与变革。美中两国需要理解对方的观点并调和相互的利益诉求,但当前根本的问题是中美战略互信缺失。
李显龙认为,即便中美竞争加剧,美苏对抗式的冷战也不可能出现。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高度交融。在亚太地区,中国是所有美国盟友和伙伴国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是这些国家的盟友或朋友,但中国是它们的最大贸易国。它们想与中美两国都做朋友,因此希望中美能够和平解决分歧而不是陷入对抗。如果新冷战真的发生,这些国家不会做出清晰的敌友之分,亚洲地区也不可能出现类似于冷战时期的北约或华约那样界限分明的军事集团。
换句话说,一旦中美战略竞争加剧,很多国家将陷于“战略游走”的状态。它们无法做出站在美国或中国一边的绝对承诺,但又不想过度“冒犯”这两个国家,因此“三心二意”将成为这些国家战略心理的常态。以新加坡为例,新中关系的定位是“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同时新加坡是美国的“重大安全合作伙伴”。中美关系良好时,新加坡的对华和对美政策是从新中和新美双边关系的角度制定的,不需考虑中美关系这一层次。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国家利益或价值观冲突时,新加坡也不免需要反对美国或者中国,但很少需要同时反对这两个国家。但是,一旦中美对抗加剧,新加坡很可能需要在不同程度上同时反对中美两国,或者只能给予中美两国不同程度的支持。无论哪种应对都无法令中美两国同时满意。
这种“战略游走”的新趋势,预示了在美中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新的地区与国际政治的“中间地带”的出现。之所以为“新”,是因为中间地带的概念最初是由毛泽东在冷战初期提出的。根据《毛泽东外交文选》的记载,1954年8月,毛泽东同来访的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话时提到:“美国反共是把它当作个题目来做文章,以达到它们另外的目的,首先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带。美国在北美洲处在这个中间地带的那一边,苏联和中国处在这一边。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欺负它们,控制它们的经济,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这包括日本、德国在内。”这时中国不是中间地带的一部分。中苏同盟分裂后,毛泽东开始把中国列入美苏之外的中间地带。他在1964年7月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是第一个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是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中间地带的国家都是反对美国或者苏联的控制的。
但当前正在形成中的中间地带的“新”,也在于其性质与冷战时中间地带的性质有所不同。毛泽东认为亚非拉欧的广大国家都属于中间地带,这未免夸大了这些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实际上,北约和华约的国家虽然各自对美苏有不满之处,但这些不满属于同盟内部的牢骚,而不是说战略共识的缺失。但他的判断倒契合当前中间地带的性质。美国在冷战时期构建的庞大的全球同盟体系仍然存在,但这些盟友在美中冲突时是否就会站在美国一边,是一个未知数,至少不同国家的态度会有所不同。像新加坡这样的美国“重大安全伙伴国”,已经明确非不得已不会选边站。如何处理这一广大的新中间地带,对中美两国外交而言,都是重大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