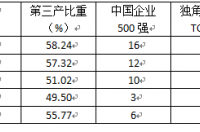历史地看,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的整体道德会随着经济发展、个人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古人孟子的“有恒产者有恒心”和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都是普遍而永恒的真理。
近代工业文明开始以来,人类道德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道德的根源在于宗教,近代以来,国家也开始有能力通过经济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来干预(增进或者阻碍)人类道德的产生和发展。工商业文明一个显著的特点在于“计算”(“推理”)之上的理性,因为通过理性才会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财富。同时,经济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为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普及和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均寿命的增加等提供了物质条件。
工商业文明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人们从农业文明之下的互不关联“个体劳动”脱离出来,走向了公共空间(市场、工厂、社区等)的互为关联的“集体劳动”,人们在公共空间交往和生活,公共空间的扩展也产生了对公共品的要求,同时也发展出公共道德规范。近代以来政府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主要是为了提供足够的公共品。随着公共(集体)空间的增加和公共品的供给,社会整体道德水平也随之提高;或者说,总体来说,社会整体上变得更加合乎道德了。
总体上说,这些经济增长和道德发展之间的关联,也发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过去由连续不断的社会政治运动(阶级斗争)和短缺经济所造成的总体不道德情况已经完全改观。大多数人已经过上了体面的生活或者小康生活,规模性的饿死、病死、累死现象大大减少,甚至消失。
尽管也有人怀念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但应当说那种道德仍然属于原始和朴素的道德状况,是农业文明的反映,甚至是特殊政治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政治压力下的道德。随着工商业文明的到来以及政治环境的开放和多元化,农业社会的道德以及政治性道德变得不可持续,道德领域的巨变是必然的。
不过,随着社会整体道德环境的提升,个体道德不仅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巨大的问题,处于下沉甚至解体过程之中。也就是说,整体社会的“趋善”环境,没有能够转化成为个体层面的道德提升。那种在很多发达社会所见到的理性、开放、进步、容忍、文明、平和、简单等行为方式并没有出现。很多人变得为了自己的一点点利益而不择手段。
有学者认为,今天的人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但实际上,在很多场合,人们并不精致,而是赤裸裸的利己主义。损人利已,为了达到目标可以不择手段,目标证明手段正确。在政治领域,人们一直把这种行为称之为“马基雅维利主义”。不过,“马基雅维里主义”指的是君主为了达到远大的目标(例如国家的统一),可以不惜一切手段。马基雅维里主义显然也适用于今天的个体。这种手段用过了头,结果便是损人不利已:自己做不了,也不让人家做;自己成功无望,也要阻止人家成功。道德的概念变得如此廉价,以至于一些人认为道德和人类社会发展已经不相关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道德状况?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探讨。
个体行为的(非)道德行为是以往总体环境(包括文化、制度、宗教、教育等)的产物。因此,处于变动时期的社会就会产生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所说的“失范”,即在旧的道德规范已经失去了效应,而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确立起来的时候,个体行为无所适从。传统社会群体的解体、教育内容和方式的改变、人在不同地域的流动、商业化等等都会对个体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对一些人来说,不知道如何行为;而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工业文明意味着城市化。在城市化的早期,尽管很多人已经从农村迁往城市居住,但从其行为方式和道德行为来说,还远远不是城市居民;通俗一点说,就是还不够“文明”。文明一直和城市化关联在一起的。城市化久了,就会出现人们所说的“市侩”,指的是市民的庸俗、虚伪和利益导向的行为。
但“市侩”不应当被视为贬义的,因为它意味着理性计算,是文明的表现形式。“市侩”群体的行为是可以预期的。但新社会群体(包括从农村来的“新移民”)的一些人的行为表现为不可预期性。农村居民的道德规范是建立在家庭和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之上的,到了城市之后,面临新环境,就产生了涂尔干所说的“失范现象”。就行为来说,道德意味着可预期性。在很大程度上说,个体行为“失范”和道德是相悖的。就是说,个体的“道德化”是需要时间的。
竞争压力是所有工商业社会的特征,也是工商业社会进步的动力。个体一旦脱离了传统共同体,而投入工商业社会,那么金钱往往成为衡量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标准。对个体来说,竞争来自比较,即与自己的过去比较,与同一辈人比较。到了新环境,就和新的群体比较。比较产生“绝对落后感”或者“相对落后感”。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比较很容易产生“不甘心”的情绪。这种“不甘心”的情绪很容易导向非道德的行为,即通过非道德的行为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以上这些(非)道德现象在各个转型社会都或多或少会发生。对当代中国来说,个体道德现象还受两个非常特殊因素的影响,即对基于政治之上的世俗道德的幻灭和独生子女政策。
在西方,个体道德的主要根源在于宗教。在中国则可以说是宗教和世俗文化的混合物。中国文化没有类似西方那样的国家宗教,属于世俗文化。不过,这并不是说,个体层面没有宗教。在个体层面,中国是多神教,包括对祖先和各种神的崇拜。即使是世俗文化也具有准宗教性质。作为道德主体的“孔孟之道”,其起源实际上就是日常生活伦理的综合规范。
尽管后来(汉朝)“孔孟之道”被上升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但一旦被确定为官方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更具有了宗教性质,即“国教”。这是因为尽管“孔孟之道”没有类似西方的超然的“上帝”,但因为“孔孟之道”是高度仪式化的,其对统治者和普通老百姓具有很强烈的规制作用。
不过,近代以来的一百来年中,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被视为个体道德的来源。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孔孟之道”已经不在官方意识形态之列。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孔孟之道”有回归的趋势,但远非主流,仅仅是些补充。尽管官方意识形态仍然具有其政治效用,但对个体道德则缺乏实质性的影响。
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方体制以惩罚为主,对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进行惩罚。任何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确可以自上而下地施加于社会,但这样的意识形态很难自觉地“社会化”,成为人们自觉行为(即道德行为)的准则。
中国新一代道德危机
在“文化大革命”成长起来的一辈,曾经对政治意识形态充满激情与期待。但在经历和目睹了这一政治运动对中国社会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之后,这一代开始对从前的理想感到幻灭。而老一代对理想的幻灭也造成他们子女一辈的道德虚无主义。无论哪个社会,父母是下一代道德最原初和最重要的来源。
独生子女政策更恶化了道德环境。个体无所谓道德,道德是群体行为,也是群体的产物。“独生子女”意味着个体。尽管独生子女有父母和爷爷奶奶等,但这是一种“不对称”的群体。在这个群体中,形成的精神便是“自我中心”,甚至极端的自私感,毫无大家庭中所具有的兄弟姐妹之间的互相礼让精神。当“自我中心”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因为缺少这种精神,仍然构成不了一种共同体;如果没有公共道德方面的强有力约束,个体道德很难得到提升。
道德危机并非只存在于中国,任何社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出现道德危机。所以,道德危机无论喜欢与否都会出现,问题在于如何应对危机,通过改善道德环境,增进社会个体和整体道德水平。
在西方,个体道德基本上属于宗教领域,或者说,宗教是道德的主体。欧洲文艺复兴之后,主导社会和个体行为的权威从宗教权力转向世俗权力。但这个转型并不是说宗教消失了或者不重要了,主导大多数个体行为的准则仍然以宗教为主。
近代以来的工商业发展促成了西方社会的快速世俗化,世俗化对基于宗教之上的道德产生了深刻(负面)的影响。但是,工商业文明也为社会个体和整体道德提供了另一种来源。在世俗层面,道德问题在西方基本上指的是法律、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内容。亚当·斯密(Adam Smith)等西方哲学家对此作了充分的论述,他们把道德的关切点从宗教转型向世俗。在他们那里,法律、政治和社会制度体系变成世俗道德的制度基础。因此,当原始资本主义对西方传统道德产生了巨大冲击的时候,这些方面的制度建设挽救了西方社会的道德。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道德罪恶的根源,这是一个阶级社会,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使得一个社会不可能产生各社会阶层都可接受的道德。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只有阶级道德,而没有普遍道德。马克思更是预言,只有消灭了资本主义,才会产生社会道德,无论是个体层面还是整体层面。
不过,西方社会并没有按照马克思预测的方向发展。政治社会方面的制度建设,不仅挽救了资本主义本身,也改善了西方的道德水平。1848年,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预言资本主义的灭亡。之后的数十年里,英国的情况的确持续恶化。但当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发表的时候,英国就通过改革扩张了民主的基础。1885年(马克思去世后的两年),《资本论》第二卷出版的时候,德国就出台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保障体系。这些发展并不说明谁的理论正确或者错误,而是说人类总是可以找到挽救和改善道德的方法的。在马克思之后,他所预言的现象也在不断重复,但社会也在一直寻找自救。
对中国来说,一方面,人们不能忽视个体道德衰落的现状,因为正是道德才构成了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一个社会没有了道德准则,这个社会就会面临解体的命运。另一方面,人们更不能陷于悲观状态,而是应当积极转型寻找道德重建的资源和机制。如果人性不变,那么如同以往,就要寻找道德的宗教和世俗的基础。
如果执政党意识形态没有宗教空间的话,那么应当容许和鼓励国家意识形态给予宗教充分的空间。同时,也要加快推进法治、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建设,为社会个体和整体道德提供世俗的资源,从而给道德提升一个机会,使得他(她)们从极端自私行为中走出来。
一句话,尽管个体道德的主体是个人,个人具有主体性,但个体道德的产生、运作和发展需要一个总体社会和制度环境。个体道德随着总体社会和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要重塑道德,就要重塑总体社会和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