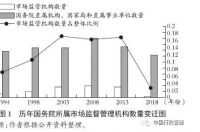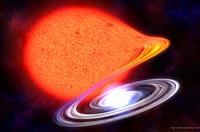
威慑理论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经过长时期的发展,曾经繁荣一时。世界有核国家的基本战略或多或少都受其影响。因此核威慑理论对世界安全环境的影响极大。核威慑理论的体系内容非常庞杂,但其主要的思想构成却相对简单。一般认为,实现威慑主要通过两个方面:通过“惩罚”(by punishment)或通过“拒止”(by denial)。前者指通过建立具有足够毁灭力的报复力量,使得对方顾及到自己的损失而放弃进攻性行为,本质上是防御性的;而后者指的是通过降低对方进攻性行为的成功率来实现威慑,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进攻性的。伯纳德·布罗迪在1959年的观点是,可靠的核威慑力量必须始终处于准备使用的状态,但不能已经被使用,否则谈不上威慑了。托马斯·谢林在1966年提出,伤害另一个国家的能力现在被用作防止其做出某种行为的一种因素。他认为,以武力为基础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是威慑理论的基础。
在冷战时期,世界秩序建立在美苏两强的核保护伞之下,形成相对的核均衡,因此核威慑理论在这段期间里,具有独特的价值,并且有所发展。因为一个相对弱的(拥核)力量可以凭借其极端的破坏力量阻止另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只要这个相对弱小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波突发袭击中有可能存留下来,那么它在国际新秩序体系中就拥有发言权。这样的观点促使更多的国家渴望拥有核力量,实际也推动了核武器以及核技术的大发展。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核技术的发展,核武器在世界的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拥有核武器,这使得核威慑理论的存在价值受到很大的质疑和挑战。2004年,弗兰克·C·扎加雷提出,核威慑理论在逻辑上不一致,在经验上不可靠。亨利·基辛格、比尔·佩里、乔治·舒尔茨、以及山姆·纳恩等地缘政治大师、学者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核威慑远不能让世界更安全,核武器已成为极端风险的因素。在国内,追踪研究核战风险的安邦咨询(ANBOUND)自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以来也曾经多次警告,由于核武器的小型化,尤其是有核国家的普遍化,世界正在面临空前的核战争风险。换句话说,安邦的主要观点认为,核威慑理论已经过时,以核武器作为威慑力量,防止核战争的爆发实际就是一种自我麻醉,现在的世界已经进入一个核对抗的时代,核战略是常规军事战略的组成部分。
如果过去的核威慑战略理论被宣布过时,那么新的威慑理论又将描绘什么样的核对抗模式?
世界潜在的核对抗模式主要是以下几种:1、以色列-伊朗的核威胁模式,确保的是拥核形成的地缘军事优势;2、朝鲜的核挑衅模式,确保的是地缘政治的议价条件;3、印度-巴基斯坦的核优势模式,确保的是常规军事优势;4、美俄中的核均衡模式,确保的是大国间的核秩序。在世界的这些核对抗模式中,最不稳定的是朝鲜,因为它的地域狭窄,战略目标集中,地缘条件使得朝鲜根本无法经受得起一轮核打击,然后再图发动报复核袭击。而朝鲜显然也明白这种地缘条件的根本限制,所以朝鲜的核战略必然带有先发制人的特点,这实际也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始终是半岛局势核心争议的根源。客观而言,我们认为,任何脱离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朝鲜问题解决方案都是无意义的,远不如维持现状更为现实可行。
世界核对抗的另一个重大危险,在于首次运用后的刺激性作用。一旦核武器战术运用的大门打开,很有可能将会一发不可收,世界由此必定将会进入核大战的周期。实际上,这方面最大的危险是在海洋,正如过去安邦研究人员在研究简报中指出的那样,世界的海洋对现在的世界经济结构具有极大影响,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核海洋,大量的核武器及其载具,在海洋中游弋,不明数量规模的核武器处于待发状态。在战术核武器的使用方面,海洋和海军是各国首当其冲的战术选项。这对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贸易以及全球秩序,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并且从未得到过去核武协议谈判重视的严重风险领域。
时代的改变非常迅速,过去同时依靠“惩罚”及“拒止”的核威慑模式正在瓦解,在核对抗来临的时代,未来的核力量及其理论将逐渐向“拒止”方面倾斜。核武器的作战目标将(更快地)由“反价值(counter value)”向“反力量(counter force)”过渡。未来的核威慑将呈现出越来越大的进攻性,而这也同时意味着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将越来越高,世界面临真实核战的风险将会前所未有的令人震惊和困惑。这不仅仅关系到全球核军控体系的瓦解和重建努力,也关系到世界和平发展是否真实,是否将会幻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