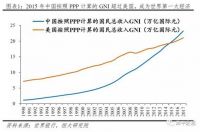近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现实主义代表学者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到中国诸多知名高校进行了巡回演讲,着实刮起了一阵“米氏旋风”。
从表面上来看,他在中国的风靡似乎是因为其一方面反对美国自由国际秩序霸权,另一方面主张遏制中国,对当前中美关系困难局面也有现实针对性。与此同时,笔者认为背后更深层次原因,源于对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话语体系建立,中国有一种迫切需求和引发讨论的期待。
包括米尔斯海默的新现实主义在内,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基本上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上,即民族主权国家已经建成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中国还是一个民族国家建设进程尚未完成的国家。中国的国家关系的逻辑,是完成民族国家建设进程逻辑与大国崛起进程逻辑的叠加,可以说两种逻辑是同样起作用的,而且在很多时候前者的影响力大于后者。
这就意味着中国很多的对外言行,是因为前者的逻辑而不是后者的逻辑引发,例如中国强调国家统一反对台独和加强军事,是为了保证民族国家进程不会出现倒退;而美国则会用崛起大国挑战既成大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看待问题。这实际上是双方使用不同的逻辑看待国际关系,自然话语体系也就会出现很大的不同,甚至出现鸡同鸭讲无法对话的情况。
随着中国的崛起,国际关系理论界对于崛起大国与既成大国之间关系的关注,一直热度不减;然而到目前为止,话语体系的建立基本上还是以美国主导为主,例如权利转移论、修昔底德陷阱、自由国际秩序等讨论的基本概念和框架。
尽管中国也有对很多相关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建设作出重要努力,例如和平发展,讲好中国故事等,但似乎尚未掌握主动权。然而随着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的演变,如何超越西方讨论国际关系的框架,丰富中国对国际关系理论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已经刻不容缓。
为了对应来自西方特别来自美国的知识挑战,中国主要通过强调历史和文化上的特殊性,来建构对应西方的“中国威胁论”的话语体系。毫无疑问,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是从实践中提炼出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也是首先基于西方历史实践基础上的知识结晶。因而,中国从悠久漫长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建构中国的崛起,必然不同于之前大国的理论建构。
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不少学者试图从古代特别是战国时代历史中寻找国际关系理论的视角,已经有不少重要的成果和努力,然而很大程度上似乎仍然与西方现实主义的以力量为基础的分析没有本质区别。与此同时,有时候大量引用古代典故,中国人都不能够看得懂,要让外国人理解可能更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例如中国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论述,而被国内外熟知和接受。
还有一些学术探索集中阐明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来寻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例如中国古代的天下思想和朝贡体制的和平性和稳定性,这些同样是很重要的知识积累。然而这存在一个困境,即过度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就会让理论话语体系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受到削弱。
事实上,中国理论的需求是整个新兴国家崛起的一个集中体现,而亚洲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未来,特别需要有一个地区性的话语体系。目前朝核问题,日韩争端一方面是历史和安全因素引发,但是深层次在于没有一套真正解释亚洲国际关系,并能够被地区国家基本接受的话语体系。
这一点不妨与欧洲比较。为什么欧洲研究能够一定程度上跳出地区研究就事论事强调特殊性的局限呢?主要还是因为欧洲一体化的经历,让他们须要在正视各自特殊性的同时,找出一些能够团结成员国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寻找的历程产生了真正的知识需求。
而东亚在一体化方面进程并不是很理想,真正的亚洲版国际关系理论还没有真正的知识需求。因而双边关系出现问题后,主要依靠通过特殊性的解释来满足民众一时间巨大的知识需求,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进行进一步深入的理论探索和对比研究,结果理论化工作被搁置。东亚国际关系的问题隐藏着研究还不够的“知识赤字”问题。
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在这个背景下知识领域的多元化也势在必行,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必然需要理论的多元化。美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也是随着美国参与国际事务经验增加而变得更加丰厚。中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和崛起大国的实践,在理论创新方面可以说是最有潜力的国家之一,处理好强调特殊性和开发普遍性的关系,以及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来激励地区话语体系建设,值得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