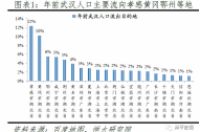引言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依然严峻,舆论乐观和谨慎的态度并存,引发了全球疫情是否即将迎来“拐点”的讨论。2月11日钟南山院士在远程会议时表示:“从目前来看,疫情拐点还无法预测,但峰值应该在2月中下旬出现。疫情拐点由返程高峰的防控情况决定。”钟院士关于疫情拐点和峰值不同的一句话,旋即引起网络上不少讨论,其中很大一部分聚焦于“拐点是否等同于峰值”。“药智新闻”转载了网上普遍的专业说法:“峰值与拐点两个概念其实都是来自于数学概念,峰值广义上就是指抛物线最大值;而拐点,又称反曲点,在数学上指改变曲线向上或向下方向的点,通俗的讲就是变化弧度出现差别的点。”这套网上流传颇广的定义尽管简明扼要,但相较于专业的生物统计定义还略嫌简单,也未能呈现两者背后复杂的历史脉络。根据专业生物统计的说法:“面对非线性(nonlinear)发展的疫情时,拐点的出现时机、次数,乃至于总体疫情统计母数的动态变化关系,与单一峰值或持续高原期(plateau period)的判定有关,都是正确预测疫情发展的关键因素。”此外,峰值与高原期亦是自然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是否达成的重要指标。根据流行病学专业定义,所谓群体免疫指让“静态人口”达到一定程度的染病率,从而在达到感染峰值后出现集体免疫性而显现整体趋势向下的拐点。面对2020年3月以来欧洲疫情失控的状态,英国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即根据欧洲普遍之传染病疫情统计及趋势分析,建议让全国六成人口感染并痊愈以自动产生群体免疫力。这与社会公众的防疫期待冲突,旋即引起科学界及舆论之广泛争议。不论是钟南山还是英国科学顾问,对于拐点的运用都立足于传染病疫情统计,只是作为专业的统计名词使用,但这却不尽符合芸芸大众的通俗理解。大众心理多半简单认为,当疫情统计达到最大峰值且趋势向下时,此一峰值就“应该”是拐点所在。通过媒体的传播,大众认知中形成了疫情趋势向好的“心理拐点”,从而掩盖了专业的“疫情统计拐点”(以下简称“统计拐点”)所应有的严谨与动态性思考。发行于美国的《世界日报》于3月3日报道中国疫情发展时即称:“武汉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新增确诊病例从高峰期逐步下行,......武汉疫情已过拐点,快速上升态势得到控制。”至少就这一说法来看,社会舆论或是媒体代表下的公众认知,让专业的“统计拐点”与大众“心理拐点”出现重合同义。一方面“,拐点”一词出现在日常词汇中,代表着社会大众接纳传染病疫情统计作为思考疫情发展的基准,这自然是中国卫生现代性的一项进步。但以“心理拐点”掩盖“统计拐点”的论调,却又可能因简化专业思考导致误判疫情与防疫松懈。本文拟由传染病疫情统计的知识史入手,从近代以来的大疫案例中,厘清社会大众如何逐渐认识、接受乃至滥用“拐点”概念,进一步理解其中隐含之社会心理,以期为今日防疫提供参考。
罗志田曾根据黄仁宇的研究指出,中国过去百多年来的动乱,是因为未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现代治国手段。就此而言,当前中国社会能以数字为基础思考疫情趋势,反映了卫生现代性上的进步性及防疫策略的现代化。但与黄仁宇关注的西方资本主义与数字管理机制不同,传染病疫情统计在西方公共卫生史上出现并被大众信赖,也只有区区百年左右。当前中国社会接受拐点这类专业名词时,不能忽略近代传染病疫情统计的简短而复杂的历史脉络。
18世纪推行牛痘接种时的政府态度与民间恐慌,应该是近代疾病统计发展的第一个推动力。虽然牛痘接种在临床上的确显现出不错的预防效果,但因为当时对于天花病毒及其感染机制了解不深,加上社会上普遍充满了对“异种移植”的想象和恐惧,欧洲各国政府想要普及强制性牛痘接种实非易事。由于牛痘接种须将异种生物的部分种植(grafting)人体皮下,并诱发温和的类天花反应,自然引起相当的社会抗拒与医学上的争辩。为支持接种的价值与反驳牛痘不会“让人变成牛”,英国医生约翰·阿布斯诺特(John Arburthnot)以“风险-效益(risk-benefit)分析”力图证明牛痘具有预防效力和并不存在变异。到1760年左右,阿布斯诺特的简单百分比分析,被数学家进一步细致化、复杂化。对于死亡率及特异性(specificity)的反复争辩,引来了欧洲学界将统计运用于医学研究的小股风潮。18世纪末,詹姆斯·林德(James Lind)在败血病治疗统计上的纪录,就是这等风潮下的最初成果,也为他赢得“临床统计分析之父”的美誉。林德的研究证明,运用统计方法,可以提炼特定研究现象的规律,为治疗与临床应用提供参考。
随着数学在19世纪被视为一切科学的基础,医学科学化与数学分析的关系愈发密切。但此时的欧洲医学界仍以临床个案的统计分析为主流,以公共卫生事件为对象的传染病疫情统计与分析尚不见踪影。举例而言,法国医生皮埃尔(Pierre-Charles Alexandre Louis)主张对相同病例进行长时段的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致力于将特定疾病的演变过程以统计方式呈现,寻找介入治疗的适当时机点,这里已有类似拐点的意味。到19世纪中期伦敦霍乱疫情迭生的十年间,统计方法在医学方面的应用,依然以临床医学为主流,而非应用于公共卫生领域。如英国医生李斯特(Joseph Lister)为了呈现手术消毒的必要性与效果,以统计方法证明李斯特灭菌法可有效反转术后感染率与死亡率的一般趋势。虽然他仍未使用拐点一词,可在感染率与死亡率趋势的描述上,事实上已与统计学中拐点之意义相去不远。原本仅限于研究医院内特定病症与其治疗的临床统计分析法,后来在伦敦大学生物计量学(Biometrics School,UniversityCollegeofLondon)得到了更为复杂的发展,并与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重视公共卫生的舆论结合,开启了近代公共卫生统计的先声。1893年伦敦大学生物计量学院正式呼吁,采用标准化与数字化分析法研究疫情的总体趋势和特征,又在1903年设立生物计量学实验室(Biometrics Laboratory)。主持该学院与实验室的正是被视为现代生物统计先驱的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作为一名统计学家,皮尔逊将许多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引入公共卫生统计中,并对分析个别疾病之长期趋势及相关疫情提供了崭新观点。拐点与峰值的概念,即已出现在他的许多研究与推论中。1906年哈默(W.H.Hamer)根据19世纪英国季节性麻疹数据建立数学分析模型,推估出麻疹疫情发展具有多个拐点的特性。哈默的研究目的除了寻找过去麻疹疫情的周期性,便是期望为英国社会提供趋势预测,以便提前进行防疫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哈默对拐点的定义是“已知个案的发展曲线与新增疑似案例的纵轴间的交点”。对哈默等人而言,由于疫情发展曲线不尽为一单纯抛物线,其发展曲率和速度常与新增疑似个案的确认率有交互关系,因此在横向时间轴中出现多个拐点是理所当然的。可见,精细化的传染病疫情统计已在20世纪初出现于专业领域。
从历史来看,疾病统计是一个十分年轻的领域。而在传染病调查与分析方法的演进过程中,数学统计方法的确立更是20世纪以后的事情。据此,依附于数学统计方法的峰值与拐点概念或相应判断准则,实在只能说是20世纪10年代以后流行病统计渐臻成熟的产物。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拐点能够被大众认可为一个对于疫情转变的期望值或具有社会信赖的流行病趋势预测值,应该是比近代流行病统计发展更为晚近的事情,甚至需要通过不同历史阶段的集体心理转化与大众卫生教育才能取得。其为大众信任和过度解读的经历,实与20世纪以来传染病疫情统计发展与疫情下的社会状态有着若即若离的辩证关系。简单来说,近代的公共卫生或传染病疫情统计要晚至20世纪初期才初有基础。但社会大众要能接受这一整套奠基于19世纪末的统计观念,乃至于疫情统计分析与预测中的峰值与拐点的概念,还得经过几次大疫的洗礼。
瘟疫的教训:传染病疫情统计的社会接纳与新问题
在19世纪末细菌致病说确立前,统计多半只运用在个别疾病或治疗技术的有效性分析上。因此一般大众对于疫情统计或趋势报告并不关心。社会虽对疫情好转有所期待,但不尽然会对官方统计有兴趣。在以细菌学为基础的公共卫生学确立前,名人染病给社会大众造成的印象更甚于疫情峰值或拐点的出现。简单来说,在20世纪以前,受限于统计与调查方法、细菌病理学、流行病学尚不完备,传染病疫情统计的专业讨论仅限于专家之间。对于大众来说,冷僻的统计叙述还不如名人染病或某地区出现大批死亡病例更令人警觉。拐点与峰值在传染病疫情统计中受到重视,乃至大众开始信任疫情统计并认识拐点及峰值等概念,都是经历过一连串瘟疫冲击后历史教训累积之结果。今以较有代表性之1854年英国伦敦霍乱、1907—1915年美国“伤寒玛丽”事件与1918—1920年全球性流感等大疫为例,说明拐点与峰值在近代传染病疫情统计中现身、受到社会大众重视并内化为日常知识的过程。
(一)1854年英国伦敦霍乱:疫情统计成熟前的社会心理
1854年英国伦敦的霍乱疫情,其实是1832年伦敦首次出现霍乱以来数十年间好几波疫情之一。埃德温·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等持“瘴气论”(miasmatheory)的专家,最早建议实行大规模的城市清洁运动,避免瘴气淤积造成霍乱流行。当宽街(Broad Street)暴发霍乱时,政府部门仍唯瘴气论马首是瞻,查德威克等甚至斥约翰·斯诺的水污染说为无稽之谈。尽管简单的传染病疫情统计此时已得到运用,但显然对双方的争辩无决定性作用。查德威克等人认为斯诺的证据缺乏统计学意义,“几乎没有人发自肺腑相信他的理论”。其中,被认为是实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先驱之一的埃德蒙·帕克医生(Edmund Alexander Parkes),于1855年发表论文指责斯诺的假设无法符合统计原则。但后来属于调和派的威廉·法尔(WilliamFarr)则又有另一套统计推论法。法尔根据1849年的霍乱病例死亡率,提出根据8项解释变量(explanatory variables)得到的霍乱疫情趋势分析,发现各地峰值时间不同,而转折点显受特定区域内卫生行为影响;类似斯诺的建议,他也据此要求自来水公司进行改善工程。法尔在1855年的总结报告中写道:“根据所有的疫情统计证据显示......造成霍乱死亡率的关键变化都是可测度的因素”;他进而呼吁英国专家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疫情。但严格来说,法尔与帕克所做的都只是一种叙述性的统计思考,甚至斯诺对于霍乱由饮水传染的来源认知,亦非来自统计方法。这些被后世误认为是传染病疫情统计的成果,多半只来自他们大胆敏锐的观察与优雅简洁的逻辑推论。
可见,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连专业的医学家与卫生学者,对传染病疫情统计的效力尚且无法达成共识,更遑论局促于生计的一般大众。公允地说,19世纪后半的五十年间,现代流行病学(epidemiology)还在蹒跚学步的阶段,更遑论具有疫情预测能力的流行病统计与预测模型。对于帕克和法尔等人来说,统计学这门专业才出现了不到一个世纪,甚至“统计”(statistics)这一英语单词都刚从德语“statistik”借用不久。19直到20世纪,今日常见的计量性流行病统计才渐渐出现,之后数据图像化的趋势分析才让拐点的位置得以凸显,大众才有条件“望图生义”。
虽然1854—1855年斯诺的霍乱调查是近代细菌学史的里程碑,但从1855年至1885年(前述伦敦大学生物计量学院成立之际),不论是学者还是社会大众都对传染病疫情统计不表信任;相关辩论也仅限于少数学者之间。在19世纪末的欧洲,执行公共卫生统计与传染病疫情统计之目的与今日并非完全相同。如英国公共卫生学者推行的清洁运动就常把劳工阶级视为肮脏与疾病之源头,部分主张几可视为中产阶级不知民间疾苦的空谈。再以1866年伦敦的另一场霍乱为例,此时英国已有相当值得信赖的疾病与死亡统计,相关之人口调查也堪称完备。至于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方面,也出现了进步性的发展。但根据伦敦市发布的疫情周报(Weekly Returns),预测疫情趋势并非进行疫情统计之目的,寻找疫源点或特定易感年龄段和社会群体,才是政府的真正目标。此时伦敦的免费公共供水政策,确实有助于改善个人清洁条件,但在整体居住卫生环境不良与贫困依旧的前提下,城市贫民及其居住区域难以摆脱疫情统计带来的指控或歧视。生计都已十分困难的状况下,一般大众既无心也无力理解或遵循传染病疫情统计的各种讯息。对他们来说,疫情消退是一种心理感受与社会现象,与传染病疫情统计里的峰值和拐点无关。从当时伦敦的公众舆情反应可见,疫情统计与趋势分析的讨论基本上仍是专家间的辩难,一般大众其实毫不关注,以至于疫情略显减退后,大众不讲清洁、不重卫生的生活习惯立即依然故我。以中断宽街公共水龙头一事为例,此举影响了周边数十户家庭的日常用水与生计。霍乱疫情消退次年,附近居民立即强烈呼吁重新开放这个公共水龙头,反映了希望回归正常生活的心理。2008年《纽约时报》一篇专稿在论述宽街关闭水龙头后的舆情时,便描述为市民集体感受到疫情“转折点”(turning point)26已经出现。就此来看,传染病疫情统计在19世纪末仍处于发展初期,专业统计对拐点之判断尚未有定论,而芸芸众生更因生计问题或知识水平,对疫情发展与拐点认知不足,甚至可能在统计拐点出现前,就以心理感受的转折点作为抵制防疫工作的理由。
(二)1907—1915年美国“伤寒玛丽”事件:公众如何接纳疫情统计
玛丽·梅伦(Mary Mallon)是移民美国的爱尔兰人,1906年起受雇担任富商的厨娘。其受雇期间,富商一家11人中共有6人感染伤寒;担心情势严峻,富商雇用经验丰富的专家索柏(George Soper)调查,赫然发现从1900年到1907年,曾经雇用过玛丽的7个家庭都出现了伤寒病患,共有22人患病,还包含1名女性死亡案例。索柏寻求纽约市卫生局协助,确认玛丽为伤寒带菌者而将之移送隔离,至1909年释放。1915年纽约又有医院出现25名伤寒病例,卫生人员调查后发现该医院厨娘竟然就是改名后的玛丽,于是再将其移送监禁隔离直至过世。由于发现与确认玛丽为伤寒带菌者的过程曲折离奇,“伤寒玛丽”之名号遂不胫而走;这一过程涉及传染病调查、医学伦理、法律人权等面向,更是日后公共卫生与医学人文的经典教案。
伤寒玛丽事件发生的20世纪初期,细菌致病论已广受接纳。因此传染病疫情统计的目的,除如前之确定疫源地外,也新增了根据特定致病微生物性状预测疫情发展的意义。只是在“伤寒玛丽”被确认前,仅少数欧洲学者怀疑有无症状感染者的存在,而且这类“会移动”的疫源中心也全然不存在于当时疫情统计的思考中。无怪乎纽约市政府此前的传染病疫情统计无法确定伤寒疫源地,更无力呈现简单线性的伤寒发生周期、峰值与拐点。这样的疫情统计当然不能安抚人心,最富裕与清洁的地区发生密集疫情,令社会大众深感恐慌,成为大众呼吁公共卫生统计改革的动力。伤寒在20世纪初期的美国高居八大死亡原因之一。此时美国大众受社会成见的影响,仍把伤寒视为“无知贫民才会感染的疾病”。某些流行病学家甚至提出“脏手指与脏苍蝇”(dirty fingers and filthy flies)理论,认为卫生习惯不佳的无知贫民间的频繁接触,以及生活环境里充斥苍蝇污染,才是纽约伤寒传播的主要原因。但1906年后出现的数起伤寒感染个案,造成重视清洁的富人也会染病的普遍印象,导致此等社会成见无法自圆其说而形成恐慌。举例而言,索柏的伤寒疫情统计仅显示了1.6‰的低染病率,只因为他针对富裕及清洁区域进行疫情统计研究,顺应了社会大众恐惧之印象,成功塑造了他在纽约市民间追捕伤寒玛丽的“神探”形象。
纽约市的伤寒疫情并未因伤寒玛丽被隔离就出现拐点而趋势反转,或许因为过于关注抓捕伤寒玛丽的戏剧性,在媒体推波助澜下,导致大众心理预期变为猎捕更多的“伤寒玛丽”方能遏止疫情。在此等心理状态下,专业的统计报告不过是大众“猎巫行动”的“科学”依据。例如,1910年怀俄明州发现的“伤寒约翰”(Typhoid John),就被当地媒体根据粗糙的政府疫情统计信息断章取义,指控其造成36名黄石公园游客的感染。尽管此时流行病学专家已能推断疫情进程、峰值与拐点,但大众对疫情的理解与期待,却始终停留在“发现疫源就是转折点”;唯一的差别只在于“固定的”疫源地变成了“移动的”无症状感染者。现代公共卫生统计与细菌学的进步并未改善社会的集体认知,舆论反倒常从官方报告中撷取片段,满足大众对疫情拐点的想象。
面对大众心理认知偏差,政府对传染病疫情统计的改进与对社会大众的卫生教育可能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对近代传染病疫情统计的发展来说,与索柏合作的贝克医生(Sara Josephine Baker MD.PhD.),才是让疫情统计与峰值、拐点等概念获得大众信任的关键人物。在调查伤寒玛丽期间,贝克即意识到既有的疫情统计已无法反映真实的伤寒疫情,更何况富人区的沦陷令大众对市政失去信心。其后,纽约市卫生局也认识到,让疫情统计与趋势预测具有可信度,不仅是防控手段,也是降低社会恐慌的重要策略。于是1908年纽约市公共卫生部门为安抚民心,由贝克出面强调政府将根据“细菌科学原则”进行疫情判断与改革,也顺应舆情地承诺要继续抓捕类似玛丽这类无症状感染者。在官方发言中,贝克相信峰值与拐点仍是相当重要的参考指标,只是两者的价值须根据疫情全局与致病微生物特性而定,而非依赖个别峰值或拐点的出现就能预测疫情走向。就此而言,她的观点与前述钟南山的说法并无二致。为重振社会大众对政府疫情统计的信心与理解,贝克一方面推广清洁与卫生运动,支持贫民区的持续消灭蚊蝇与环境清洁运动;她还将特定公共卫生与医疗政策的实施搭配疫情统计与总死亡率变化加以说明,用简明小册子的宣传方式,说服大众相信政府的传染病疫情统计,让纽约大众感受到拐点“可能”发生在正确的卫生行动之后而非发现疫源后。此后,峰值与拐点常被引用作为官方疫情统计与趋势分析的科学证据,也是常见的安抚民心的重要指标。贝克任职纽约市政府时期是纽约市卫生现代化的关键期(1914—1922),也是美国公共卫生史上的现代化的里程碑。
20世纪10年代中期,美国城市中产阶级兴起一股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思潮,强调个人应为自身健康负最大责任;为保护个人的健康与福祉,除了严守个人卫生外也须排除环境中的健康威胁。因此,如何读懂疫情统计、理解拐点,成为公众自我健康保护的一股社会时尚。为满足个人主义下舆论的期待与实际的公共卫生需要,美国各州纷纷学习纽约市,改进传染病疫情统计。但此时在一般大众用语中,讨论运势或情势转变的口语用词“转折点”,仍经常是疫情“拐点”的同义词,甚至在期待情势向好的心理影响下,与“峰值”合而为一。《纽约时报》在1915年的专题报道,即反映出这样的大众心态及用语习惯,其引用疫情统计资料作为佐证,声称“伤寒玛丽”的隔离监禁就是纽约市伤寒疫情消退的转折点。但事实上,一直到1930年代,伤寒疫情都存在周期性爆发,大众的猎巫心态与日常化的拐点概念,虽然加强了对卫生科学的乐观信心,却也可能造成轻忽而导致疫情反复发生。要言之,“伤寒玛丽”事件发生后,20世纪初期的纽约市民应该已经接受了疫情统计作为分析疫情发展之工具,相比19世纪中期的伦敦市民的确跨出了科学思维的一大步。但相对地,由于像贝克这类的专家才能掌握与理解复杂且专业的疫情统计,芸芸大众常把“转折点”的心理感受披上专业“拐点”的科学外衣,从而让寻找拐点变成“猎巫”,或造成对科学防疫的过度乐观。
(三)1918—1920年的全球性大流感:误判“拐点”的严峻后果
在美国,传染病疫情统计方法的标准化,大约与医学现代化改革同时兴起。纽约市卫生当局在伤寒玛丽事件后进入了新的标准化与现代化阶段,美国东海岸各地也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间点,陆续进行相关之改革。20世纪的前20年中,美国已有40个州建立常设公共卫生机构,专司卫生统计与细菌检验等工作;纽约市卫生局更因伤寒玛丽事件与其重要经济地位,成为其中举足轻重的单位。美国的公共卫生学与卫生统计机构逐渐趋于标准化、普及化。
1918年大流感爆发之际,因为统计分析方法的普遍应用,西方主要国家的疫情统计方法与项目都已非常相似,使得各国疫情信息得以互相交流并促进共同防疫,也方便事后学者进行比对研究与检讨。以1918年12月纽约市卫生局月报的一项统计为例,作者制作了9幅不同分类与分析目的之统计图表。有的图表列出1890年以来的流感死亡率趋势,并通过绝对峰值的高低比较显示1918年流感为历年来最凶猛者。有的图表包含各年龄段流感死亡率比较图、性别与婚姻状态等生理和社会因素与死亡率的对应关系等,其中月死亡率趋势变化显示,死亡率峰值出现于10月中旬、疫情拐点紧接着在两周后显现。同期另一篇报道也可作为此时西方疫情统计高度趋同的证据。在名为“卫生局记录之入院流感病患”(Hospitalization of influenza patients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的论文中,作者将包含中国在内的42个国家与地区之入院治疗及死亡个案列表比较。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与某些亚、非地区的数字显示出不合理的偏低,或可据此推断,这些地方尚未建立现代的标准化传染病疫情统计制度。这种疫情统计的标准化现象与公众认知的共有特征,随着近代传染病疫情统计方法与美式医学的全球化,在1930年代后成为亚洲诸国的普遍现象。
然而,美国政府与大众过度自信及乐观的心理,却造成美国面对大流感之初未能充分应对,以致原本严峻之疫情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举例而言,为庆祝即将到来的战争胜利,费城在 1918年 9 月 28 日举办盛大游行,超过 20 万人上街参与。卫生专家对此并非没有忧虑,但显然对于科学防疫的信心,蒙蔽了大众对疫情的警觉性。在游行举办前几天,费城海军医院负责人乐观地告诉采访的记者 :“没有提高警戒的必要,我们相信一切都在掌控中。”但事实却证明,游行结束的一周后,据估计约有 45000 名费城市民感染。流感疫情之所以在费城快速蔓延,并不是像过去一样,是因为疫情统计不够精确或趋势推测有问题,很明显卫生当局与公众的过度乐观、心态轻忽才是主因。根据詹姆斯·希金斯 (James Higgins) 的研究,当时费城的公共卫生统计较之其他美国大城市毫不逊色,疫情分析也预测到,在这场充满了爱国情绪的大游行一周后,流感在费城的感染率将达到第一个峰值。但因缺乏防疫警觉,此后费城却进入疫情高原期,而非如某些专家预测与民众期待那样,随峰值后出现疫情拐点且趋势渐缓。
1918年底的费城并非特例,或因胜利大游行、或因持续的群众聚会与社交,甚至是芝加哥、匹兹堡等地为迎接战后经济生产而大肆开工的拥挤生产线,均推动流感疫情快速蔓延全美,所有主要城市面临医护短缺无一幸免。一份针对疫情后期1919—1920年美国50个主要城市抗疫的研究显示,尽管各地峰值与拐点出现的数值与时间都有不同,但全国疫情统计方法与评估模式已渐趋标准化。根据835份《纽约时报》的相关报道分析发现,由于以共同的疫情统计为基础,纽约舆论普遍相信,个别拐点的出现当为整体疫情趋势向好的“曙光”。但事实上,期待疫情快速消退的乐观态度却未必符合疫情统计趋势,有时反而造成个别地区防疫松弛或忽视新疫情已兵临城下。1919年春,人口移动屡屡造成美国疫情拐点盘旋。此时统计专家虽然发现峰值已经出现,但对于拐点是否同步显现众说纷纭。但美国大众却根据简单而线性的疫情经验,认为峰值过后就该是疫情向好的拐点而放松戒备,没想到因此造成人员移动以致流感再次蔓延。入夏以后流感的暂时衰退,强化了舆论简化“拐点”概念后反映出的大众乐观心理。面对疫情在秋天的二次来袭,又由于缺乏有效治疗药物,医生仅能提出已知的防疫手段作为给大众的建议。如耶鲁大学宣布禁止校园与周边所有的学生聚会,并要求师生保持社交距离2英尺以上。边境各州也都下令封锁边境禁止移民进入。
严峻且无法快速消退的疫情,终于让社会大众冷静下来,一方面严格遵守专家建议的防疫手段,另一方面也再次呼吁传染病疫情统计的专业化及细致化。疫情最终消散,但改进传染病疫情统计的呼声并未停歇。接下来的数年间,美国各州对于现代公共卫生与疫情调查统计人员的需求持续上涨;哥伦比亚、哈佛、耶鲁等名校纷纷设立公共卫生学院。根据1918年大流感所获得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奠定了后来预防医学专家选择流感疫苗种类、卫生专家预测疫情趋势的重要专业基础,另一方面也成为疫病流行时大众遵循医嘱与建立心理期待的依托。这一系列历史发展奠定了公共卫生学与流行病学的专业地位,若非如此,疫情统计与预防医学的专门机构如CDC等实无由出现。简言之,1918年大流感过后,疫情统计不仅能够分析疫病发展现况,对疫情趋势的预测能力也增强了;这些发展都有利于预防医学适时介入防疫、抗疫,也常是安抚大众心理的专业依据。不过,从历来疫情如2003年的SARS、2009年的H1N1流感乃至当下的新冠肺炎(COVID-19)中可以发现,大众以心理拐点比附统计拐点的情况仍不时发生。
大众心理拐点的社会建构
如前所述,以统计方法研究疫情发展始于19世纪后期,可谓比较年轻的领域。因此在“伤寒玛丽”事件发生之前,由于疫情统计方法不够可靠,专业的“统计拐点”与“心理拐点”的重叠,完全可以从历史脉络中予以理解。比较值得注意的反倒是1918年大流感之后,尽管传染病疫情统计与预测的科学能力已有长足进步,但去专业脉络化的大众心理拐点却依然存在。这种情况或许不该再归责于疫情统计与分析技术的不足,而须回到社会情境中予以理解。
首要原因在于20世纪盛行的以科学主义为特征的时代气氛和思维方式。疫情中专家的讨论,尽管未必能深入到大众语汇中,但相关词汇如峰值、拐点、疫情趋势等,却已在舆论与街谈巷议间流传开来。就本文题旨而论,社会舆论脱离统计专业并将“拐点”口语化,当然显示出科学的疫情统计一定程度上深入人心,也反映了20世纪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科学主义”(scienmtism)信仰的现象。所谓科学主义,按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的说法,是对于科学(science)及其语汇的滥用,甚至是将其作为不可置疑的本体的一种信仰态度。根据苏珊·哈克(Susan Haack)提出的科学主义六项判断指标来看,前述三大疫尤其是1918年大流感时期舆论有关拐点的使用语径,就符合其中五项指标:1.充满敬意地使用任何挂有科学头衔的词汇;2.恣意使用科学数据或名词,而不了解其生成的背景与脉络;3.对于所有号称科学的说法,都先入为主地预设为真理;4.坚信科学方法是获得真理的唯一手段;5.相信科学可以带来一切的答案。事实上,曼苏尔(Kramer S.Mausner)等学者早在1970年代的研究中,就指出流感期间舆论强调疫情统计科学的言论、社会期待疫情统计能预测拐点的心理,正是受到这种科学主义大众心理的影响。尤有甚者,利用科学语汇包装社会成见,也是一种疫情民粹主义的极端表现。这种用科学包装的民粹语言,除前述的各种疫情中的激烈言论及排他行为外,也出现在2020年4月以来意大利、西班牙以及美国等地对于新冠病毒来源及称呼的无谓争执上。总体上,大众以心理拐点比附专业统计拐点的做法,只是把科学统计作为一种信仰,无关于专业疫情统计所需考虑的局限性与复杂性,更有造成防疫心态松懈的风险。
集体心理则是形成此等现象的另一原因。面对疫情造成的集体恐慌,人性中不免有期待瘟疫消退曙光乍现的一面。然而随着疫情时间延长、范围扩大或反复发生,质疑的声浪不免一波胜过一波,特别是企图在未知中寻找并歼灭疫情的“源头”。以伤寒玛丽事件为例,受教育程度有限的爱尔兰移民玛丽,本就符合大众想象中可以归咎的他者形象,媒体更以“科学”数据暗喻她是充满伤寒病菌的“毒妇”与疫源中心。尽管这样的叙事满足了社会舆情,认为抓到“伤寒玛丽”就该是拐点出现之时,但事实上纽约的伤寒疫情却仍周期性持续发生。简单理解疫情拐点、将疫病归责于他者,除了舒缓大众情绪不安,无助于防疫抗疫。尽管1918—1920年的大流感已经过去,今日的传染病疫情统计与拐点预测也精进许多,但在SARS、H1N1流感等疫情中,以统计拐点包装心理拐点的情况其实从未消失。心理学家菲利普·斯特朗(Philip Strong)分析多项瘟疫下的大众反应后认为:人性对于他者的不信任与未知前途的恐惧,才是疫情恐惧或期待的根源;对大众集体心理来说,科学论证与分析只是用来巩固这些心理状态的片段而已。前述伦敦霍乱时期针对都市贫民的歧视、伤寒玛丽事件发生后对新移民的排挤,乃至美国以“西班牙女士”(Spanishlady)谑称1918年的未知流感,都与这样的集体心态有关。
从理论层面看,尽管西方医学界意识到疾病发生的原因往往是复杂的,但疫情统计资料大多是统计性、数字性的,以致大众并不容易理解形成该疾病的原因。疫情预测统计专家更专注于可控因素的标定,而把影响疫情发展之社会因素留给社会舆论自行运用甚至想象。因此,疫情当下社会舆论对疫病的描述,无疑会掺杂许多现实利益的考虑,具有社会建构性的特点。历经约百年发展,当前流行病统计与量化模型早已高度专业化、复杂化,远远超过一般常识或社会媒体所能理解,但大众对流行病调查统计的简化理解却依然故我。早在2017年,就有公共卫生统计专家对于政客与媒体对流行病统计与预测模型的名词及概念断章取义感到忧心。但专业人士的谔谔之言,无力挽回公共卫生统计专业的民粹化趋势。在新冠肺炎流行时期,随着政客与媒体尤其是网络声浪的媚俗和推波助澜,各种满足大众心理期待的言论如雨后春笋四处蔓生。不仅峰值、拐点被从原本复杂专业的统计模型中剥离,而被赋予常识性但过度简化的意义,某些国家面对盘旋的拐点,甚至把预测及分析动态模型中的“压低曲线”(flattening the curve),作为鼓吹大众支持防疫政策的目标与口号;这其实无异于20世纪初美国大众利用流行病统计及拐点满足乐观期待的社会心理。要言之,大众心理拐点的产生其实无关统计拐点的科学专业性,归根结底是个人性与社会建构性的问题。
总结来说,当1854年伦敦暴发霍乱时,拐点与峰值这两组概念尚未在公共卫生统计中完全启用,整个英国公共卫生学界对传染病疫情统计与拐点的理解非常模糊,社会大众对此更是漠不关心。伤寒玛丽事件时政府的疫情统计已将对拐点的推测纳入,其间也显示出峰值与拐点的盘旋及不确定性,说明公共卫生部门应当认知到,疫情发展不只有单纯的线性函数趋势,而峰值与拐点间亦非一对一的映射性关系。随着疫情扩大与名人罹病的渲染效果,大众才发出疫情统计与趋势预测精确化的呼吁,从而成为政府改善传染病疫情统计、定期发布峰值及拐点变化以安抚民情的驱动力。此时大众虽因科学主义之影响,对专业的统计拐点有所参考与信赖,但还不能将两者等同视之;严格来说,大众心理所理解的拐点更接近用科学包装过的、日常语言中的“转折点”。一战后期的大流感爆发后,传染病疫情统计已具备复杂的数学模型预测功能,这一方面虽然满足了专业疫情统计与大众期望精准预测拐点的功能,但复杂的统计模型却再一次脱离日常知识的范畴,专业化的统计拐点与大众心理拐点形成落差。此种现象,除了再次显示社会对疫情精准统计寄予厚望外,也反映出心理拐点作为一种人性与社会心态反应的本质,并不会因疫情拐点预测的准确度增加而有所动摇。
结语
上述统计拐点与心理拐点的落差与纠结,同样可能发生在当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随着新冠肺炎确诊数字下降,大众的希望于焉燃起,对于每一个峰值或拐点的提出,都禁不住视其为疫情改善的曙光乍现。如2020年2月6日《北京青年报》上出现一则以“拐点”为探讨主题的报道。文中对于拐点的定义是符合统计学原则的,对于影响拐点变动的因素说明,也确实应和流行病学的分析基准。这些面向一般大众的内容,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科学防疫和统计预测的高度接纳,是中国卫生现代性的一大进步。但另一方面,或许是为了安抚疫情下煎熬的民众心理,报道也指出“所有的感染都会有一个下降的过程”,而拐点就是这个下降过程的始点,于是热烈期待“迎接‘拐点’早日到来”。这种态度似乎重现了20世纪初伤寒玛丽或大流感时期的美国舆论氛围。事实上,当大流感疫情稍歇时,专家即已注意到拐点的出现与判断存在许多前提;对比各国拐点发生脉络后,亦确认各国社会与医疗情况不同会造成拐点出现的条件差异化,甚或造成拐点盘旋、疫情不消的状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大众心理拐点认知所造成的过度乐观,反而可能导致防疫松懈,出现疫情复发的尴尬局面。
对比数月以来中国境内疫情变化趋势以及当前欧美瘟害正炽的处境,以个别趋势之疫情拐点,粉饰大众心理的乐观自信,恐怕有重蹈历史覆辙的危殆。尤其以当前全球交通之迅速、人流货运之频繁,疫情趋势再起变化并非毫无可能。《光明日报》上的一则报道有言,“别让‘心理拐点’越过疫情拐点,就是‘科学面前不打诳语’......‘将人心比自心’......识大体顾大局”,这番话非常适合作为本文结语。历史镜鉴,以大众心理拐点掩盖专业的疫情统计拐点,往往是以增加抗疫风险为代价。期盼拐点出现、瘟疫退去、早日回归正常的心理,人皆有之,但不可只看峰值就误以为拐点即在眼前,拐点本身只代表变化的开端,无须为此过度乐观。文艺化或民粹式的语言或可满足人的心理期待,但理解科学、相信专业人士,才是平安度过疫情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