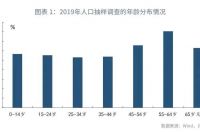金融制裁是国际组织或主权国家根据法律条文对特定的个人、组织、或国家等采取的意在阻断金融交易和资金流动的惩罚性措施。金融制裁是经济制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高烈度”的经济制裁,金融制裁已成为美国、英国、欧盟等实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目标的常用工具,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种重要方式[[1]]。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美国与其他经济体的贸易金融摩擦不断深化,美国政府不仅频繁使用贸易制裁,而且开始调整政策体系,更多地使用了金融制裁、综合施策、极限施压等方式来达成政策目标。
传统上,贸易是经济制裁的首选。通过阻断被制裁对象的贸易往来,使得其经济利益受损并面临多方面压力。但是,诸多研究认为贸易制裁的有效性较低[[2]]。上世纪90年代以来,“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开始出现,由于其具有更好的针对性和弹性,逐步成为重要的经济制裁方式[[3]]。“聪明制裁”的对象是广义上的实体(entities),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国家,还包括社会组织、金融机构、企业、个人甚至军队。当这些实体取代国家成为制裁对象之后,经济制裁“聪明”程度明显提升。比如,美国针对伊朗的制裁不仅采取全面的国家制裁方式,而且采用针对特定对象的聪明制裁方式。近期,美国针对中国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昆仑银行、珠海振戎公司等的制裁也是典型的聪明制裁手段。在金融领域,聪明制裁具有两个基本手段:人员出入禁令和金融交易冻结。前者致力于阻断被制裁实体的人员往来,后者致力于对被制裁实体进行金融封锁,将其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4]]。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制裁实施过程中被制裁实体的支付清算活动被切断,支付清算所支撑的国际贸易亦难以进行,金融制裁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贸易制裁的政策目标。在过去20-30年期间,得益于全球化要素流通和国际金融一体化,金融制裁取得日益显著的成效,并逐步成为重要的经济制裁方式[[5]]。
金融制裁是经济制裁的重要方式,成为美国日益重要的对外交往政策工具。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后,美国对外金融制裁尤其是对伊朗的制裁不断升级,导致国际地缘局势日益复杂化。2019年3月,美国财政部调整金融制裁清单体系,强化特别指定国民和人员封锁清单(即SDN清单)的制裁功能,同时统筹其他类别的制裁清单。在一体化程度不断深化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美国依靠其特有的美元霸权及其金融基础设施,在对外交往中多样、频繁和强硬地使用金融制裁,被制裁实体受到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和复杂。接下来,本文先介绍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框架,梳理其政策目标、体系基础、法律依据和组织框架等内容,接着分析美国金融制裁的主要类别,尤其是清单系列制裁和两级制裁体系,然后致力于从金融机构维度和金融功能视角分别梳理美国金融制裁的主要运作模式以及影响机制,最后以中国为考量对象,提出应对美国潜在金融制裁的政策建议。
制裁是制裁发起国通过某种惩罚性手段造成被制裁国遭受损失或削弱其对抗能力以迫使其改变行为、接受制裁发起国政治意愿或条件的政策性工具 [[6]]。制裁具有多种方式和手段,可以分为外交制裁、经济制裁、军事制裁等。经济制裁是最为重要的一种制裁方式,包括财政、贸易、金融、交通、援助等一系列限制甚至是隔绝措施。
美国经济制裁是一个包括外交、政治、法律、经济、金融等要素相互融合的复杂体系,包括但不限于贸易制裁、金融制裁、技术制裁和援助制裁等。比如,2019年5月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对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制裁是美国商务部主导的贸易制裁。但是,由于贸易和金融交易与资本流动紧密相关,美国或第三方的金融机构亦会审慎评估其为华为提供金融服务的政策和法律风险。金融制裁是经济制裁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烈度的制裁举措。美国大部分经济制裁都涉及金融制裁,同时,美国金融制裁具有较为完善的目标、法律、政策和实施体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实施了针对诸多个人、组织或国家等的金融制裁,主要为了服务美国的三个政策目标。一是履行大国责任。主要是维护世界和平、保护人道主义、打击恐怖主义、反洗钱等。比如美国在联合国框架下对利比亚、伊拉克、塞尔维亚等国家和塔利班组织、索马里海盗等进行了相关的金融制裁。《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系列决议是美国对外实施金融制裁最主要的“法律基础”。二是保障国家安全。“911”事件以来,美国绝大部分金融制裁都是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特别是对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系统的控制强化凸显了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安全意识大大提高了。三是实现特定诉求。主要是实现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比如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与美国对外政策、地缘政治诉求紧密关联。
虽然经济制裁是美国对外关系的一种重要政策工具,但是21世纪以前,美国以贸易制裁为主的经济制裁的有效性相对较低,亟待寻求新的方式来实现制裁的目标。贸易制裁的政策逻辑是通过贸易制裁影响其进出口、国际收支、汇率以及国内产出,使得其内部经济以及内外经济关联等面临崩溃压力。当一个经济体被贸易制裁之后,它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迂回进行制裁规避,使得贸易制裁的效力降低,主要表现为替代效应和迂回效应。比如,一个国家A对另一个国家B进行贸易制裁,A和B的贸易往来中断。但是,由于B与其他多个国家仍保持贸易往来,那么B就可以和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实现替代,甚至通过第三方C迂回继续与A保持贸易往来。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基本政策目标是提高制裁的“聪明程度”或有效性。美国发现针对银行或实体等的针对性打击可以较为有效地提高制裁的政策效果[[7]]。
美国政府的行为基本上是以法律为准绳。金融制裁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等都具有扎实的法律基础,即使是由美国总统发起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制裁也有相关的法律依据。从20世纪初期开始,美国金融制裁行为不断深化,逐步构建了一个以《联合国宪章》为名义上的支撑,以成文法、总统决议及财政部等部门规章为核心支撑,以州政府法规等为补充支撑的金融制裁法律体系。
1. 《联合国宪章》是“最高”法理依据
《联合国宪章》第25条和第41条是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最高”权力来源[[8]]。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全理事会之决议”,这就要求美国应当遵循安理会的决议。第41条赋予安理会实施经济制裁的权力并“促请”会员国执行。虽然安理会决议是“最高”法律,美国在较多情况下是以联合国安理会等决议发起金融制裁。但是,安理会决议是指导性而非强制性的,美国基本上是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对外制裁的“令箭”,同时以国家利益作为是否实施金融制裁的准绳。部分制裁甚至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体现了美国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近期最为典型的事件是,2015年7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伊核问题的决议,2016 年 1 月 26 日包括美国、伊朗等在内的六方达成的《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开始实施,但是2018年5月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继而对伊朗等实施严厉的金融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宪章》及相关决议属于国际法范畴。虽然,国际法在美国国内具有法律效力,但是,美国将国际法分为自动执行和非自动执行两个类别,前者无需国内立法就具有法律效力,后者需要通过匹配国内立法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对外制裁基本上是以国内法为支撑,美国立法机构通常在利益权衡之后将约束力相对较低的国际法转变为约束力相对较高的国内法。特别是当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的决议对美国有利时,美国国内立法的驱动力就更为凸显。
2. 联邦法律是核心法律支撑
美国联邦层级法律是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核心支撑,可以分为三个类别,即基本法律、专项性法律和其他法律规定。基本法律一般是指与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重大法律。专项性法律是美国金融制裁的主要法律支撑,是针对项目类别或国家类别等的专项制裁法律。其他法律规定主要是指其他立法涉及到的金融制裁的相关条款。
一是基本法律。1976年《全国紧急状态法》和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是美国金融制裁的“上位法”。[[9]]前者赋予总统在宣布紧急状态后实施金融制裁的权力。后者将金融制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禁止条款的适用,即在国家安全、对外政策或经济利益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总统有权命令国内金融机构停止与被制裁对象之间的金融交易、款项划拨、货币转移等业务;二是冻结条款的适用,即在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被制裁国家或实体的侵犯时,美国总统有权命令冻结外国公司或者个人在美国的资产,实行贸易禁运,或采取其他适当的应变方式。
二是专项性法律。这主要指美国政府根据不同对象、主体或目标制定的金融制裁专门性法律,可以分为国会立法、总统行政命令和部门规章这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美国国会成文法。比如,1996年12月15日美国国会通过的《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是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基础性法律,美国政府对伊朗的后续制裁均以该法为基础。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其后2012年美国又通过了和《降低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10]这三个成文法是美国政府出台针对伊朗的行政命令和监管条例的基础性法律。第二层次是由总统签发的行政令。1979年卡特总统颁发了第12170号行政令,冻结了伊朗在美国的120亿美元资产并实施经济制裁,其后每年评估一次行政令是否延期,这是美国首次对伊朗进行的制裁。卡特总统后历任美国总统一直将该行政令的有效期每年延长一次。2018年8月7日特朗普总统颁布第13846号行政令恢复对伊朗的制裁,主要是恢复2010年《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11]]第三层次是监管条例。主要是以美国政府部门为主出台的监管条例,此类条例的制定基础是美国国会法律和美国政府行政令。比如,《伊朗金融制裁条例》是由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负责制定、由美国财政部颁发、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规章。《伊朗金融制裁条例》是对《降低伊朗威胁和叙利亚人权法》、《2012年国防授权法》相关条款以及2012年第13622号行政令的细化和执行。[[12]]
三是其他法律中出现的制裁条款。美国诸多法律赋予美国总统实施金融制裁的相关权力,主要包括《与敌对国家贸易法》《爱国者法》以及每年末颁布的《国防授权法》。《与敌对国家贸易法》禁止与敌对国家进行财政、金融和商业贸易,美国财政部据此制定了《外国资产管理条例》,其明确可冻结相关国家资产并禁止金融交易。1950年美国利用《与敌对国家贸易法》对中国实施了制裁。[[13]]2001年因“911”事件而出台的《爱国者法》赋予总统在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况的情况下进行金融制裁的权力。[[14]]
3. 州政府法律及政策是金融制裁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美国是联邦制国家,各州具有重要的立法权,部分州政府亦出台了适用于本州的金融制裁法律或政策。《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十条规定,宪法未授权合众国、同时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将由各州或人民保留。20世纪80年代,美国多达28个州因种族隔离制度对南非进行金融制裁。由于州政府出台的金融制裁法律或政策需要在立法和行政上协调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比如,需要动用美国联邦政府资源才能获得被制裁对象的金融交易信息,可能引发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在制裁政策方面的混乱。关于州政府的金融制裁权力一度出现较大的争议,甚至有观点认为州政府金融制裁权将会弱化联邦政府的外交特权。[[15]]1995年美国最高法院支持州政府拥有对外金融制裁的权力,各州可出台符合联邦政府政策且有助于强化联邦政府政策意图的制裁举措或立法,但各州不得违背联邦政府政策原则及法律规定[[16]]。
州政府对特定对象进行制裁一般是与联邦政府相关部门联合或通过地方司法部门进行。华盛顿特区、纽约等地的联邦法院经常主导或联合其他部门(司法部、财政部、商务部等)对特定金融机构或实体发起调查、制裁与罚款,罚款所得的部分亦可能分给州政府。2010年纽约联邦法院判决美国对冲基金在其起诉阿根廷政府债务违约一案中胜诉,并主导了对阿根廷政府在美资产的冻结。当然,也有部分州政府独自制定法律对特定国家或实体实施制裁。2005年伊利诺斯州政府出台《伊利诺斯州苏丹法》,对苏丹政府、营业地在苏丹或与苏丹从事商业活动的公司进行制裁。[[17]]一定程度上,美国地方政府金融制裁与联邦政府制裁具有一定的等效性。
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是美国金融制裁决策的两个核心主体,而美国总统具有实质性的决定权。美国国会可依据相关法律或者通过制定新法律等方式来要求总统实施金融制裁,而美国总统在实施金融制裁法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同时具有自主颁发制裁命令的行政权。比如,1993-2001年期间美国总统颁布了56个包含金融制裁在内的经济制裁行政命令,而同期美国国会通过了35个类似法案[[18]]。
美国总统具有较大的金融制裁自由裁量权。由于美国《全国紧急状态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与敌对国家贸易法》《爱国者法》以及每年末颁布的《国防授权法》等联邦法律均赋予总统行使金融制裁的权力,总统可根据这些法律实施金融制裁。尤其是2001年“911”事件后颁布的《爱国者法》授予总统“在适当情况下”实施金融制裁等权力,这使得美国总统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2018年6月,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中,特朗普总统一度企图启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宣布全国进入国际经贸紧急状态。
美国财政部是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核心部门,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Assets Control, OFAC)是金融制裁实施的核心执行主体。OFAC依据战时和国家紧急状态时的总统权力范畴、具体立法授予的总统权力以及美国总统的行政法令,对美国管辖下的交易实施控制并冻结外国实体资产。“911”事件之后,美国对把控恐怖主义信息和对涉恐组织及个人的金融制裁均不断强化。2001年美国通过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强化了对涉恐组织金融交易和资金融通等的信息把控,全球银行业的共同基础设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美国政府的个体性政策工具。2004年美国财政部成立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办公室并下设四个部门,其中,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成为了金融制裁实施的核心执行主体。
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制裁清单大部分是美国单方面对部分国家或实体进行制裁,大多属于单边制裁。虽然部分制裁是以安理会决议的形式出现,但是大部分制裁是美国单方面宣布的制裁措施,其清单也主要是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主导制定和公布的。对于部分类别的制裁政策和制裁清单,美国财政部会商谈美国国务院、商务部、司法部等部门,但美国财政部在金融制裁执行上具有较强的主导性。
美国具有实施精准金融制裁的基础设施体系,这是美国金融制裁的载体依托。美国掌握全球最基础的金融基础设施,尤其是以SWIFT和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HIPS)为主体的跨境资金支付清算系统及其相关的基础设施。SWIFT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跨境资金服务的最核心系统,主要提供支付报文服务。一旦掌握SWIFT支付报文信息就基本掌握了全球跨境支付信息。CHIPS是美国所有的全球最大的美元支付系统,承担全球95%以上的银行同业美元支付结算业务和90%以上的外汇交易清算[[19]],是全球美元资金调拨系统。
美国可重点进行以支付清算为载体的隔离型制裁。目前美国财政部金融制裁框架下具有SDN清单和非SDN清单(综合制裁清单)。综合制裁清单中最为重要的一类清单是外国金融机构通汇账户制裁清单(CAPTA),核心目标就是将被制裁实体从美元支付结算体系中“隔离”或“切除”。由于美元支付结算体系是国际贸易和投资的核心体系,一旦进入此类制裁名单,就相当于与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相隔离,无法进行涉及支付清算的绝大部分国际贸易与投资。这种制裁可以针对一家金融机构,也可以针对一个经济体的所有金融机构。由于美元是国际金融市场应用最广泛的货币,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旦被隔离在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之外,一个经济体就基本上失去了与国际金融市场和全球产业链之间进行链接的载体。
(一)三个制裁类别
美国对外制裁的对象可以分为多个类别,覆盖特定国家、个人以及机构等实体。大致而言,美国对外金融制裁可以分为三个类别[[20]]:一是针对特定国家的制裁(Country-Based Sanctions),主要是针对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或所有经济金融活动和交易进行全面的制裁。目前,美国针对伊朗、中非共和国、叙利亚、古巴和朝鲜这五个国家进行全面性经济制裁。针对特定国家的制裁主要是限制这个国家的居民、企业或政府机构在特定经济领域的交易活动,大致覆盖货物、服务、技术和金融交易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时,还包括对特定对象国家及相关实体的资产冻结与没收。对特定国家的制裁是美国政府实施的最高级别的制裁,基本采用敌对式的制裁立场。这种制裁一般由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主导,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在执行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类是清单系列制裁(List-Based Sanctions)。该制裁类别也被称为“聪明制裁”,主要是对更加明确的制裁对象施加特定的制裁。清单系列制裁由于目标更为明确、内容更为清晰,已经成为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主要制裁方式,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清单就是SDN清单。目前,SDN清单主要包括针对恐怖主义、毒品交易、武器扩散(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人权践踏、种族灭绝和国际有组织犯罪等方面行为的六个子清单。清单系列制裁之所以成为美国目前最主要的制裁方式,是因为清单系列制裁能够更好地定位于特定的被制裁实体,避免对一个国家大量的无辜者进行无区分的制裁;同时清单系列制裁有助于美国居民和企业更有效地获得被制裁对象信息并与之隔离关系。基于此,此前针对土耳其和黎巴嫩的国家制裁近期亦转化为清单系列制裁。
第三类是行业性制裁(Sectoral Sanctions)。该制裁方式主要是针对特定行业进行的制裁,主要是限制美国实体与相关国家相关行业进行特定类型的交易。比如,针对乌克兰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冲突的制裁项目是美国实施的第一个行业性制裁,主要是对俄罗斯的金融和能源行业进行制裁。
(二)清单系列制裁
1. 六类清单及其调整
美国政府进行的国家制裁、清单系列制裁、行业性制裁等各自虽有区分,但整体上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比如部分针对国家的制裁与清单系列制裁就较难区分。以清单系列制裁为例进行说明。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以清单区分来设置制裁项目、相应的制裁内容并公布制裁对象清单。其中,主要包括六类金融制裁清单[[21]]。1)特别指定国民和人员的封锁清单,即SDN清单。这是美国金融制裁针对性最强的清单,包括六类子清单,但是,子清单不是绝对独立的,大部分与针对国家制裁以及其他类别的制裁相互关联。2)行业制裁识别清单,主要针对俄罗斯个人、企业或实体的制裁名单。3) 海外逃避制裁者清单,主要是针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制裁,制裁对象是其行为还没有严重到需纳入SDN清单的实体。4)巴勒斯坦立法会非SDN清单,即针对巴勒斯坦立法会及其相关实体的制裁,制裁对象是其行为没有严重到需纳入SDN清单的实体。5)伊朗制裁法非SDN清单,主要是涉及伊朗的金融制裁,制裁对象是其行为没有严重到需纳入SDN清单的实体。6)外国金融机构第561条款清单。
针对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内容具有相似性,主要是为了隔离外国金融机构与外部的联系,使其业务难以开展。比如,第561条款清单是《伊朗金融制裁条例》(Iranian Financial SanctionsRegulations,IFSR)第31章第561条明确的对外国金融机构进行制裁的清单[[22]]。制裁的核心目标是将被制裁机构排除在美元支付结算体系之外。
2019年美国对金融制裁清单体系进行重整,强化了SDN清单的重要性。2019年3月14日第561条款清单变更为外国金融机构代理账户或通汇账户制裁名单(CAPTA)的一部分。CAPTA清单还包括《支持乌克兰自由法》《朝鲜制裁条例》《美对俄制裁法》以及第13846行政令等实施的制裁清单。同日,美国财政部将非SDN制裁的清单统一成“综合制裁清单”(the Consolidated Sanctions List),即非SDN的五类清单变为一类清单。因此,目前美国财政部金融制裁框架下主要有SDN清单和非SDN清单(综合制裁清单),其目标主要是强化SDN清单的重要性,同时提升其他非SDN清单的内部统筹和政策一致性。
在这些制裁清单中,被制裁对象统称为实体(entities),这使得制裁清单的“聪明”程度明显提高。金融制裁以实体(entities)为基本制裁对象,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的优势:一是以实体作为基本支撑对象,实质性地扩大了制裁范围,几乎达到了无所不包的状况。这使得金融制裁的弹性更显著,制裁主体甚至可以利用其国际影响力实现一定程度的域外管辖权。二是以实体替代国家,弱化了制裁的政治色彩,缓解了制裁主体与被制裁对象潜在的冲突,比如部分制裁项目可能涉及到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盟国的实体。三是以具体实体作为制裁对象,可以更直接地打击目标,实现定向打击和精准制裁,比如美国以外国银行作为制裁对象,可迅速地将俄罗斯从美元支付清算体系中予以隔离[[23]]。四是精准制裁可以避免人道主义危机。此前以国家为对象的全面性制裁,在击垮该国家及其政权的同时,可能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让制裁的合法性大打折扣甚至广受诟病。[[24]]
2. SDN清单
SDN清单是美国对外金融制裁中最为核心且最严厉的制裁清单。SDN清单是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公布的针对特别实体实施的“特别指定国民和人员封锁清单”。SDN清单上的实体名单将动态更新并进入美国联邦公报系统,成为美国政府各个部门的“黑名单”。被列入清单的实体的资产和财产权益将被冻结,不能与美国实体进行交易。
截至2019年8月2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列出了55个SDN制裁项目及清单。[[25]]SDN制裁项目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根据特定主题事务项目而设立的子清单,比如,武器扩散、恐怖主义、毒品交易、跨国犯罪、洗钱等。二是针对特定国家进行的制裁项目。比如针对俄罗斯、白俄罗斯、布隆迪、巴尔干半岛、中非共和国、古巴、达尔富尔地区、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尼加拉瓜、索马里、苏丹(南)、乌克兰、委内瑞拉、也门、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均有特定的金融制裁项目,其中针对伊朗、朝鲜、乌克兰等每个国家至少有3个制裁项目。这两类清单相互交织,比如武器扩散清单可能涉及多个国家。2019年7月珠海振戎公司再度被美国财政部和国务院制裁,制裁依据是针对伊朗的EO.13846号行政令,并且珠海振戎公司被列入了SDN清单[[26]]。
3. 561清单
561清单是《伊朗金融制裁条例》(Iranian Financial SanctionsRegulations,IFSR)第31章第561条第201款和第203款明确的与伊朗制裁相关的外国金融机构的制裁清单[[27]]。2019年3月14日561清单变更为外国金融机构通汇账户制裁清单(CAPTA List)的一部分,但是其核心条款保持不变,其依据仍然是第561条第201款和203款。制裁的核心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对特定外国金融机构在美国开立或维持代理行账户(a correspondent account)或通汇账户(a payable-through account)[[28]]实施严格的限制;禁止美国金融机构为特定外国金融机构开立或维持代理账户或通汇账户。美国政府制裁中国的昆仑银行就是依据第561条的规定。2019年3月14日通汇账户制裁清单(CAPTA)取代第561条款清单后,昆仑银行仍在列,相关制裁内容不变。
条例第561条第201款规定,如果美国财政部一旦发现一家外国金融机构蓄意(knowingly)地尝试或已涉足《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规定的6项禁止性活动中的1项或多项重大活动,那么这家外国金融机构将被列入561制裁名单。[[29]]被纳入制裁名单的外国金融机构就无法在美开立或继续保有代理行账户或通汇账户,美国金融机构也被禁止为该金融机构在美开设或保有代理行账户或通汇账户。被制裁实体将被贴上“561制裁清单”(Part 561 List)的标签并在联邦信息公开系统予以公布。
《伊朗金融制裁条例》第561条第203款是基于《2012国防授权法》第1245条规定而设定的制裁内容,即针对伊朗中央银行和特定伊朗金融机构的关联性制裁。[[30]]第203款规定,美国财政部一旦发现某家外国金融机构蓄意地参与与伊朗中央银行或特定伊朗金融机构的任何金融交易或提供相关便利,那么经财政部长同意后将对该金融机构进行制裁。同时,针对私营外国金融机构、政府所有或政府控制金融机构(中央银行除外)、外国中央银行等三类机构进行差异化的制裁,差异化主要体现在针对三类机构的限制性、豁免性和条件性条款的规定有所不同。
《伊朗金融制裁条例》设置特定的豁免机制。在交易内容限制上,对向伊朗出售农产品、食品、药品和医疗服务等活动提供金融交易服务及便利的外国金融机构实行豁免。在豁免期限、条件和内容上,对于政府所有、政府控制金融机构(中央银行除外)而言,在2012年6月28日及其后、2013年2月6日及其后针对它们的豁免条件和内容有所不同。在豁免层级上,美国总统可就显著减少购买伊朗原油和石油产品的部分经济体给予为期180天的显著性减量豁免(significant reduction exception,SRE),在此期限内从事伊朗原油和石油产品相关金融交易和便利提供的外国金融机构不在制裁之内。
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2016年1月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2018年11月5日,特朗普政府再度对伊朗实施全方面的制裁,但给予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意大利、希腊等经济体进口伊朗原油的180天豁免期,前提是这些经济体要采取措施逐步减少并最终停止向伊朗购买石油(即显著性减量豁免)。2019年4月22日美国宣布不再对任何经济体实施伊朗石油进口禁令的豁免,此决定于5月2日起生效。
(三)次级制裁
美国财政部以美国实体和非美国实体将制裁区分为两个层级:一级制裁(Primary Sanctions)和次级制裁(Secondary Sanctions)。一级制裁主要针对美国的个人或实体,包括美国自然人、企业、其他机构以及在美国领土上的他国实体(包括个人、企业和机构等)。次级制裁是指经济制裁发起方在对目标方进行制裁时,针对第三国的公司或个人进行的旨在阻止其与目标方金融往来的制裁活动,凸显了美国制裁的域外管辖特性。
次级制裁是美国过去五年频繁使用的新型制裁方式,主要是针对非美国实体(特别是外国金融机构和企图逃避制裁的实体)。次级制裁在金融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政府可以通过其美元体系的系统影响力让海外第三方金融机构屈服于美国的法律管辖,从而提高美国制裁的效力。次级制裁与针对伊朗的国家制裁、清单制裁类别有交叉,比如SDN清单制裁可包含一级制裁清单,也可以包含次级制裁清单。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次级制裁目前只涉及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但是,美国政府提示其适用范围可能在未来发生改变[[31]]。2016年 1 月 26 日《关于伊朗核计划的全面协议》实施后,大部分针对非美国主体的SDN次级制裁措施暂时中止。但是,特朗普政府上台后不承认该协议。2018年8月6日美国重新实施第一轮SDN次级制裁。2018年11月5日根据该协议暂停的所有次级制裁都重新启动实施。2019年4月8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被美国列为外国恐怖组织,这是外国政府机构首次被认定为恐怖主义实体而被列入美国SDN次级制裁清单。2019年5月,美国政府重启《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实质性地将次级制裁适用于古巴及与之关联的第三方实体。《赫尔姆斯-伯顿法》第三条此前一度被认为是“铁幕重启”[[32]]。
次级制裁的目标就是全面破坏被制裁对象的金融体系功能。美国金融制裁不仅适用于美国人、美国人在境外拥有或控制的实体,还适用于因交易活动与美国存在联结点而受美国法律管辖的非美国实体以及不受美国法律管辖的非美国实体,这将使得被制裁机构陷入全面的被动式隔离。逻辑上,只要与美国实体或涉及美国SDN制裁项目的实体存在联结点(Nexus)就可能成为SDN次级制裁的实体。被实施次级制裁的机构将遭遇被动式隔离,所有现存的联结点以及未来潜在的联结点都将被切断,金融体系支付清算、价值交换、量价传导、资源配置、风险管理以及经济调节等功能基本上会遭受破坏。被制裁金融机构或经济体的未来潜在联结点被切断,被制裁对象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孤岛”。
次级制裁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较大质疑。一是关于联结点的界定。联结点的判断以“最低关联原则”为支撑[[33]],美国财政部根据联结点上相关实体交互的方式、规模、频次、影响以及相关主体的主观蓄意程度来判断其是否与美国实体或被制裁实体存在最低关联性。美国财政部在判断最低关联时在一定程度具有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二是刺激制裁涉及的域外管辖。由于次级制裁可对美国域外实体施加制裁并进行司法管辖,这使得美国对外的次级制裁具有域外管辖权[[34]]。美国在对目标实体发起制裁的同时,可以通过对具有最低关联的第三方实体进行限制,并对违反相关法律的第三方实体施加制裁。域外管辖破坏了其他经济体的司法独立性,同时可能使得次级制裁的范围被刻意放大。
美国财政部主导了美国对外金融制裁的政策和实施,通过国家制裁、清单制裁和行业制裁等类别对外实施不同程度的金融制裁,甚至在对伊朗金融制裁中采用次级制裁。国家制裁、清单制裁和行业制裁等类别的制裁项目经常出现交叉,比如对一个国家的制裁可能有清单制裁也可能有行业制裁。为了进一步了解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此小节根据制裁对象来进行模式区分,梳理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整个国家金融资产等进行制裁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经过数十年的实践和发展,美国金融制裁体系已经比较复杂,因此,类别划分和模式区分不是十分严格。
(一)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制裁
在制裁措施和清单方面,美国根据制裁名目、特定国家和严重程度等构建了以SDN清单和“综合制裁清单”为支撑的制裁措施和清单体系。根据过去较长时间的经验,针对中国相关实体的制裁主要涉及核武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NPWMD)、毒品交易(SDNT)、全球恐怖主义(SDGT)等主题型制裁项目以及针对朝鲜、伊朗、叙利亚、俄罗斯等国别型制裁项目,其中与针对朝鲜、伊朗等国的制裁相关的最多。
综合制裁清单制裁以及SDN清单制裁的对象主要是个人、企业、私人部门金融机构等。这些措施可能会对相关实体本身产生较大的影响,但仍是一种个案式的制裁,不会对一个经济体带来重大的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问题。比如,2014年6月法国巴黎银行为美国实施制裁的国家转移资金而被罚款89.7亿美元[[35]],一度使该银行经营陷入波动。再比如,美国对昆仑银行等的制裁主要是由针对伊朗的金融制裁项目所产生的“连带”制裁,对该银行的经营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个人和私人部门银行的单点式制裁是美国“聪明制裁”的基本支撑。
(二)对国有大型金融机构的制裁
在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框架中,美国可以就一个国家的私人部门银行、国有或国家控制银行以及中央银行这三类机构进行差别化、针对性的制裁。在相关制裁项目下对个人、企业、私人金融机构或小型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之后,如果事态升级,那么美国可能根据相关法律和制裁项目对国有或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比如,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后,伊朗首家政府全资控股银行—伊朗商业银行(Tejarat Bank)受到美国金融制裁且进入SDN名单,这使得该银行无法在伊朗国外进行业务操作。[[36]]在以中国为国别的制裁清单中,伊朗商业银行亦在列,这代表中国金融机构不能与其发生业务关系,否则就将成为美国金融制裁的连带实体。
由于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一般为大型机构或系统重要性机构,针对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会带有一定甚至明显的政治和安全意图,是一种针对性强、打击度高、破坏力大的金融制裁。第一,可能引发系统重要性问题。一般而言,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都是各个经济体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倘若被制裁特别是进入SDN清单,那么对这些银行可能带来重大的打击,甚至可能引发系统重要性问题,以至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第二,可能形成“金融孤岛”。假如一家中国国有银行被制裁,特别是进入SDN清单,绝大部分国际和国内金融机构都不敢与其发生业务往来,被制裁机构将成为“金融孤岛”。第三,可能更广泛地引发经济社会问题。大型国有或国家控制金融机构涉及较大规模的金融消费者,比如规模巨大的储户。一旦该机构被制裁导致业务运行停摆,那么可能引发严重的挤兑事件,甚至演化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
美国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就采用了对大型企业和银行重点打击的方式,给俄罗斯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冲击。2014年3月克里米亚地区脱离乌克兰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发起多轮制裁,其中的金融制裁力度空前。美国率先冻结了7名俄罗斯官员和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17家俄罗斯企业在美境内资产,之后美国和欧盟又联合禁止俄罗斯国有金融机构参与欧洲金融市场交易,要求维萨(Visa)和万事达(MasterCard)停止向俄罗斯被制裁银行提供支付服务,限制俄罗斯能源和科技企业等的融资。其中,2014年7月俄罗斯前两大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被欧盟制裁,随后9月俄罗斯联邦储备银行被美国制裁。金融制裁给俄罗斯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带来了较大冲击,评级机构下调俄罗斯主权信用评级,卢布出现大幅度贬值,2014年当年超过1515亿美元资金流出俄罗斯,俄罗斯与外部的支付清算受到重大破坏。[[37]]
(三)对中央银行的破坏式制裁
中央银行是一个国家主权重要的支撑机构,对中央银行实施制裁可能使得两个经济体进入一种准战争状态。因此,对于中央银行的制裁一般十分慎重。2019年9月20日,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最高级别制裁”,即对伊朗中央银行、伊朗国家发展基金以及一家伊朗企业进行制裁[[38]]。这是美国首次针对一家中央银行进行的全面制裁。伊朗中央银行在美国的资产将被冻结,更严重的是,绝大部分其他中央银行不敢与伊朗中央银行进行交流合作,使得伊朗中央银行的外部连接被破坏,而美国的政策目标就是要对伊朗中央银行的对外合作进行破坏式打击。
中央银行受制裁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问题。首先,中央银行境外资产被冻结将弱化金融稳定的基础。部分央行的境外资产,比如外汇储备投资,是其所在国家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的物质保障。境外资产被冻结以至罚没,将动摇金融稳定的基础。其次,央行被制裁可能引发信用评级下调。央行是一个经济体金融体系的核心,央行受制裁可能会使金融稳定受到较大破坏,评级机构可能下调所在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引发重大信用风险。再次,央行被制裁基本代表所在国丧失国际融资机会。由于资产被冻结、评级下调以及信用风险加剧等原因,该央行、所在国所属商业银行以及其他企业难以在国际金融市场开展融资。最后,央行被制裁可能弱化了央行职能。该央行的货币政策、金融稳定等职能可能受到破坏,比如,市场对其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将持怀疑态度。部分投机资金可能刻意做空所在国的金融资产,冲击其汇率制度等。
(四)对特定国家的紧急资产冻结
根据美国紧急状态的相关法律,美国总统具有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并可实施与紧急状态相关的政策,包括对相关实体进行各种程度的金融制裁。其中最高级别的制裁就是针对特定国家的敌对性经济制裁,包括冻结甚至罚没该国资产,罚没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存款、股票和债权等。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偷袭后,美国于12月26日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总数约1.3亿美元,并将日本所有的金融资产、进出口贸易资金都置于美国政府的管制之下。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因中国参战,1950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财产和资金。2018年6月底,特朗普总统一度企图启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紧急状态条款对中国极限施压。一旦该法的紧急状态条款被开启使用,美国就可以对被制裁国实行贸易禁令、冻结并没收该国持有的美国资产。
美国冻结海外实体资产主要依托贸易隔离、美元结算账户系统冻结特定账户资产和依托第三方机构冻结资产等方式分别或者交织进行。在贸易隔离方面,主要是阻断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和资金往来,这使得被制裁方通过贸易渠道转移资产十分困难。在美元结算账户体系方面,国家和个人都可以设立美元账户,并且账户相互独立。资金结算账户系统分为一级存储和二级存储,一级存储是实体直接在美国金融系统开设的账户,二级存储是实体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在美国的分支机构或在其他国家金融机构开设的美元账户。二级存储账户一般需要通过美国的金融机构通汇账户连接美元结算体系。美国启动对特定实体的资产冻结时,就可以直接冻结一级存储账户上的资产,同时可以通过第三方来冻结二级存储账户上的资产。虽然大部分第三方金融机构不属于美国金融监管或司法管辖的对象,但是,它们与美元支付结算体系相连接且担忧被美国直接制裁,基本上采取与美国政府合作的态度,配合美国实施资产冻结,这使得美国实施的资产冻结可以跨越美国本土。紧急状态下的敌对式资产冻结,对于一个经济体的海外资产将带来致命性损害。但是,美国在考虑该政策选项时,需要考虑被制裁方的实力与反应,特别是从金融摩擦转变为全面对抗甚至战争的可能性。因此,针对一个国家的全面资产冻结应当是一个非常审慎的决策。
中国的政策应对
从美国对外政策的变化趋势来看,特朗普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可能使用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诸多政策工具来实现其政策目标,而不管这种政策是否符合美国长期的行为路径或者其自身设定的规则体系。近期,美国政府单边主义有所强化,对金融制裁的运用更加频繁,对中国的各类制裁也在强化。在一个不平等、不平衡和不稳定的美元霸权体系中,中国应该运筹帷幄、多措并举、前瞻布局,从而有效应对包括金融制裁在内的美国多样化制裁的潜在风险。
(一)积极深化多边合作,维系国际秩序稳定性
美国近期发起的诸多贸易摩擦、金融制裁等体现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多边化和合作化的趋势背道而驰,美国正试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应该充分利用国际金融组织的相对中立性来评估美国政府在金融货币领域的政策公信力。中国应当积极主动地与联合国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组织进行合作,强化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政策和币值决定市场化改革的认识,强化人民币汇率与经济基本面相符的基本判断,强化国际社会对美联储独立性和公信力的讨论,同时致力于维系现有国际金融体系规则与秩序的相对稳定性,并寻求多边合作来改善现有秩序。最后,中国应当与美方保持沟通和交流,求同存异,共同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建议常态化跟踪美国金融制裁的政策演进。过去几年,美国金融制裁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单方面破坏《伊朗核协议》后,美国对伊朗的金融制裁不断升级,伊朗国民卫队和伊朗中央银行先后成为首个被制裁的政府机构和中央银行。美国的制裁政策、工具和力度都在不断变化。2019年3月美国财政部调整了制裁的清单体系,相关的政策框架、制裁举措和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发生新的变化。
目前中国有多个实体被美国制裁。虽然这对国家的整体冲击还不大,但是,出于未来风险防范的要求,相关部门、机构应该针对美国金融制裁清单进行全面梳理,明晰与美国金融制裁对象的关联程度、制裁内容、潜在影响以及应对之策。同时,针对受到制裁影响的不同类型的人员、机构及企业等采取差异化政策,尽力支持与国家经济发展、金融稳定和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实体,并且尽量避免中国实体被列入美国金融制裁清单。
(四)加速完善人民币支付清算系统
支付清算下的隔离式制裁以及对个人和金融机构的单点式制裁是美国惯用、常用的金融制裁手段。受到此类制裁时,相关支付清算系统陷入困境,一些经贸活动被迫中止。因此,应该加快推进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尤其是将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的能源、粮食、矿产、基础原材料等的经贸交易、支付、清算纳入其中,形成一个完善的支付清算系统。2019年1月31日英国、法国和德国宣布建立“支持贸易往来工具”(INSTEX),这是一个以迂回方式来与伊朗或其他经济体进行交易的系统,也是一个备份系统。此系统的开启主要是对美国将SWIFT等全球金融公共基础设施予以私用的一种应对。INSTEX的系统总部设置于法国并于2019年6月正式开启,但由于受制于各种因素,该系统至2019年9月底还没有实质性地开展业务。中国应当借鉴欧洲经验,考虑构建一个“备份”支付清算体系。
(五)加快“阻断法”立法,对冲域外管辖权
“阻断法”是某一司法管辖区用于阻止外部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在其境内生效的法律,专门用于应对域外管辖。美国的域外管辖在“911”事件后取得重大突破,未来可能进一步强化。欧盟的应对之策是制定“阻断法”。制定“阻断法”就是以法律形式明确不承认美国法律对于本国企业的适用性,通过立法的方式打破美国单边制裁的有效性,维护本国企业和个人在海内外的合法经营权益。“阻断法”可能无法完全应对域外管辖的风险,但是,可以给相关企业、机构提供一种缓冲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美国金融制裁不可预见性和随意选择性的损害程度。
(六)考虑构建中国版金融制裁政策体系
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不断深化,外国金融机构和大型跨国公司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不断深化。因此,特定的金融制裁政策可作为“针锋相对”、“以牙还牙”的政策储备。可借鉴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别是设置制裁实体清单及其标准。
(七)深化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
在美元霸权体系下,金融制裁具有不对称效应。即使被制裁方作出完备的政策应对,美国仍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对于与中国直接相关的金融制裁,尤其是针对国有金融机构、中央银行以及全面的“敌对式”制裁,美国会十分谨慎,因为这不仅可能对中国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冲击,也可能给美国自身金融体系以及全球金融体系造成巨大的破坏。当然,对于这种金融安全领域的小概率但具有系统破坏性的外部冲击,中国应当做好相应的政策应对准备。
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做好“家庭作业”,深化经济金融体制和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完善利率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与国债收益率曲线建设,提升内部金融体系的韧性和弹性。中国应当完善会计和审计制度,防止美国以此为借口制裁中国的相关实体;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更多地引入美国、英国、欧盟等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形成微观层面的经济金融利益共同体。同时,以内外两个市场统筹为支撑,对金融市场开放进行再评估,在金融安全和稳定的前提下,加快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提升内外市场一体化水平。未来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融是大趋势,中国应该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构建中国与世界经济互动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参考文献:
[[1]]Kaempfer,William H. and Anton D.Lowenberg,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anctions: APublic Choice Approac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78(4):786-793, 1988.
[[2]] Dashti-Gibson,Jaleh,Patricia Davis and Benjamin Radcliff, “On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Success of EconomicSanc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41(2):608-618, 1997;Lektzian, D. and M. Souva,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Sanctions Onset and Success”, Journal ofConflict Resolution, 51(6): 848-871, 2007.
[[3]]聪明制裁主要是指实施制裁的主体通过对特定实体(Targeted entities)进行针对性制裁以取代此前针对整个国家的制裁,并取得了更好的制裁结果。相对于此前相对广泛的制裁,这种针对特定目标的制裁显得更加“聪明”。详见,Tostensen,A. andB. Bull, “Are Smart Sanctions Feasible?”, World Politics, 54(3):373-403, 2002; Friedman, U.,“Smart Sanctions”, Foreign Policy,193:28-29, 2012.
[[4]]Eckert, Sue E., “The Useof Financial Measures to Promote Security”, Journal ofInternational Affairs,62(1):103-111, 2008.
[[5]]Servettaz, E.,“ASanctions Primer: What Happens to the Targeted?”, World Affairs,177(2): 82-89, 2014;
Barry, C. M., and K. B., Kleinberg, “Profiting fromSanc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69(4): 881-912, 2015.
[[6]]Hufbauer,G. C.,J. Schot and K.Elliott, Economic Sanction Reconsidered,2nd Edi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0; Hufbauer,G. C.,J. Schot, K.Elliott and B. Oegg, Economic SanctionReconsidered, 3rd Edition,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Economics, 2008.
[[7]]Rachel, L., “Bank Shots: How the Financial System can Isolate Regimes”, Foreign Affairs, 188(2):101-110, 2009.
[[8]] 这里用“最高”一则想说明联合国宪章和安理会等机构的决议是美国对外制裁的重要依据,二则通过加引号想说明美国经常打着联合国的幌子来实现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9]]全国紧急状态法(The NationalEmergencies Act of 1976),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The International EmergencyEconomic Powers Act/IEEPA)。详见https://www.congress.gov/bill[2019-12-20].
[[10]]详见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Pages/iran.aspx.[2019-10-15].
[[11]] 2015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形成伊核协议,《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规定的相关制裁均暂停。
[[12]]伊朗-利比亚制裁法即The Iran-Libya Sanctions Act of 1996,《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即The Comprehensive Iran Sanctions, Accountability, andDivestment Act of 2010,《减少伊朗核威胁和保障叙利亚人权法》即Iran Threat Reduction and Syria Human Rights Act of2012, 《伊朗金融制裁条例》即The Iranian Financial Sanctions Regulations。本段所涉及的各项法律均在美国财政部对伊朗制裁介绍中列示。详见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Programs/Pages/iran.aspx.[2019-10-15].
[[13]]刘建伟:“美国金融制裁运作机制及其启示”,《国际展望》,2015年第2期,第111~126页。
[[14]] 《与敌对国家贸易法》即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of 1917,《爱国者法》即USA PATRIOTAct of 2001,详见https://www.congress.gov/bill.[2019-12-17].
[[15]] 杜涛:“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对外经济制裁及其对美国联邦宪法和国际法的挑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0年第1期,第65~74页。
[[16]] 杜涛:“美国州和地方政府对外经济制裁及其对美国联邦宪法和国际法的挑战”,《武大国际法评论》,2010年第1期,第65~74页。
[[17]] 郑联盛、张晶:“阿根廷债务技术性违约的根源与影响”,《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40~47页。
[[18]]徐以升、马鑫:《金融制裁:美国新兴不对称权力》,中国经济出版社,第2~3页,2015年。
[[19]]许文鸿:“美欧对俄金融制裁的影响及若干思考”,《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5期,第37~43页。
[[20]] OFAC, “OFAC Economic Sanctions Programs”, https://ofaclawyer.net/economic-sanctions-programs/[2019-10-13].在网站上,美国财政部将制裁类别分为四类,还有一类是次级制裁(SecondarySanctions)。但是,次级制裁目前只针对伊朗,同时与国家制裁、清单制裁有交集。作者在此将制裁类别分为三类。在后面域外管辖讨论中再分析次级制裁。
[[21]] OFAC, “OFAC Economic Sanctions Programs”, Oct.10, 2019, https://ofaclawyer.net/economic-sanctions-programs/[2019-12-08].
[[22]]OFAC, “31 CRF Part 561[N]. FederalRegister”,Nov 8, 2012, https://www.treasury.gov/about/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fices/Pages/Office-of-Foreign-Assets-Control.aspx[2019-10-08].
[[23]]许文鸿:“美欧对俄金融制裁的影响及若干思考”,《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5期,第37~43页。
[[24]]李婷婷:“‘聪明制裁’之后联合国对朝制裁的经济效果评估”,《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2期,第42~49页。
[[25]]OFAC, “The SDN List”,https://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2019-09-18]. 该清单动态更新。
[[26]] 美国财政部:“美国对从伊朗购买石油的中国珠海振戎有限公司实施制裁”,2019年7月22日,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the-united-states-to-impose-sanctions-on-chinese-firm-zhuhai-zhenrong-company-limited-for-purchasing-oil-from-iran/[2019-11-03].
[[27]]OFAC, “31 CFR Part 561.203., FederalRegister,March 15,178(51)”,https://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2019-9-26].
[[28]]通汇账户是美国金融机构为外国金融机构提供开立支票特权的存款账户。
[[29]] 201条款的依据是《全面制裁伊朗、问责和撤资法》的金融机构制裁规定(CISADA-based sanctionson certain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0]] 203条款的依据是《2012国防安全授权法(NDAA)》第1245条制裁规定(NDAA-basedsanctions on certain 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31]] OFAC.“OFAC Economic Sanctions Programs”, https://ofaclawyer.net/economic-sanctions-programs/[2019-10-19].
[[32]] Council on HemisphericAffairs, “Helms-Burton Act: Resurrecting the Iron Curtain”, June 10,2011,http://www.coha.org/helms-burton-act-resurrecting-the-iron-curtain/[2019-11-03].
[[33]]最低关联原则最早来自于国际鞋业公司的判例。1945年经营地在密苏里州的国际鞋业公司向美国最高法院起诉华盛顿州,认为华盛顿州政府收缴其在该州推销员的失业救济金违法。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国际鞋业公司推销员的缴纳义务直接产生于公司在华盛顿州的活动,这种活动具有与华盛顿州的最低关联性。法院最后判定国际鞋业公司败诉,并认定华盛顿州法院对该案件具有管辖权。这就是最低关联原则(Certain Contact Principle)的缘起判例。
[[34]]李庆明: “论美国域外管辖:概念、实践及中国因应”,《国际法研究》,2019年第3期,第3~23页。
[[35]] 新华网:“触犯美国对外制裁法规,巴黎银行认缴史上最贵罚款”,2014年7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4-07/03/c_126703546.htm[2019-10-23].
[[36]] 美国财政部动态更新SDN清单, 2019年8月3日更新的清单中仍有伊朗商业银行(Tejarat Bank)。https://sanctionssearch.ofac.treas.gov/[2019-09-18]。
[[37]]许文鸿:“美欧对俄金融制裁的影响及若干思考”,《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5期,第37~43页。
[[38]] “美国宣布对伊朗央行等实体实施制裁”,2019年9月21日,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921/c1002-31365597.html[2019-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