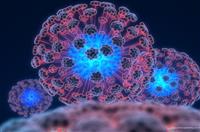凌晨3点,广西柳州郊区的一座村落里,万籁俱寂。
村里人早都睡熟了,只有吴伯家还亮着灯。
“差不多了”,吴伯捞出越来越厚的泡沫,把大部分柴火抽出,埋进灶膛底层的木灰里。火小了,豆浆凉下来,吴伯起身扯起“豆皮”来。一张张“豆皮”被扯起挂上竹竿,拿去屋外场上晾了。
从清晨的太阳开始晒,一直晒到日落,豆皮就成腐竹了。
做腐竹辛苦,麻烦。
做之前,要算好天气,不是大太阳天不行;
要晒一整天的太阳,晾晚了错过日出不行;
从泡豆到出锅起码要十二个小时,不通宵不行。
也有不辛苦、不麻烦的做法。
用巴西/美国/东北的黄豆,产量大,便宜好买;豆皮扯出来后,挂在一张大铁皮上,铁皮底下点废纸、塑料、破布烧。很快就干,随时能做,不用等太阳;用腐竹精,“豆皮”产出率高,颜色晶莹光亮;加防腐剂,搁一年都不坏。
东北黄豆甜,影响腐竹口味,巴西黄豆、美国黄豆转基因不说,味道更不对。非得是柳州本地的小黄豆才能做出纯正的口味。而这种小黄豆产量少,如今种的人少,贵,还难买到。
为了让这样的传统手工艺可以继续传承,广西爱农会一方面组织其小农网络里的农户来协助种本土小黄豆,一方面寻找年轻人来学习传统腐竹制作手工艺。如今受外来的廉价转基因大豆的冲击,小黄豆价格相对较高,爱农会更是提供补贴给吴伯,以便其继续使用本地小黄豆来做腐竹。
2008年春天,广州一家注重环保、支持CSA(社区支持农业)理念的NGO组织沃土工坊,从柳州有同样理念的NGO组织爱农会那儿得知吴伯的腐竹,特意上门拜访,拿了一些回来卖。
卖出几扎后,雨季还没过,客人的投诉就来了。“买了没多久,打开腐竹袋子一股霉味,还卖得那么贵!”面对这种投诉,沃土工坊的创始人阿标并不意外。
“抱歉,忘记告诉你我们的腐竹买回家要立刻放冰箱了。传统工艺做的腐竹不放防腐剂,的确容易坏,最近雨季,霉得更快。你拿回来,我给你换。”
不单是腐竹,沃土工坊从爱农会的合作农民那里拿回来的有机大米、面粉、蔬菜,都没有市面上的耐放、品相好。为此,阿标和他的同事不得不反复提醒客人,以免矛盾。
在西方和日本已经发起并流行了近半个世纪的社区支持农业(CSA),在中国,才刚起步。
这种模式于上世纪70年代起源于瑞士,并在日本得到最初的发展。当时的消费者为了寻找安全的食物,与那些希望建立稳定客源的农民携手合作,建立经济合作关系。
如今,CSA的理念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传播,它也从最初的共同购买、合作经济延伸出更多的内涵。
近几年,CSA的概念被引进到国内,一些热心从事CSA事业的人建立起有机农场,比如上海的青蓝耕读合作社和北京的小毛驴市民农园;还有一些是有志于促进发展有机生活理念的NGO组织,比如广西柳州的爱农会和广州的沃土工坊。
不打药,雇农民捉虫
地里的大白菜生虫了,孙杨欢雇请的农户跑来问她,要不要打药。
不打,我们不打药,不用化肥。
农户站着不走。不打药,菜都被虫吃了,烂了,产量少,还不好看,卖不上钱。人家都打。
孙杨欢第二天雇了一位农户,花了2天时间捉虫。
在英国读书时,孙杨欢每两周随她的英国房东去郊区的有机农场做一天义工。不用化肥农药种植、城里人参与耕种的农业生产模式,让孙杨欢觉得健康、环保、新鲜。
回国后,看着报纸网络上屡见不鲜的食品安全危机报道,孙杨欢觉得CSA在国内会有受众。做了5年外贸生意,攒了些积蓄后,孙杨欢在上海崇明岛上租了130亩地,投了一百来万,建立了做有机蔬菜种植和乡村创意园的上海青蓝耕读合作社。
后来,收菜的时候,还是有农户接受不了:“你这菜多难看,都是虫眼,肯定卖不掉。”
孙杨欢给所雇的农民按日付工资。农民并不承担产量、销量的风险和压力,即便如此,如何说服农民摆脱化肥和农药,还是让孙杨欢费尽心思,磨尽嘴皮。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上面去说服农民,农民还是更愿意听上面的话。但是目前,上面对我们这种做法,热情有余、实惠不足,持观望态度。”
上世纪70年代,农药化肥以有票才能购买的“稀缺品”姿态进入国内农民的生活。在田间来回走几趟,用喷雾器喷几下,代替了一连几天弯腰低头的双手捉虫;翻土撒药代替了担粪沤料肥田。农民尝到了工作量减轻、产量增加的甜头。
此后,农药化肥的一再普及,农产品价格的低廉,让从繁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农民已经不愿、不敢离开农药化肥。
“在惯性农业已经进行了二三十年的今天,很多农户已经没有信心回头了。”爱农会的志愿者刘胡佳感叹道。
农民对产量和销售的顾虑,在情理之中。消除这种顾虑,预付款显然最直接。
每年年初,爱农会跟部分合作的农民一起算,这块地如果用常规的耕种方式,大概能产出多少,挣多少钱,除去农药化肥能净收多少。双方达成共识了,爱农会把这笔钱预付给农民。要求是,不用化肥农药。
预付款,也正是国际上CSA组织最常用的一种方式。按惯例,每年年初,CSA组织的会员预付未来一年的农产品费用,以降低农民的生产风险,提高有机耕种蓄养的热情。北京的CSA小毛驴农场和青蓝耕读合作社也是使用该种方式:年初预付2000到4000元不等,每周可收到来自农场的农产品一次,每年20至40次配送,品种是农场有机种植的时令农作物。
而爱农会还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用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合作农户的农产品。
爱农会与合作者沃土工坊也会帮农户寻找优质种子、幼苗、家禽家畜的幼崽,尤其是本地的传统品种。
比如饲养土鸡,爱农会找到当地优良的传统土鸡种后,免费提供给适合养鸡的农户,待鸡长大后、产蛋时,再去收购。这样即使没有用预付款方式合作的农户,也少了些风险。
寻找“奇异”农民
能解决问题的不只是钱。还有对顺应自然这种普世价值观的认同。
广西漓江边上有片金桔林。
林主伍伯被桂林泥巴坊的工作人员称为“有思想的奇异农民”:一个与老婆抗争始终坚持不用农药化肥而用木屑花生麸、堆肥做肥料的传统的农民;一个不用除草剂而在地里种草的农民;一个自制植物生长剂使老枝都能结果的农民;一个一年花200多块订阅农业杂志、唯一一个在农业培训时带上笔和笔记本做笔记的农民。
伍伯心疼他被化肥农药糟蹋的土地,也知道现代农业对人类的影响,“其实我们农民都知道农药化肥跟现在越来越多的疑难杂症有很密切的关系,可大家就是不敢尝试不用。我相信自然农业技术,不除草、不杀虫不用化肥,水果一样有好收成,卖得起价钱,吃得放心。”
有一次泥巴坊的工作人员到伍伯家,伍伯拿出他自己配制的营养液“伊尔目”请大家品尝。
营养液的味道类似果醋。伍伯自喜地跟大家介绍,这种营养液富含多种有益微生物,可以激活体内的消化系统,调理肠胃、排毒养身。每天喝一小杯,胃口就会大增。
转身,大家看到伍伯家的柚子,问有没有“洗过澡”(用化学保鲜药水浸泡柚子,保持柚子的新鲜光滑,几乎每一位农民都会用),伍伯老实说“洗”过了。
一片失望。不料,伍伯补充说,我是用你们刚才喝的这个营养液清洗的。这种营养液富含多种有益微生物,可以消除有害微生物的滋生,所以能保鲜。
像吴伯、伍伯这样坚持“道法自然”的耕种蓄养方式的农户,在爱农会、泥巴坊和沃土工坊日复一日的寻访中,不断被发现,被介绍给他们嘴里的“城里人”。
让买菜的和种菜的面对面
入冬后,孙杨欢陆续收到一些投诉。菜的品种少,送来的都是便宜菜,菜的品相也不好。
她一一跟对方解释,我们不用大棚,不用化肥激素,只能种当季的菜,菜的品相也不会很漂亮。当季的菜在市场上自然便宜。天气冷,菜的品种也跟着少。
理解的总是大多数。不理解的,孙杨欢会劝他们选择超市里大型有机农场生产的品相更好、品种更丰富的蔬菜。她称这为“筛选顾客”。
选择,基于信任。
而在当下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重重的中国内地,信任是需要重建之后才有的。
与国际上的CSA组织相同,国内几乎所有的CSA都会努力让食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直面交流、相识,最好是相熟。
每周,小毛驴农场和青蓝合作社都会有自己的开放日。公众、组织的份额成员都可以前来参观。
几年里,接待了一批批参观者的小毛驴核心人物石嫣熟悉外面人来到这块土地上的反应,“成员们来了很容易感受到农场的不同。用了农药的农田一走近,就能闻到刺鼻的气味,但是这里没有。”
“你绝对不可能弄虚作假。成员们、公众、媒体都可以来到我们农场上,跟田间地头的农民聊天。不可能要求每一位农户配合着撒谎。开放日里,很多份额成员会带着家人过来参观农场,看农民劳作,这都能增加他们对我们的信任感。”
孙杨欢总是记得开放日里的一个家庭,孩子伸出小手指向一棵蔬菜,昂起头向父母问没完没了的问题。细心的爸爸用力拔出萝卜又不动声色地轻轻插回去,转身让年幼的女儿感受亲手把萝卜从地里拔出来的喜悦。
爱农会的下乡活动,因合作农户的多样而主题丰富。“赶鸭子上架”、“看禾苗返青”、“捡土鸡蛋”,一天的体验活动内容常有更新。
农户们也被邀请到爱农会自己的餐馆里,来自马山的农妇拿着榔,围着石槽跳起了古老的打榔舞;横县的农妇开口便唱起了采茶山歌;武鸣的大叔用壮语唱起对歌。
随身带来的自家收成上,都挂一个小竹牌,正面写着重量,反面则写着是农户名字、所在地、生产时间,有的甚至贴着动植物生长时田间的美景照片。
不认证,靠彼此信任
有趣的是,北京、上海、广西、广东、四川的几家CSA组织,在面对建立有机农产品购买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感时,态度高度一致:
不认证,依靠和消费者的直接联系来维系信任。
四川郫县安德镇的安龙村,在村里高家的带领下,有9个农户用CSA模式耕种。高家的高清蓉去年5月在北京参加消费者合作社大会上,自述安龙村农民的CSA经验:
不做认证,一方面因为认证很花钱,另一方面,我们那边有个农村是有认证的,是政府主导的,我们和消费者去参观,结果发现1000多亩的地连堆肥都没有,大家就明白了,其实他们只是进行含量上的监测,仍然没有彻底有机化。
我们的消费者也没有要求我们做认证,完全靠彼此信任。周六、周日都是用来和消费者交流的时间,周一到周五是农耕时间。配送时,我们用袋子装好,谁家的、谁种的都写好。他们也不会太讲究分量什么的,从来不问。也不是没有麻烦,——若是与数家农户合作的CSA组织,如何保证分散的合作农户不用化肥、农药、饲料?
高清蓉就遇到过这个问题,“我们靠自我监督,但这也不容易。各家农户自律程度不一样,确实也有不太上心的,我哥哥亲眼看到过有人上农药,就停了他一段时间。”
爱农会也用类似的办法,请农民间相互监督,几次违规后,就取消资格。被取消资格的农户眼看着爱农会用远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别人家东西,心里也后悔。村里其他人该怎么做,心里也有了数。
“我们在寻找农户时,会从几个方面看他是否适合:为人诚信;坚持CSA(社区支持农业)理念中互信互助的原则;农业投机分子不予考虑;有适合养殖的场地,并有种养结合传统。”刘胡佳解释,“合作久了,我们跟农户,双方都不要求书面的协议,全凭长时间的交往建立起来的信任来做。”
更像乡土社会里人与人的交往方式。
无论是生产者,还是购买者,对于CSA这种模式,都正在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