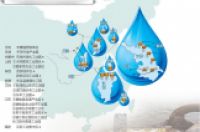
环评成了“必须且一定能通过,建设到什么程度就验收到什么程度。”
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相当部分是“过水厂”,“一般都属于地方政府,很敏感,我们无法介入。”
有些企业甚至扬言要把一年的罚款都提前交了,“这相当于罚款换排污权,违法变合法”。
(明镜/图)
污染“七宗罪”
原本被誉为各地经济发展引擎的工业园区,部分成了藏污纳垢的代名词。
丑闻不断,位于大连石化产业园区的PX项目,位于云南陆良县西桥工业园区的铬渣污染……提起这些,马勇感慨万千,他手里握着一份《关于我国部分工业园区环境问题的调查报告(下称工业园区报告)》,集纳了工业园区重大污染问题,为控污治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他是中华环保联合会环境法律中心督察诉讼部部长,常年与“环境访民”打交道。中华环保联合会是环保部主管的非政府组织,活跃于民间。
尽管工业园区报告出自这个带有官方色彩的组织,但是出台近一年,反馈寥寥,各地污染事故频发。
这份报告来自马勇所在的法律中心接手的污染案件。他发觉,越来越多的案子直指工业园区,集中生产变成了集中排污。污染事件引发了众多群体性事件:江苏响水县数万人因污染谣言雪夜大逃亡;福建江阴工业集中区毒气外泄导致强烈冲突,几十名污染受害者被捕,等等。
中华环保联合会觉得有必要摸清中国工业园区污染的真实状况,在2010年3月到10月间,马勇和他的同事调查了八个省的18个工业园区。
调查的结果仅水污染一项就令人惊心:调查样本中有2个国家级、7个省级工业园区,都或紧邻重点流域和饮用水源,或居于人口集中区,100%有水污染问题,78%的涉及大气污染,17%存在固体废弃物污染。13个工业园区涉嫌污水直排江湖。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省级以上开发区逾2000家,其中各类国家级开发区超过200家。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洁生产与循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乔琦介绍,加上县、市一级的各类工业园区、集中区和集聚区,这一数字接近7000家。
约7000家工业园区的污染现状,从工业园区报告中可管窥一斑。
报告列举了污染七宗罪:环境风险隐患突出,环评审批和“三同时”执行成为“表面工程”,工业园区污染治理设施形同虚设,环境纠纷隐患突出,污染转移现象严重,环境执法监管不力,土地资源浪费严重。
这七宗罪几乎成为工业园区通病。
“县市级的工业园区问题多多,省级以上的管理相对规范,但也少不了问题。”马勇清楚记得,江西省乐平工业园区是江西30家重点工业园区之一,曾被评为省级先进工业园区和经济指标综合考评先进园区,建园长达七年之久,配套污水处理厂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调查期间还未投入正常使用。园内污水直排入鄱阳湖。
“可以想见,占七成的县市工业园,情况不会更好。”作为中国生态工业园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乔琦曾去过不少地方调研,每每听到一些园区管委会领导大谈环保、无污染,她都“很反感,感觉是被欺骗了”。
手握第一手资料,中华环保联合会力求有所作为。然而,在近一年时间里,马勇感到很无力,“我们也有一些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领导,批示了都没用。”
污水处理厂成“过水厂”
在调研的18家工业园区中,具备配套污染治理设施的共有13家,占70%以上。但在这13家中,污染治理设施或闲置不用或间歇运行,完全实现不了污染物达标排放要求。污染治理设施俨然成为了应付检查的表面工程。
中华环保联合会的调查发现,工业园区环评审批中违法、越权现象比比皆是:本该由国家或省市审批的项目,被分解为小项目由县审批;本该编制环评报告书的项目却被简化为报告表。甚至许多园区企业把环评审批文件当做“护身符”,敷衍执法检查,而环评审批中规定的治污设施却迟迟不能建设。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县金山工业园区便是典型案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园区一企业环境影响报告表写明项目不产生废水,而2010年6月22日,赣榆县环保局却以“生产废水超标排放”对该企业进行行政处罚。
环评成了“必须且一定能通过”。按规定,工业园区污染防治措施要达到75%负荷才能验收,实际上,“是建设到什么程度就验收到什么程度。”马勇说。
福建省福清市江阴工业集中区的环保“三同时”验收早早通过,然而,时至2010年该园区运营八年后,污水处理厂还未投入正常运营,污水直排入邻近海滩。工业园区索性与村委会达成协议,将滩涂彻底变成排污场。
污染企业还有一招,以试生产做挡箭牌。按规定,企业在最多一年的试生产阶段,防污措施可不验收。一些企业生产了七八年,却一直处在试生产阶段。马勇揶揄这样的企业“试生产的设备都老化了”。
北京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叶正芳直言目前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厂,相当部分是“过水厂”。工业园区产品种类多,排放污水不均衡,水质、水量变化很大,而污水处理工艺大多采用活性污泥法加上混凝沉淀或过滤,“这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可能具备处理复杂化工污水的能力”。
环境咨询公司ERM中国区总裁谢辉发现,工业园区挂羊头卖狗肉是常见现象,“说是电子工业园,其实化工、重金属都进来”。据他了解,不少工业园区在工业污水中混入生活污水,“处理谈不上,稀释后至少浓度降低了”。
“过水厂”排放却能达标,江苏省连云港市响水县一位环保执法人士道出其中奥秘:污水排放指标有几十项,但真正被严格执行的,不过COD、氨氮等三四项,由于只能做常规处理,“最后可能也就COD能达标”。
“现阶段国家的环保要求就是这样。”上述人士表示,再加上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企业交排污罚款远比处理废物合算。马勇了解到,不少企业在做年度预算时,甚至早已把排污罚款纳入其中,有些甚至扬言要把一年的罚款都提前交了,“这相当于罚款换排污权,违法变合法”。
2006年7月16日,湖北宜昌市一个人工涵洞不停地“吐”着墨汁般的化工污水直扑长江。 (刘君凤/CFP/图)
“废物最小化俱乐部”
谢辉和马勇有个共识:行政的力量掣肘过于强大。
马勇感慨环保执法不力之时,常劝污染受害者们尽量不要起诉。“案子往往三五年也不能了结,即便结案败诉的可能性也很大”。更要命的是,一旦司法介入,行政力量则撒手不管,受害者可能两头无靠,案件多以调解告终,“这是在行政力量之外,为环境维权寻找缝隙”。
作为外资背景的环境咨询公司,谢晖和ERM的客户大多来自世界500强,却鲜有地方政府和工业园区。“工业园区的污水处理站一般都属于地方政府,很敏感,我们无法介入。”谢辉说。
环保部环评司巡视员牟广丰更是坦承,现在环境问题不断陷入应急状态,其根源在于体制,当一套体制的每个环节都有问题时,如何指望最末端的污水处理厂和除尘装备力挽狂澜?
不久前,乔琦回访天津泰达工业园,一个细节吸引了她。泰达是中国最早获批的三家生态工业园之一,这个园区成立了“废物最小化俱乐部”,试着把A公司的废物变成B公司的原料。
一开始,企业家们兴致不高。但管委会主任很积极,常往俱乐部跑。几番下来,企业老板们也发现了不少商机,先是建立了园区内部的废物交换网站,随后又把废物卖到了国外。
丹麦卡伦堡是这一模式的成功代表,早期是由当地几家发电厂、炼油厂为了应对淡水短缺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成本危机,自发形成废水、废气交换共生体。这种交换在1989年被学术界发现并命名。
这是生态工业园的工作模式。截至目前,中国获批的生态工业园区总计54个,不足全部工业园区的1%。被称为“第三代”、代表工业园区理想模式的生态工业园,其准入的基本条件中,有“过去三年内没有发生过重大污染事故和环境破坏事件”、“达标排放”等。
叶正芳有些不解,“这不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基本要求吗?”
乔琦刚刚参加完国家“典型工业园区环境风险评估与环境监管技术研究”项目评审,可能将开始改变中国工业园环境风险估计严重不足、缺本底调查和基本数据的残酷现实。
“最好的和最坏的都在中国。”乔琦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