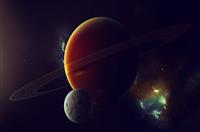既然是回应与对话,那么对于欧先生,我就用第二人称写。
整场讨论,我始终明确了一点,这次批评,对事,不对人。但看到您的回应,认为我一条和朋友互动的无关微博是为了给碧山“泼粪”,认为我批评英文PPT“怕是触动了哈佛女博士的特权了”,乃至您认为我“心里区隔过大”——类似的诛心之论,不仅莫须有,并且仍然是对人,不对事的。
“星星” vs. “路灯”,是在说审美区隔。并且,从微博到豆瓣,从始至终,我一直说得很清楚,要看星星的是“外来知识分子”,并没有特指你们。不过,我也给出了媒体对您的采访,认为村民想要路灯,是“面子工程”,这话,却的确是您说出来的——“面子工程”,在我国当下语境里,有什么样的隐含语义?将村民对路灯的整场渴求,说成是对面子工程的追求,是否是想当然的?
Moleskine说的是身份标识(status symbol),status symbol和通俗语义里的“炫富,完全是两个概念。对身份标识的拥有与展示,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边界的方式。当然,这或许是一种学术话语与理解,造成误解,十分正常。
碧山书局和南京的先锋书店十分相似——碧山书局里,有一整面书柜的钱穆先生全集、有108元的牛皮笔记本、雨棚上写的是法文的“先锋书店”(librairie avant-garde)等等,说它的审美趣味是精英的,不知您异见在哪?实话说,我在碧山两天,没有看到一个村里人来祠堂改建的书局---但我在豆瓣和友邻交流时,也说得很清楚,两天的观察,样本量太小,所以我也从来没拿那说事儿。
说您用英文PPT(并且PPT里全是大词,那些词,翻译成中文也是“大词”)、说您提到各种西文典故,是在说整套话语知识、品味和趣味的区隔——针对的仍然是碧山计划的话语,而非您个人。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思想和心路历程,外人无权评判。不过,既然是讨论碧山计划,那我就多说一句建议:您在演讲和回应文章中,不断提新西兰、美国、日本等地的经验,这固然是您的观察和体验,但是,听者读者一个非常自然的问题是,这些经验能否被用于中国的乡村建设?您在演讲中说了一句话,大意是,"为了理解中国的乡村与乡村建设,我去了美国伊萨卡……”,这是否是理解中国乡村的好办法?就好像有人说我,爱用西方理论套用中国——这是我学术训练带来的局限,对方说的很对,我也虚心接受,那么,同样的,既然是建设中国乡村,这些海外经验,多大程度上适用,应该被怎么拿来用,如何避免“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就是你们作为实践者,不得不深入思考的问题。
说星星vs.路灯、说Moleskine、说碧山书局的审美趣味、说英文PPT与西文典故,这些,都是在说碧山计划的话语里(而不是您个人)存在的“区隔”。我的文章,本就是一篇讲文化再生产的文章,虽然不是一篇论文,但的确是立足于学术话语的。豆瓣上有评论说我爱用大词,我认为说得十分有理,虚心接受——我的文章,的确是在借用布迪厄谈区隔与文化。如果您要是非认为,谈点布迪厄的区隔就是搞阶级斗争、就是煽动仇恨戳人G点——不说这其中诛心得可怕,这也逼得我只能非常无礼地回应一句:多读点书好嘛……
下面再来说一些我认为您并未回应的问题:
你们看不惯西递宏村的发展模式、反对碧山村民自己想要的“高档化”(Gentrification),认为如果这样搞,就没有农村该有的样子——那请问,农村该有什么样子?凭什么是你们决定农村该有什么样子?你们看不惯西递宏村村民“在村口拉生意”,可是猪栏酒吧也是搞盈利性经营——都是生意,都是生活,为什么要被赋予情怀与价值秩序上的差异,这其中,你们的逻辑如何自洽?
甚至,说开去,您说我是空降碧山——其实追根溯源,你们和我一样,不也是空降碧山吗? 你们真的和民国几位先生一样,尝试融入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中了吗(不是有人来做个客就叫“融入”),真的搞的是以村民、而非知识分子为中心的乡建吗? 既然是要搞乡村“共同体”,那么如何平衡计划话语中的精英主义倾向与文化区隔?共同体,究竟是谁的“共同体”?
说开去,和村委会座谈,村委会对于碧山发展的定位是很清楚的,是一个“休闲文化旅游度假村”——村委会对于您、对于左靖先生的态度也很明确,是“城里来的老师,帮助打造我们的文化产业”。村委会也坦言,村民有的意见很大,也有不少来反映过问题。您的碧山计划,和村委会的发展目标不同,和村民的诉求也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听到了您说要“远离资本远离基层政府远离NGO”强调自己的“理想主义”和情怀,然而我却并不知道,靠着这种“远离”与情怀,在中国当下的模式下、在碧山的具体情境中,共同体如何能平衡好乡村基层政府与村民的关系,成为真正包容(inclusive)的“乡村共同体”,而不是外来知识分子小团体?
您说有和村民的沟通座谈,这我不否认——然而那天的座谈中,也有人提问了,参加座谈的“村民代表”,就是不多的一些老年男性。在后续的Q&A中也说到,“老年男性”常被看成是村民中的“智者”。那么不说别的、不说“智者”和“非智者”的划分,就说在这里,女性村民,也是在你们的沟通座谈中缺位和失语的——那么,还是回到我的那个问题,当我们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个乡村共同体,又是谁的共同体?
对于您对我个人的质疑和攻击,回应如下:
您看不惯我“深情”回忆与反思自己的精英教育经历,这没问题,就和我看不惯碧山计划话语里的精英主义一样。可您一面单向地,甚至是恶意地曲解我的用心,一面大呼“我恶毒揣测您”作委屈状,那么,我还是那句话,您如何自洽?还是,这仍然是和看不惯村民拉生意但又赞美知识精英下乡经营一样,搞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招数?
你说我一条转发朋友的微博,转发是为了给你们“泼粪”——对此,我真的不知该说什么,或许只能大笑三声——我这边已经准备从网络辩论中翻篇儿了,和自己生活中的好友微博正常互动,压根就没提到你们,你们也要上赶子来自己对号入座——且不说这行为本身就是您自己批判跳脚的“刻意曲解别人用作靶子以满足自己的私心”。,就说你们,真的,能不能,别这么玻璃心且擅长脑补啊。要知道,这个世界、别人的生活,真的不是时时刻刻都围着你们转的好嘛……您(至少对我)还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事实上,我文章里批评的知识精英的自我满足、自我膨胀、自我拔高的优越感,很多就来自一种觉得别人啥事儿都是针对揣测你、欺负你、误解你的“莫名自矜”(self-important)。
现在,再来说两点澄清:
一、您说我得出的结论是和一位方姓村民交流——我不知您从哪里得到了这个信息。我从未在任何文章里公开被访谈者的可识别信息。和我交流的村民不姓方(或者说,我不能承认也不能否认他真名儿到底姓不姓方)——所以,对您还是那句话,既然说到别人“曲解自己”时情绪激动,那自己也就少脑补一些。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伦理,这种对个人访谈对象的私人可识别信息,想想也知道,我怎么可能随便公开。
二、我的文章,只代表我自己的观点,和南大暑期班无关。对于南大暑期班,写文章前,并未料到文章会发酵至此(毕竟我的微博与豆瓣,都是和朋友交流的地方,关注量有限),但这的确也是我顾虑不周。如果对暑期班造成了任何影响,我都表示十分抱歉。对于陆远老师,十分感谢这两周您的费心安排,也感谢去碧山一路帮助照顾。
最后想说,我从来不想以对抗的心态来讨论问题:中国环境的复杂性,一个问题的复杂性,加上不同人不同的视角,得到的观感,看到的东西,自然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一个计划,甲认为好,乙认为不好,这很正常;您认为碧山计划十分有利,我认为其中有值得商榷之处——我把我认为不好、值得商榷的方面和原因讲出来,这也很自然。
不能因为提出批评,就认为别人是居心不良——这是良性沟通的重点。
也有支持您的评论,认为您“做”,就是比“说”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里我不想趁机标榜自己其实也“做”过什么,我倒是想说,不是所有“做”,都是天然正当绝对正确的。倘若归个谬,难道做得全错,也是正当的“做”吗?“说”和“做”并不天然矛盾,提出批评意见的旁观者,也不是抱着看实践者笑话、说风凉话的心态去的。就好像批评质疑碧山计划,又并非是希望您计划破产、又并非是希望碧山村“倒掉”,对于猪栏酒吧——我也没有断人财路的爱好。您那天也提到了“自我审查”,既然都觉得“自我审查”是问题,那么当别人实践自己的“言论自由”时,不是应该抱着更加理解的态度吗?
还是我前面那句话,既然自己觉得被曲解的委屈,那就也不要去脑补他人的出发点、心态和用意。
在网上写文章,的确发现,我经常被人拿“哈佛女博士”说事儿——我自己写文章批评精英主义时,的确也会说自己在北大和哈佛的教育经历,这倒不是像一些人揣测的那样“为了变相秀优越感”或者“压人”——我想说的恰恰是:我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非常精英主义的人(甚至如今仍有痕迹),也一直身在精英教育的体系里。不仅北大哈佛,我的小学与中学,都是入学要各种选拔、在某种意义上十分讲精英教育的地方——我不避讳自己的成长经历、不避讳曾也是个精英主义者,所以当我批评精英主义、谈文化与区隔时,我其实也是在回溯与反省自己与自己身处的环境世界,也正恰恰是因为这样,反而不是把“我”和“你”对立居高临下的。
我对精英主义的批判,自然是我自己的价值观。当然,精英(虽然谁是“精英”本质是非常模糊的)、精英教育、精英主义,并非什么“原罪”——然而,如果在谈“共同体”谈包容(inclusiveness)的同时,用一套精英主义的话语生成着新的不平等、区隔和排除(exclusion);如果在谈村民自主自治的同时,带有的是一种“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农村该有的样子”的想象与俯视心态——那这其中的自我矛盾与不自洽,就成了观者批评和质疑的空间。
就说这些,最后祝您在碧山生活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