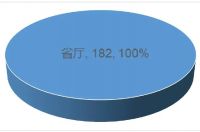可称得上是“思想”的东西,不是零散的议论,也不是灵机一动的所得,而是系统思考的产物。我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真正的思考始于“风波”之后,而独立的思考则始于90年代中期。这些思考不是单纯的好奇心的产物,而是出于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不是出于偏见的人云亦云,而是立足现实的独立思考。
这些思考表述于一系列文章之中,主要是《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制与合法性基础》、《未来三五年中国大陆政治稳定性分析》、《再论“行政吸纳政治”》、《论合作主义国家》、《仁政》、《文化民族主义论纲》、《中国特殊论》。前三篇文章是对改革以来中国大陆政治演变的回顾,再三篇文章是对未来发展前景的探索,而最后一篇文章则是一个总体性论述。在这些文章中,我尝试提出一套概念,确立一套命题,形成一种库恩意义上的“范式”,为理解中国的政治现实和政治发展提供一种有力的理论工具。
王思睿说:“许多人对康晓光有一种误解,认为他是‘精英联盟’的拥护者和鼓吹者。笔者在与康晓光本人面对面讨论这个问题之前,也有类似看法。其实康晓光对‘精英勾结’、‘精英联盟’的现实是深恶痛绝的,因为这种勾结与联盟是为了‘盘剥大众’,加剧了社会不公正。”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我对“精英联盟”既非“全盘否定”,也非“全盘肯定”。
一方面,我对“精英联盟”所带来的政治腐败、钱权勾结、金融风险、不平等确实“深恶痛绝”。我认为这种格局是不公正的,缺乏起码的道义基础,应该也必须予以改变,所以我才要探索更好的政治方案,进而提出了“合作主义国家”和“仁政”。另一方面,我并不全盘否定“精英联盟”。在转型初期,这种联盟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利于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且客观上它确实带来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带来了经济、社会、政治自由的扩大,带来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而且支撑“精英联盟”的内在机制(“行政吸纳政治”或“政治行政化”)也是可以行之久远因而也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政治运行机制。所以,在批判“精英勾结”的同时,我对“精英联盟”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积极贡献也给予充分肯定。有鉴于此,我主张在权威主义框架下探讨政治发展道路,致力于建设一种“好权威主义”。我的答案就是“合作主义国家”和“仁政”。前者是可以实现的最好的权威主义国家,而后者则为“好权威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理论。
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的“合作主义”是一个来自西方的概念。“合作主义”(corporatism)也被译为“法团主义”、“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工团主义”以及“阶级合作主义”等等。通常情况下,这一概念指示一种特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也被用来指示一种特定的市民社会形态,但是很少被用来描述一种民族国家的政治体制。
最早用“国家合作主义”解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是旅居澳州的陈佩华。在中国大陆,最早用法团主义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是我。在1997年出版的《创造希望》一书中,我就明确提出,对于中国来说,法团主义应该成为调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随后,我又在一系列公开发表的论文和专著中宣扬这一观点。张静对法团主义做了一个出色的综述。但是,她把法团主义作为一种学说或思潮来讨论,而没有讨论它对于中国的现实意义。
对于我来说,“合作主义国家”首先是一种“理念”。这一理念所推崇的是一种有效、公正、稳定的社会合作秩序。它承认社会分化的事实,承认社会冲突的存在,同时也意识到合作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赖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其次,这种理念进一步体现为一组“原则”,即“自治”、“合作”、“制衡”与“共享”。在市场社会中,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劳动阶级是四个最主要的社会阶级。因此,所谓“自治”是指四大阶级的自治,所谓“合作”是指四大阶级之间的合作,所谓“制衡”是指四大阶级之间的制衡,所谓“共享”是指四大阶级公平分享合作的成果。第三,这些理念和原则又进一步体现为一系列“制度”,即“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福利国家”。“权威主义”保证统治阶级自治。“市场经济”保证资产阶级自治。“法团主义”一方面保证劳动阶级自治,一方面提供了阶级合作机制。“福利国家”保证劳动阶级能够比较公平地分享社会合作的成果。而“权威主义”、“市场经济”、“法团主义”保证了四大阶级的分权制衡。第四,任何制度都需要“合法性理论”,所以我提出了“现代仁政论”。“现代仁政论”规定了权威主义政府的价值取向(民本主义)、行政原则(富民教民)、权力更替规则(禅让制)和社会理想(大同世界)。“现代仁政论”一方面为合作主义国家提供了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也为社会批判提供了“参照系”。最后,有效的合法性理论必须有民族文化渊源,所以我提出“文化民族主义论”。
可见,“合作主义国家”具有特定的理念、原则、制度、合法性理论、文化渊源,而“合作主义”仅仅相当于“合作主义国家”的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法团主义”),所以,我所提出的“合作主义国家”与社会学和政治学中流行的“合作主义”不可混为一谈。
少数人统治、剥削、愚弄多数人是最基本的政治现实。古今中外一切国家都是如此,社会主义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也不例外。国家是垄断暴力的机构。自从出现阶级分化,政治就表现为“阶级专政”,而“阶级专政”加剧了不公正。所以我提出以“阶级分权”代替“阶级专政”。这就是“合作主义国家”实质。毫无疑问,“合作主义国家”期望以“精英制衡”代替“精英勾结”,但是“制衡”不仅仅局限于精英之间,也存在于大众与精英之间。在“市场社会”中,“法团主义”和“福利国家”是支撑大众与精英制衡的制度设置,而“权威主义”和“法团主义”则是支撑精英制衡的制度设置。
“合作主义国家”承认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这一事实,并且把阶级看作为“理性经济人”,相信政治格局是各个阶级生死较量的结果。这就是建立“合作主义国家”所需要的理论前提。显然,“合作主义国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推论。它没有马克思主义那么复杂精致,也没有那么大的理论雄心,不打算提出一个覆盖人类全部历史和未来经验的历史哲学。它只是对现实的回应,只是希望未来比现在更加公正。仅此而已!这里不存在什么“经济决定论”、“阶级统治论”、“阶级分权论”之间的冲突,因而也不存在王思睿所谓的“缺乏理论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
至于“合作主义国家”有没有资格与“马克思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相提并论,它是否提供了第三种具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并不单纯取决于理论形式是否完美,而要看它是否真实而准确地反映了支配中国政治现实的主导力量及其相互关系。而且即使理论真实准确地反映了现实,也需要一个长期的发展和完善过程。任何“大理论”都有一个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期间至少要经历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艰苦努力。
王思睿质问道:“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官僚和商人就一定是相互制约的关系,而不是相互勾结的关系吗”?我什么时候说过“在现代工商社会中,官僚和商人就一定是相互制约的关系”?“合作主义国家”属于“权威主义”,但“权威主义”不等于“合作主义国家”。在《论合作主义国家》一文中我把现实中的权威主义分为四类,而“合作主义国家”仅仅是其中之一。也就是说,“合作主义国家”仅仅是“权威主义”的可能形式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形式或必然的形式。同时,“合作主义国家”也意味着权威主义并不一定必然“不好”,还存在“好权威主义”的可能性。
王思睿还认为我承认存在“外部压力”就是与我所主张的“中国特殊论”和“文化民族主义”是自相矛盾。殊不知,我的一切讨论都是在“全球化”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没有来自西方的“外部压力”就没有中国的近现代历史。而且,如果没有“全盘西化”这种“外部压力”,又何须讨论什么“中国特殊论”和“文化民族主义”呢?这里哪来的矛盾?
四、再驳宪政民主神话
在《论合作主义国家》中,我没有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而是依据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正当性和有效性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批判。奇怪的是,在《合作主义与国民意识形态》中,王思睿对此没有提出任何正面挑战,只是把早已过时的关于民主的陈词滥调重复了一遍。他把民主说得天花乱坠,对其缺陷则只字不提。可以说,王思睿对宪政民主的表述基本上还停留在卢梭时代。
在这里,我不想重复《论合作主义国家》对自由民主主义的批判,仅就宪政民主与阶级合作的关系、宪政民主的基本理论结构做一简要回应。
王思睿说:“宪政民主国家打破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一体化,社会底层的代表可以通过普选进入议会和最高行政当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社会上层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优势”。事实上,宪政民主并没有打破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一体化”,而是建立了一种新的“一体化”。这种“一体化”的特征是经济精英成为主宰,而政治精英成为经济精英的附庸。宪政民主就是维护资本利益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正是它使得资产阶级的经济优势堂而皇之地转化为政治优势。社会底层中的个别人也许会进入上层社会,但这些“幸运儿”不会成为底层的代表,而是成为上层的新成员。这种“社会流动”的作用是充实上层的力量并削弱下层的力量。在宪政民主国家里,不同政党对待大众的态度也许有差异,但是在捍卫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根本立场上绝对没有差异。王思睿又说:“在宪政民主的早期阶段,精英制衡是促进社会公正的一种重要机制,而在当代宪政民主国家里,通过大众民主的普及,民众对于精英的制衡已经取代精英之间的制衡成为推进社会公正的主要动力。”实际上,无论是宪政民主的早期阶段还是当代,都不存在“精英制衡”,在宪政民主国家里,经济精英支配一切,从整体上来看,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是经济精英的忠实“马仔”。
王思睿指出宪政民主的“系统理论的硬核”是“阶级调和—社会契约—民主国家”。这简直就是学术笑话!如果硬要编排出一个“系统理论的硬核”的话,那么“宪政民主”的逻辑链条应该是“主权在民—社会契约—民主国家”。现代国家理论是伴随着主权国家的发展而来的。“契约论”把主权赋予“全体国民”。“契约论”强调“一致”或者说“人人平等”,而不是强调“差异”或者说“阶级分化”。国家是平等的国民建立的“契约”,而能够体现这种平等契约的国家形式就是“民主”。这里根本就没有涉及到“阶级”概念,更谈不上什么“阶级调和”。“阶级分化”、“阶级斗争”、“阶级调和”都是从现实出发进行政治理论思考的产物,而“契约论”仅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思辨”,除了天真可爱的卢梭,大概没有人相信所谓“自然状态”、“建立契约”之类的东西具有现实和历史依据。契约论的鼻祖霍布斯也仅仅把“自然状态”当作逻辑演绎的前提,而不是国家发展的历史事实。
为什么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民主的宣讲还停留在如此低下的水平上?我认为存在三种可能:第一,无知,不了解这些几十年前的理论进展;第二,弱智,看了这些东西,但是没有能力理解;第三,看了,也准确地理解了,但是出于偏见或政治上的算计,故意信口开河。这三种情况同时存在。就王思睿而言,我相信他是一个勤奋而有头脑的人,所思所言不会是出于无知或弱智,而是出于偏见。我奉劝王先生,不要把“政见”说成“真理”,否则会把那些无知或弱智的自由主义者引入歧途。当然如果你说“这就是我的策略”,那我就无话可说了。
五、另一种“思潮分类体系”
许多学者热衷于对思潮和学者“分派”、“划线”。王思睿也不例外。最近,他提出“五分法”,把学者和思潮划分为“极左派”、“左派”、“中间派”、“右派”、“极右派”。有意思的是,他把自己划入了“中间派”,而把我划入“右派”或“右翼马克思主义”。也许在王思瑞看来当“中间派”的好处是可以左右逢源。例如,他本人就放开手脚把别人的好东西都抓过来据为己有。
为了回应王思睿的挑战,我也凑个热闹提出一种“思潮分类体系”。我根据两个维度划分学者和思潮的类别,一个是“社会经济权利维度”。这一维度指示各派对各个阶级的态度,主要体现在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共政策主张之中。另一个是“政治权利维度”。这一维度指示各派对政治权力归属的态度。政治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精英的特权。各派的差异在于把政治权力赋予哪一类精英。我用一个2×3矩阵表示分类结果。为了便于理解,在每一类中还列出了一个具体“标本”。
在我的分类体系中,“合作主义国家”属于“中庸型权威主义”,王思瑞的“宪政民主”应该属于“民主主义右翼”,但是考虑到他最近主张“共同底线就是社会公正,就是宪政民主”,也可以把王思瑞式的宪政民主归入“中庸型民主主义”。我相信这种分类方法可以更加清晰、准确地表现出各类思潮的本质差异。
社会经济权利
政治 维度
权力维度
倾向大众
兼顾大众与精英
倾向精英
主张政治精英专权
权威主义左翼
民粹型权威主义
中庸型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右翼
精英型权威主义
主张经济精英专权
民主主义左翼
社会民主主义
中庸型民主主义
“第三条道路”
民主主义右翼
自由民主主义
六、也谈“共同的底线”
经过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如今资本已经坐大,同时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上“公正”呼声持续高涨,于是自由主义者识时务地改换了谈话的主题,不再谈“民主”了,而是大讲“自由”和“宪政”。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继续鼓吹不平等有被社会抛弃的危险,于是毫不犹豫地把“新左派”的“公正”大旗抢过来扛在自己肩上。例如,王思睿就提出“要能够求同存异,达成‘底线的共识’。这种共同底线就是社会公正,就是宪政民主。”
“共同底线论”的发明权应归于秦晖。如今它已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镇宅宝物。“共同底线论”着眼于各派的“共同价值”,并希望据此建立对抗权威主义政权的“统一战线”。要知道,在理论分歧的背后是利益分歧和阶级对立。不同的阶级拥有不同的利益,对政府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的制度建置也有不同的要求,几乎不可能找到一种令各阶级皆大欢喜的解决方案。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各个阶级有一致的利益,但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也相当深刻,所以很难建立一种有实际意义的“共同底线”,更不用说在此基础上建立有效的“统一战线”。
就今日中国而言,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们恐怕都不会接受“社会公正”这一“共同底线”,而“宪政民主”只能是经济精英和依附于他们的知识精英的“共同底线”。所以,把“社会公正”与“宪政民主”混为一谈是荒谬的,而把“宪政民主”定为全社会的“共同底线”更是自以为聪明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也许是可能的,但如果涉及到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即使是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也不可能存在。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在于,对外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对内建立一个繁荣公正的社会。我认为只有“合作主义国家”才能帮助中国人实现这一伟大目标。所以,在市场席卷全球的时代,如果说十三亿中国人真有什么“共同底线”的话,那么这“共同底线”就是“合作主义国家”!
我感觉在围绕“思潮分类”和“共同底线”的讨论中,从秦晖到王思睿都不是在讨论学术问题,而是在讨论政治策略。更准确地说,是打着学术的幌子传播政治斗争策略。“分派”和建立“共同底线”都是为了建立“同盟”,其根本目的是团结各派社会力量与权威主义政府作斗争。在历史上,资产阶级受压迫时期与大众存在“共同底线”,在夺权过程中与大众建立过“统一战线”,但资产阶级夺权成功之后就抛弃了“共同底线”,而是忙于限制大众的民主权利,遏制“多数暴政”,抨击“民主”,鼓吹“自由”,并积极宣扬“宪政”。毫无疑问,今日中国的“共同底线论”也是为资本利益服务的“伪学术”。
2004年3月6日,初稿;
2004年3月1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