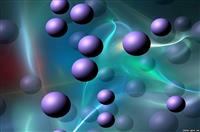2011年5月28日,媒体报道了卫生部证实在业界早被热议的中国全球基金援助款项被冻结的消息。根据今年3月发布的《中国全球基金观察》(第14期)透露,中国全球基金RCC 项目一共有753个社会组织申请到了8 442个项目,用于支持这些项目的资金预计是3 200 000 美元。一旦这笔资金冻结甚至退出,对草根组织将带来什么影响?防艾领域的草根组织未来的生存之路在哪里?
背景
成立于2002年的全球基金全名为“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是全球唯一一家政府与民间合作创办的国际金融机构。据称,2003年来,中国接受了来自该组织的5.39亿美元援助,这些资金主要用于降低结核病发病率、预防和治疗艾滋病感染及消灭疟疾等项目。本文内容皆围绕该援助中的防艾项目被暂时冻结展开。
全球基金是以国家为单位申请的,国家层面有一个国家协调委员会,简称CCM,是根据全球基金的有关要求,为审议、批准和协调申请全球基金项目,监督和指导经全球基金批准在中国境内实施的项目而建立的协调机制。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被指定为全球基金项目执行机构(PR),负责全球基金批准项目的计划制定和组织实施,定期向国家协调委员会汇报项目的执行情况,并接受国家协调委员会的监督。
据AIBO青年活动中心(“常坤的家”)创办人常坤介绍,2010年11月全球基金秘书处与Curatio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和YozuMannion有限公司联合签订了一项合同,要求其对中国艾滋病滚动整合项目(RCC)开展外部评估。在国内层次上,全球基金被冻结是和这个评估,以及社区组织的人和机构不断表达抗议、发一些不满的信件有关。全球基金在民间的推动下的确越来越透明,但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累积之后也是不少的。其中最大的争议就是资金的分配,还有资金使用的腐败问题。
草根组织受影响
红树林是一个抗艾网络型组织,这次资金冻结对该组织没有影响。负责人李想说:“红树林不足以代表其他的草根组织。从资金上说,我们的确拿过全球基金的经费,但是这在我们的总经费中所占比例不足5%。而且从2008年开始,就不再申请所有的全球基金项目了。”据悉,最近3年红树林主要由一家国际基金会资助,只做网络项目,防艾公益圈里的其他活动很少参加。李想说:“最近几年,全球基金的变化我不是很清楚,因为我很少参与其中了。”
中国女性抗艾网络目前由21家小组组成。何田田是中国女性抗艾网络的负责人。全球基金冻结以后,该网络对大家的资金来源做了简单的调访。小组成员中曾经使用过全球基金的资金的有5~6个小组。这几家小组中经费几乎全部来自全球基金的占到一半,另一半小组从别的地方获得活动经费。资金全部依赖全球基金的小组目前基本上停止了工作,但是她们有时候也开展活动,因为小组成员联络等活动并不一定要有资金支持。
北京爱之方舟负责人孟林在微博转述了一份快速评估报告里的数据,资金冻结对防艾领域的NGO的影响达到80%多。孟林说,全球基金冻结在中国的资助,肯定会给草根组织带来非常大的冲击,从冻结以来这半年的情况来看,已经有失业出现了。
全国艾滋病信息资源网络(CHAIN)经理蔡凌萍说,要评估全球基金暂停对NGO的影响,首先要区分执行全球基金的NGO到底有哪几种。在蔡凌萍看来,除了协会学会这样的组织之外,社区组织也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类是自发型组织。这类组织在全球基金没有进入中国的时候,就已存在并开展社区服务和倡导工作,因此没有全球基金的支持也有可能继续发展;另外一种是催生型组织。这类组织是由全球基金项目催生出来的,而且也是由目标人群成立的,但是主要的工作是为完成全球基金的项目。这类组织中发展得好的即使没有全球基金项目也可能继续做下去,发展得不好的会因为没有了资源就会解散;第三种是寄生型组织。这类组织的人员本身就是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或者高危人群干预队,不管有没有全球基金都会继续工作,因为疾病控制本来就是他们的本职工作。这类组织也是很多社区人士口中的“假组织”。由此可见,执行全球基金项目的NGO构成复杂,所以不同组织所受到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
常坤介绍,在RCC项目之前,不同轮次的全球基金项目中,对民间组织、社区组织等定义是不同的,这也是一个不断细化的过程。这个细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过程,比如最早将官方的群众型组织也作为民间组织,而后细分了社区组织、社团等不同的种类。但是,利益各方依然以对社会组织不同的理解而造成巨大的利益纷争。
常坤是全球基金的批判者。在他管理的中国最大的艾滋病邮件组(chinaaidsgroup@googlegroups.com)中,曾有HIV感染者发出“全球基金滚蛋”的抗议。他说,中国全球基金项目的各级执行机构大量存在着以洗钱和腐败为目的而“制造组织、捏造组织”和分化独立的社区组织的现象。
常坤还认为全球基金当下的执行体制破坏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现在的社区组织没有钱不办事,以前我们做的是助人自助,要承担责任。现在我们搞个调查问卷,没有钱都没有人给你填卷了。”他认为,到目前最没有规则的还不是政府,而是草根组织。全球基金培养了不少不好的东西。做一个2~3万的全球基金项目,经常能听到说结余了一半的钱归负责人了。“草根组织的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这点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关键在于,在有人‘作恶’的时候,要有纠正机制。但是全球基金在华执行机构为了完成他们的指标,在包庇‘作恶’,甚至协助造假。”他认为,开放组织注册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资金发生梗阻的原因
中国全球基金观察执笔人贾平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RCC项目是国家在统合所有抗艾资源,包括中央转移支付经费、省、市和县(区)级投入,以及其他国际合作项目的资金,通过全球基金滚动资金渠道申请到的整合滚动项目。整个盘子约有22亿美元,其中来自全球基金的资金为5.09亿美元,自2010年开始为期6年。孟林说,RCC整合不该是一个简单的集权,但是现实却是如此。
资金没有达到真正的草根组织,梗阻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在孟林看来,有东、西方文化对非政府组织的不同理解,还有社会制度和文化差异。全球基金要求一部分项目资金给非政府组织执行,但是到底什么叫非政府组织?争论到现在,全球基金在中国是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是到了必须捋顺关系的时候了。下一步要明确什么是没有政府背景的公民社会组织?怎么去区分这些不同组织?
蔡凌萍从结构上分析了梗阻的原因:全球基金项目在中国有三个工作内容:一是药品供应,比如给中国提供免费的药物,这部分“生命钱”并没有暂停;二是支持中国草根NGO的参与和发展,全球基金和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定义理解的差异”也是导致此次经费暂停的因素之一;三是加强卫生疾控系统的服务和能力建设。 当然,全球基金的很多理念在中国贯彻的过程中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但是以往的全球基金项目主要是在一些特定地区开展,而2010年启动的新一轮的RCC项目强调的是“整合”,包括管理的整合、计划的整合、经费的整合和指标的整合。全球基金项目实际上被纳入了国家的整体规划,这些策略、资源、指标等都纳入国家体系里,国际资源变成了国家经费预算的一部分。而由于政策和管理的限制,草根组织是没有办法“被整合”到国家体系中的。其具体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并未如约定那样,将规定的项目资金分配到草根组织。这是一个结构性矛盾的具体体现。
蔡凌萍说,RCC的项目让我们看到的是“一国两制”。虽然项目管理方是在国家和地方的疾控部门,但是一部分项目执行方是NGO,但NGO不在这个资源分配、管理、培训考核等工作的系统里,从体制和政策上来说,将NGO“整合”到这个体系里,还是非常困难的。这个结构性的因素才是中国无法达成全球基金要求的首要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管理者的意识问题,即各级政府是不是愿意支持NGO的发展,或者是否信任NGO的发展。第三个问题才是社区组织的能力问题。
继续“淘沙”
在防艾NGO人中,孟林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北京爱之方舟感染者信息支持组织的负责人,他是中国全球基金项目国家协调委员会以社区为基础组织或其他非政府组织类别组代表(CCM代表)。在邮件组里,他经常被一些社区组织骂到。
他对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现状的基本认识:“第一,全球基金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以及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第二,目前的管理机制不利于草根组织的公平参与及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在接受中国发展简报的访谈时说:“这两个想法一致纠结着我,从技术层面我去推动、操作,也是基于这两点考虑。”
造成目前这个僵局,有政府的责任,NGO也有问题。孟林说,全球基金的资金不是作为福利发给草根组织的,而是要给具有执行能力的NGO。不能因为你是草根组织,你是艾滋病患者,你是同性恋,就必须给你钱。这会导致思想上、资源分配上的混乱。
全球基金冻结只是个契机,事实上这是社区发展到这个阶段上应当做出的回应。 孟林说:“下一步要做一个NGO的评估和评级工作。比如A级组织达到标准后,对申请的资金可以上不封顶,有能力的做500万的项目都可以。新生的组织也不能将其排挤出来,比如C级组织可以是最初级的组织,对这类组织也有一定的标准和资助要求。”
现在公益圈之外的人光看到了艾滋病圈里的“狗咬狗”,但实际上里面有很复杂的东西,有利益、也有理念的冲突,还有沟通上的不足。孟林说,全球基金在中国的政府执行层面已经明确提出了改革的要求,政府也明确表态回应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措施。接下来如果社区不去反思,不去加强自己的内功,注定还是要被淘汰出局的。诚信怎么提高,合作怎么开展,内耗、内斗都等着去解决。
孟林坦诚地说:“我正在打算将过去在网上骂我的、反感我的,请到北京来,面对面的给我提意见,我会请国际组织观察员到现场。这是理性建设、开始走向合作的第一步。过去我们没有时间,因为还要考虑民主与效率的关系。他们以为我们是资源的分配者,其实不是,他们完全理解错了。在这个情况下骂我们。当然,因为我是草根,我的能力视野都有不足,沟通能力、妥协能力都成了很大的障碍,我也在反思。慢慢来吧,谁也不是救世主。”
李想认为不断的争吵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他说:“以前我们红树林的确是在里面做代表,但是从2006年武汉大会开始,我觉得这里面挺没劲的。尽管这样,我还是认为,这个在外面看来一团糟的争论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让其发声。不过,淘沙的状况还没有结束。”
筹款出路
当笔者问常坤:“一旦全球基金撤出,未来的草根的筹款局面将会如何?”他解释到,让全球基金滚蛋的真实意思是,让全球基金在中国的执行机构滚蛋。在机制上做出改革举措,比如能不能有双PR机制而形成竞争,犹如中国电信收购了联通的CDMA,形成中国移动、联通和中国电信的三家竞争。
何田田谈到,现在大家也在困惑中,毕竟全球基金给的资助并不多,2~3万元不足以维持草根组织的正常运转,而且全球基金不负担办公费用和人员工资。女性抗艾网络没有向全球基金申请过资金,几乎所有资金还是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资助,此外,有一家位于上海的法国餐饮企业Kathleen"s 5向她们提供过资助。该网络目前在寻求解决办法,比如向企业筹款。但还在动议阶段,没有具体的行动。
在寻求国内资金方面,红树林先走了一小步。李想说,现在国内这些基金会对艾滋病领域资助的确是存在的,但国内资助方从资助方向和地域上看都是很狭小的,而有的国际组织长期支持一些项目,产生的影响也会是长期的。红树林主要资助方的资助也只到今年为止,今年处在一个转型和过渡的时期。现在红树林在网络项目方面拓展与其他机构长期合作,目前已经作为合作方之一参与到某公募信托基金资助的项目中。简单地说,信托基金从收益里拿出一定比例捐赠到这个项目中。
蔡凌萍担心,假如全球基金撤出中国,这不仅是对NGO的挑战,也是对政府的挑战。在国家的艾滋病防治经费中,全球基金提供的经费不到20%,但是2010年、2011年的预算中,所有NGO的经费都是由全球基金项目提供的。一旦撤出,国家是否要填补其在NGO领域的投入?对NGO来讲,在全球基金还没有离开中国之前,我们是否要倡导政府“拿出预算购买NGO的服务”?
防艾组织的成长和贡献
防艾组织是公益领域里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个圈子更少为外人所知,即使在公益圈内部也少有跨领域的交流。外人看到的可能是防艾组织邮件组里的争吵,而且言语激烈,火药味重,让人避之不及。蔡凌萍对防艾NGO的工作却予以高度评价。她认为,通过全球基金草根NGO做了很多的工作。她甚至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领域的NGO能够做到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与政府直接对话,而且是有机制保障的对话。NGO代表和感染者代表作为全球基金国家协调委员会(CCM)成员进入决策层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机制。两个代表实际上在RCC项目以来,正在影响着国家艾滋病防治策略制定和经费分配,而国家NGO咨询小组和各地的NGO咨询小组也正在各个层面影响着项目的管理和执行。 从一个更积极的角度看,全球基金不仅仅是一大笔资金,它更重要的是在促成一种NGO参与的机制。其他领域的NGO应该加强对艾滋病领域NGO的了解,因为在同样困难的背景下,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同性恋、性工作者、静脉吸毒者等等这些‘社会边缘群体’,以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开展工作,实在是非常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