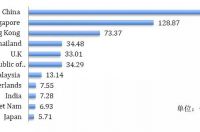本文编自陈韦帆的实习报告《在土地中汲取重整的力量》
作者 介绍: 陈韦帆,少数民族女性,教育经历主要是7年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本科也兼修了经济学学位。在校期间多参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人类学方面的调研项目,2008年毕业后,先后加入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乐施会城市生计团队工作。
2014年,出于一直以来的返乡召唤,离开学习工作13年的北京,回到家乡云南,在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欢快地工作在流动妇女组织工作的社区岗位上,两年后调任研究统筹,负责推动连心的行动研究和政策倡导工作,同时也负责沧源、昆明等地社工机构的陪伴督导工作。
12年来,她坚信自己的使命在于从日常生活与身体力行开始,推动社会性别公正、少数民族社区可持续发展和青年人成长。
陈韦帆来自云南连心社区照顾服务中心,两岸青年协作者互派实习计划2018年成员,2018年秋在台湾花莲好事集实习。
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在山里喝茶的时候,在校园里行禅的时候,我都会突然有一种恍惚感,觉得自己身处宇宙之中,虚无又实在地存在着。这会不会就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踏实,又或是一种重新回到“全人”的完整?
出发去台湾的那段时间,我处于非常焦虑和疲惫的状态。
一半因为自己正处于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眼前有很多种可能性,却没有太多自信去选择;一半因为自己深切地体会到生命的破碎,这破碎未必都是坏事,比如有可能让我更敏感于自己的一些重要人与事,但却让我一时间非常渴望一种“完整感”。
我带着很多问题在这样的状态里跋涉。比如,在培养和陪伴少数民族年轻人的过程中,我体验到Ta们困于生计和城乡不公结构的“沼泽地”,也体验到“社工全能化”在政策空间争取中的不得不为,以及由此带给一线同事们的压力。
我自己的破碎状态,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在,我所能借助的“工具箱”越来越小,包括思维惯性越来越严重,督导视野更加受限,难以支持年轻同事们更多地看到Ta们自己的力量和资源。
这些状态和问题,也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在台湾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短短十五天的时间,我尽可能放下自己,多些聊天、提问、思考和体验,在丰富的信息之中去沉淀。
台湾花莲好事集
为什么农友的生活品质不能提高呢
这次实习,我在两个有机农友家停留了几天,帮忙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但更多是和他们访谈和讨论,围绕着农业发展、生命历程和未来计划等几个方面。
江玉宝和黄明汉两家人是当地从惯习农法转向有机耕作的第一代农友,十几年来他们不断地更新对农业和生态的认识,让我特别感触。
江大哥从“争取每天5点能够下班,每周休息一天”说起,到反思“有机农友为城市人提高了生活品质,那为什么农友自己的生活品质不能提高呢?”这大大刷新了我对有机农业“很苦”的认识。
但提高生活品质也需要付出代价,农友需要更有智慧地工作,也需要减少自己对收入的期待。
“你一天做12个小时的工作,你同时也会错失了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拼命地工作呢?”
“我们在追求生态的平衡,那我们的心态也需要平衡,否则怎么可能实现呢?”江大哥如是说。
更有智慧地做农,其实也是有机农业的题中之义。
江大哥实验出来一个经验,福寿螺与野鸭子在不同时段能够发挥不同作用;黄大哥通过多样性种植来抵抗风险。这都是农友们结合自身所处生态系统,不断观察摸索、学习累积出的宝贵智慧。
我们少数民族本身有稻田养鱼、稻田养鸭等农作方法,这也是“万事互相效力”生态系统观的一个体现。
而这些智慧中,最重要的是认知到“人的有限性”。我们只有认知到自身的局限,才能更加细致地去“认识”自然的力量,从而能够掌握关键点,增加自己的智慧。
所谓智慧,不再是“控制”,而变成了“连接与协力”。
如果说惯习农法是通过“科学”的力量无限扩大人的控制力和重要性,那有机农业可能反而是需要人的退后和让步。农人在生态系统之中,更多地成为了一个桥梁和系统的搭建者,不再妄图成为整个系统的主导者。
这个感悟同样也适用于社会工作者。
成为协作者
在黄大哥的社区里,他和我分享了很多社区营造的经验,也带我认识了接班的社区服务者。他反复强调的不是自己的重要性,而是如何能够培养出社区里的更多中青年力量,继续为社区公共事务效力,如何培养出接班人后,自己就尽快退后。
他带我认识的这些中青年人,有些是社区发展协会的负责人,有些是不同社区的社会组织带头人。虽然我之前学过社区营造的基础知识,但这次我发现,台湾不同的实践者对社区营造的理解并不尽相同。
虽然社区营造的工具箱是同一套,“造人”、“人文地产景”等,但造出“人和人的关系”之后该做什么,社区社会组织造出来后又如何运作?两个社区的短短参访让我体会到,社区营造有一个重要价值是:搭建平台。
在社区发展协会这个平台上,不同社会组织因应社区具体需求而建立,然后社区发展协会需要找到不同的资源,协助村民完成不同的企划申请,之后就让不同的社会组织在一个社区中“互相效力”。
而社区发展协会的负责人需要掌握一套能力,协助组织带头人们设计和撰写企划书,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培养人,在适时的时候往后退。
沿着这样的思路,我想到自己面对的云南乡村社会工作困境,我们可能需要更具“智慧”和想象力。除了 “半农半X”这个可能性外,我们对乡村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也可以更加整全化,而不仅局限在社会工作。
通过这次学习,我再次确信了,回归农业生产对于乡村社会工作者的重要性,它不仅是一种生计补充,也可以是一种力量的重建。因为社工每天要面对太多的人际互动,能量总是处于消耗状态,与土地的重新连接,也许可以为社工提供一些空间,重新获得能量并真正“回到”乡村。
与土地的连结,可以长出力量,不仅是自下而上、生长的力量,也是自上而下的、扎根的力量
另外,我也看到,如果要重建一个“万物互相效力”的乡村公共服务系统,社工势必需要看到自己的局限,学习“协作者”(Facilitator)的智慧与方法。
从长期目标来看,社工站不能成为公共服务的终极提供者,而需要更有意识地成为服务的资助者、组织者和协调者。当然,这对年轻同事的要求非常高,也势必需要作为支持者的我们,更有意识地思考和设计。
抽象地看,我觉得我们需要一种想象力和视框,“整全”地看待乡村社会工作和乡村工作者。“全人”的视角,决定了我们非常需要学习“系统中的力量与互相平衡”,以及“协作者的自我觉察和合适位置”。
我相信,只有这样的视角和智慧,才足以支持我们,在耗尽青春与情怀之后,仍然能看到自己工作的动力和价值。
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回乡村
因为关注年轻人的支持与返乡,这次我也刻意与更多年轻“农二代”和青年们交流。
如果说,年轻人之前是因为乡村资源和发展机会有限而被“排挤”出了乡村,那近五年来,台湾花莲迎来了更多移民或回归的年轻人。我的接待方蔡建福老师和学生一直在观察这个趋势,并使用了“生活主权”、“风格移民”等概念去解释类似“逆都市化”的现象。
台湾青年人回流乡村,消极方面看,是都市的发展和资源日渐有限,且人的破碎化让年轻人对自身的生活主权更加渴望;积极方面看,则是台湾通过一系列惠农政策(虽然台湾朋友都认为不够)和民间在地化社会运动,让年轻人看到了做农的价值和空间。
一些政策,如以补贴鼓励资深农人做督导,支持年轻人务农,表彰一些农二代榜样等等,也让“农二代”们看到返乡做农的可能性和自我价值感。
微观地看,更多有机农业技术、市场通路和乡村生活品质的上升,也是年轻人们愿意返乡的重要助力。农友们都说,年轻人的体力不如上一代了,但却需要更高的生活品质、更有趣的生产内容,这些都要求我们让有机农业变得更有意思。
换言之,当乡村的生产和生活变得更加丰富、更加考虑人的“生活品质”时,年轻人才会逐渐真正愿意“回到”乡村来,而不仅是彷徨游走于城乡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从社区营造这个侧面,我也看到乡村发展协会是如何“创造”一些位置和空间,让从都市回乡的中青年人发挥自己的能力和价值。我发现大家都有非常现实的考量,乡村可能未必处处都有7-11等便利生活设施,但乡村的健康环境、家庭的承担、自己的主导权等积极因素,都是返乡群体看重的地方。
这些观察提醒我,我工作中的乡村社会工作站也可以“设计”和“创造”出更多位置,使返乡者发挥作用并体现价值。此外,我们也需要意识到并创造条件,支持我们的返乡青年社工们,作为中国第一批真正返乡的年轻力量,活出自己的品质,让更多同龄人和后辈们看到自己的可能性和希望。
如果一直是“苦”的乡村状态,真的会有人愿意背负着家庭的不理解和同辈的笑话,返乡并坚持下去吗?如此的话,对年轻人来说,也未免太苛求了。
向接待机构汇报实习成果
我个人觉得,大陆“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顺应目前经济形势和年轻人状态的重要政策空间。且不说那些政绩工程,就我自己的观察,如果大陆大多数农村能实现台湾乡村生活条件的哪怕80%,年轻人回到乡村的可能性就会大大提高。
社工也许无法控制道路硬化或人居环境改善,但至少可以为返乡者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或者说,社工本身就是多种可能性的先锋象征。
如果想让更多年轻人愿意扎根乡村,我们就要一起努力,夺回乡村和年轻人的生活主权,让乡村不仅可以是晴天的蓝天白云和浪漫乡愁,更可以是雨天的安全出行、不脏脚不堵车;让乡村工作不仅是下雨天可以放下手头事回家收衣服,也是一种对自我价值感和社会评价的体系重塑。
但是台湾年轻人的言行也让我看到,这样的“野心”不是一股力量可以达到的,除了政策倡导要切实地被拉回到“人的发展”层面来,更需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和坚持。这样的践行和坚持,不是停留在“小确幸”的精致个人主义,而是在改变既定但不完美的结构中,无处不在的共同争取。
并不是乌托邦
实习期间,住在花莲五味屋“丰田的册所”青年旅舍十天,我也努力“钻”进五味屋的日常工作中,从仓库整理、开箱分类、上架下架到儿童陪伴等简单体验。
五味屋
在小小的五味屋中,我看到乡村社区同样存在着人口老化、隔代照顾、单亲家庭、边缘儿童、族群刻板印象等等情况。五味屋并不是偏乡的乌托邦,对这些经历的任何过度美化反而会妄自菲薄。
但也正如一行禅师所说,脚步落地,就“到达了”。走好当下每一步,让每一步都尽量是自己所认同的那一步,都尽量是完整的、踏实的、平衡的、那一步。
免责声明:本站文章图文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处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