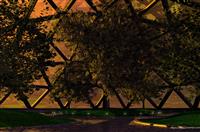在这个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飞速更新的时代,网络和人权的关系更加紧密。网络具有开放性、全球性、交互性、虚拟性,一方面大大拓展了人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权行使的空间,另一方面,其具有的信息海量、把关人缺失、传播迅速的特性又为违法不良信息的传播开启了方便之门,容易给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和个人权利造成威胁。因此,如何保障和依法限制网络人权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热点课题。我国学界对于网络人权的研究较少,而国际社会对于网络人权的理论阐释以及制度建构都已有不少成果。本文从国际视野研究了网络人权的概念、研究现状和性质,网络人权的理论基础,网络人权保护和限制的制度建构实践,并从中总结出我国可以借鉴的经验,以期对提升我国互联网治理水平、增进网络人权的国际对话提供有益参考。
在国际上,网络人权一般被称为Human Rights on Internet,是线下的传统人权在网络空间的衍生。2003年在日内瓦举办的信息社会高峰会议(World Summit o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简称WSIS)报告认为,在充分尊重《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要保障人们在互联网上获得信息的权利。[1] 2011年5月,联合国特别报告员Frank La Rue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作了“表达自由和互联网”的报告。此后,国际人权会议多次从人权角度审视和讨论互联网治理问题,比如2011年内罗毕召开的第六届互联网治理论坛(Internet Governance Forum,简称IGF)强调,接近互联网以及免费使用互联网的机会是一项基本人权。2011年9月,欧洲委员会47个国家发布“网络治理指导原则宣言”(Declaration on Guiding Principle on Internet Governance),认为互联网治理应当依据国际人权法,保障基本人权,确保其普遍性、不可分割、互相依赖、互相联系。[2]2012年6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促进、保护和享有网络人权的决议》(Resolution on the 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申明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人们在互联网下所享有的权利在互联网上同样应该得到保护,尤其是言论自由,这项权利不论国界,可以通过自主选择的任何媒介行使;确认互联网作为加速各种形式的发展进程的驱动力所具有的全球性和开放性;吁请所有国家促进和便利上网,为在所有国家发展媒体及信息和通讯设施开展国际合作;鼓励特别程序适当时在其现有任务内考虑到这些问题;决定根据理事会工作方案,继续审议在互联网上和其他技术领域增进、保护和享有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权的问题,以及如何使互联网成为一项重要发展工具及行使人权的重要工具的问题。[3]2012年联合国在阿塞拜疆举办的互联网治理论坛的报告以及2014年联合国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IGF的会议报告中,都强调“互联网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即通过互联网作为一种手段来更好的保障人权,以及更加充分的保障人们在互联网中所享有的人权。2016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在互联网上促进、保护和享有人权》(Promotion, 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的决议,吁请所有国家根据本国关于保证在网上保护表达自由、结社自由、隐私权和其他人权的国际人权义务,解决对于互联网的安全关切,包括通过国内民主和透明的机构,以法治为基础,采取确保互联网自由和安全的方法,使之能够继续充当带动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4]
从网络人权在国际组织的发展演变来看,网络人权的内涵逐步从笼统到具体,从强调其为一项基本人权到强调政府的保障义务,并且强调互联网上的人权保护与民主和法治的关联。
随着1992年布什政府宣布进行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划,美国的互联网开始快速发展,与此同时,互联网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担忧,探讨网络人权的论著开始相继出版。David R. Johnson 和David G. Post的《法律和边界:互联网空间法律的兴起》中指出信息自由流动是一种受到保护的人权[5]。Thomas Cochrane在《网络空间的国家法律:成为压制互联网人权报告的动因》中探讨了政府压制网络关于酷刑报道对于表达自由和信息自由的侵犯。[6]Lessig Lawrence出版了《网络空间法则》一书,讨论了互联网对于版权、言论自由和隐私权的挑战及规制的问题。[7]S. Hick, E. F. Halpin以及E. Hoskins合作出版了《人权和互联网》一书,收录多篇文章,首次较为全面地对人权与互联网在欧洲、亚洲、南美洲、非洲的发展情况,互联网与儿童权利、受教育权、隐私权、表达自由等关系进行了介绍和探讨。[8]此阶段网络人权研究的特点是:对于网络人权的内涵和外延作了一些初步的描述性界定,也开始研究如何平衡网络上不同权利的关系,但总体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带来的挑战的增多,学界的研究范围逐渐拓展,开始关注对互联网的限制,互联网与民主、治理、外交的关系,如何保护网络人权等问题。研究视角也更加多元,包括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Stuart Biegel在《超越我们的控制:面对网络空间的法律制度的不足》一书中指出了网络空间面临的四大问题:网络恐怖主义、版权、消费者网络欺诈、在线憎恨性言论,并提出规制方案。[9]Selian, A.N.在《信息通信技术在人权、民主和善治中发挥的作用》一文中分析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在人权保护中的作用,强调个人、非政府组织、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应该利用ICT技术发展人权外交,积极互动交流。[10] Balkin J.认为数字时代的言论自由将改变民主文化。[11] Michael L. Best在《互联网能否成为一种人权?》一文中指出,互联网可以成为一种人权,因为其大大拓展了表达自由。[12] Beutz Land在《保护在线权利》中指出,通过灵活协调机制来加强人权与获得知识行动之间的联系。[13]Joanna Kulesza在《全球信息社会中的表达自由:互联网人权宣言的问题》中探讨了IGF的产生和发展,以及ICCAN被美国控制的问题。[14]
随着全球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研究转向为移动互联网的人权、人权与规制的平衡、网络中立等。Aleksey Ponomarev在《平衡互联网规制与人权》论文中探讨了对互联网规制应当采用法律和技术规制手段,考虑有效性、成本、人权因素。[15] Richard Fontaine 和Will Rogers在《互联网自由:虚拟时代的外交政策规则》中指出,网络人权包括隐私权、表达自由、获得信息和知识的权利,但更关注表达自由。互联网治理应通过多方利益主体的参与和对话,包括:公民社会组织、政府、私人企业、国际组织、个人。[16]Luca Belli Matthijs van Bergen讨论了网络中立对于人权的推动作用。[17]Joy Liddicoat和Avri Doria讨论了人权和互联网协议在基本原则上的相似性,如:责任、平等、非歧视、参与、责任、自由等。[18] Belli L探讨了通过网络中立来保护终端用户(end-users) 的人权。[19]Ian Brown和Christopher T. Marsden探讨了互联网治理需要加强公共产品的竞争性供给,包括:创新、公共安全和基本民主权利。[20]Alec Ross回顾了互联网自由的发展历史,并指出其未来发展路向。[21]
第一,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既有学术著作、论文,还有大量的研究报告、会议报告。
第二,视角较为多元。既有从法律角度的研究相关权利如何保障、互联网如何规制的问题,也有从国际政治、外交等层面的研究,研究互联网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影响、民主的促进、互联网政策制定以及反恐、人道主义等问题。
网络人权究竟是一项独立的权利还是一系列权利的集合,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少数学者认为,由于《世界人权宣言》制定的时候互联网并不存在,如今随着互联网对于人权的作用日益明显,从互联网中获得信息的权利能够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权存在并且受到保护,应当独立成为互联网权(Internet Human Rights)。[22]
多数学者认为网络人权并非独立权利,而是是若干传统权利的集合, 但关于究竟包含了哪些权利存在着不同的理解。Aleksey Ponomarev认为网络人权包括表达自由、隐私权、文化多样性、受教育权、获取知识的权利(The Right to Access to Knowledge)等多种传统人权。[23]2007年在意大利召开的“网络权利对话论坛”上首次提出“网络权利”(Internet Rights)这一概念,提出网络权利包括: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协调性(Interoperability)、互联网代码的全球可达性( Global Reachability of all Internet Codes)、使用公开模板和标准( the Use of Open Formats and Standards)、公众获取知识(Public Access to Knowledge)、信息的自由流动(Freedom of Flow of Information)、创新和遵循面向市场的原则的权利( the Right to Innovation and Compliance with the Market-orientated Principles),比如公平和竞争性在线市场(Right to Fair and Competitive Online Market )以及消费者权利(Consumer Rights)。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提出了“网络自由”(Internet Freedom)这一概念,强调网络自由包括: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24]
笔者赞成第二种观点,因为网络本质上是一种媒介,不同的人权在互联网上和实际生活中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都是一样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网络和现实的融合日益密切,很难将线上和线下的人权绝对区隔开来,因此没有必要把网络人权作为一种独立的权利加以单独强调。但是由于网络人权和传统人权毕竟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因此研究其特点和保护对策仍十分必要。
按照联合国《国际人权宪章》的标准,网络人权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网络表达权、网络结社自由、网络集会自由、网络宗教信仰自由、网络监督权、网络知情权、网络参与公共事务权、网络隐私权、网络名誉权等,主要是消极权利,即不受政府任意干涉的权利;第二类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通过网络保障受教育权、文化多样性、获取知识的权利,等,这些权利属于积极权利,即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加以保障的权利。
网络人权作为一种权利,政府有义务进行保护。然而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的,都有一定的边界,因此对其进行限制也是国际通例。目前国际社会争议较大的问题是,对于网络人权是应该更多地强调自由和人权保护,还是更多地强调责任和限制。主要的代表理论有三种:
1.网络自由论
1996年,John Peny Barlow在线上讨论社区发表了“致各国政府的一封信”(也称“虚拟空间独立宣言”),宣称“你们在这里不受欢迎,在这里你们并不拥有主权,你们也没有伦理意义上的统治权,而且,你们也没有任何手段使我们感到必须受制于你们。这个网上世界并不在你们的边界以内。”他把互联网当成是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无组织、无政府、无国界的数字空间,永远不受政府管辖。其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明确提出了网络自由理论(Internet Freedom),并将其作为主要外交政策之一。2010年,Ross Alec系统论证了网络自由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路径;[25]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演讲中正式提出了“网络自由”这一概念。[26]网络自由论者主张,网络自由分为两种:一种是网络上的自由(Freedom of the Internet),包括网络表达自由、网络集会自由和网络结社自由,是表达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基本人权在互联网上的延伸。另一种是通过网络实现自由(Freedom via the Internet)即通过互联网帮助一些个人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27]但这一理论也受到批评,认为该理论缺乏明确的定义[28]和确定的路径。[29]该政策实际上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认为表达自由能够引发“亲美革命”,[30]二是公司企业在保障表达自由方面的地位高度模糊。[31]
2.网络规制论
国际的主流观点是主张网络人权要受到一定限制,但论证的理由各有不同,主要有三个:
(1)网络主权说。200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WSIS上发布了《日内瓦原则宣言》,提出:与互联网有关的公共政策问题的决策权是各国的主权。对于与互联网有关的国际公共政策问题,各国拥有权利并负有责任。[32]
(2)共同责任说。2005 年,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工作组(Working Group on Internet Governance,简称WGIG)提出,网络治理是指国家、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在他们各自角色范围内制定和执行的原则、标准、规定、决策程序以及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计划。强调了不同主体在互联网治理中的共同责任,为网络限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3)影响巨大说。比如:欧洲人权法院早在2011年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判决中指出,互联网在存储和传递信息方面与传统的纸媒不同,互联网在全世界拥有数十亿用户,互联网上的内容对于人权的影响要更为巨大,因此对其规制应有别于传统纸媒,受到更多的限制。[33]
3. 网络中立说
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按自己的选择访问网络内容、运行应用程序、接入设备、选择服务提供商。这一原则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内容和访问,防止运营商从商业利益出发控制传输数据的优先级,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自1996年起,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万维网发明者Tim Berners Lee、互联网协议的共同发明者Vinton G. Cerf为代表,认为互联网中为社区免费提供服务的宽带网络,应当对多数人配置的设备和使用的通信模式保持中立,且不因一种通信而降低另一种通信的服务等级,以确保互联网“非歧视性的互联互通”。[34]该学说主要是防止通信运营商从技术层面阻止互联网的信息流动,确保平等使用互联网。
比较以上三种理论,笔者认为,第二种理论即网络限制说更为合理。因为无论是从国家主权理论、还是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来看,网络都应该受到一定的规制,网络人权不是绝对权利。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多国家也采取各种机制对网络进行规制,比如澳大利亚采取黑名单制度,越南、白俄罗斯以及我国采取了网络实名制,40个多国家对互联网内容进行过滤。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把握限制的度,这是各国都面临的难题。
由于网络人权的重要性,各国都强调了对网络人权的保护,同时也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对其加以限制,对于网络人权的保护和限制的国际经验,有如下三方面值得重视:
法治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普遍注重对网络人权的保护,一方面需要政府采取措施积极保护,比如修建和改善网络基础设施,提高网络普及率,从而确保人们通过网络受教育权、获得知识的权利;另一方面,政府在对网络人权进行限制的时候,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律边界,不能任性而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欧洲人权公约》等国际公约都规定了对表达权、人格权、结社自由等权利进行限制的限制,即限制应该符合“三段论”原则。三段论的三个要求缺一不可,具体内容如下:
1. 为法律所规定(Prescribed by Law)
首先,限制应当有国内法的根据。这里的法包括制定法,也包括判例法。法无明文规定不得限制,这体现了法治原则。
其次,欧洲人权法院在The Sunday Times vs. UK 案中,明确了“为法律所规定”这一标准的两个基本要求是:第一,法律必须可充分获知(Accessible):公民必须能够在法律规则所适用的一定案件的情况中获得充分指引,最基本的要求是法律要公布。[35]在Silver案的判决中,欧洲人权法院认为,英国内务部发给各监狱长的有关法令和指示因为没有公布,不能为囚犯所用,其内容在监狱须知的材料上也没有说明,因而不具有可获知性,不具备“为法律所规定”这一要件中“法律”一词的要求。[36]第二,可预见性(foreseeable)。一项规范除非制定得足够准确从而使公民能够用于调整自己的行为,否则就不能被视为“法律”。法律要想使人们“可以预见”自己行为的后果,就必须在表达上具备准确性。
2.有正当的目的(Legitimate Aims)
对人权的限制还应当具有正当的目的,即符合公约规定的一个或多个合法目的。比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中规定的合法目的包括:(1)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2)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二款所提及的目的更加广泛,大致可以区分为三类:一类属于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安定、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防止秩序混乱或犯罪,维护公众健康或公共道德等;另一类属于私人利益,包括保障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披露保密获得的消息等;第三类是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无偏。这类目的兼顾公私利益:一方面,维护司法权威和公正无疑是公共利益之所在;另一方面,维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又常常关涉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以及要求不损毁法官个人的名誉。关于人格权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也规定了合法目的包括: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或保护他人的权利与自由。
3.为民主社会所必需(Necessary in a Democratic Society)
较之于前两个要件,证明限制是“为民主社会所必需”更为关键。这又保护了两个层次的含义:其一,应当有“紧迫的社会需要”(Pressing Social Need)。其二,手段和目的之间充分且相关(Relevant and Sufficient),合乎比例。当涉及到国家安全、道德等问题时,成员国有较为宽泛的裁量权(Margin of Appreciation)。就表达权的限制而言,不同类型的表达也会影响到成员国裁量权的大小。从政治表达到艺术表达再到商业表达,呈现为国内裁量范围的递增和欧洲监督力度的递减。因为政治表达具有特殊重要性,构成了民主社会的一个核心特征。就人格权而言,公众人物(Public Figure)及政治家(Politician)由于自愿将其置身于公众监督之下,其名誉权、隐私权要受到更大的限制。[37]三段论的限制原则强调合法性、合目的性以及合比例性,和我国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有类似之处。
(二)有效运用合作规制
国际上对于网络领域的规制,主要有三种模式,分别是政府规制(Statutory Regulation)、自我规制(Self-regulation)和合作规制(Co-regulation)。政府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体现了政府的干预。[38]自我规制则是一种自律,包括企业自我规制[39]和行业协会的自我规制。[40]政府规制和自我规制代表着规制的两个极端,而合作规制则介于二者之间,是政府与企业、行业协会等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共同制定标准,共同寻找对策的过程。[41]合作规制是对传统政府规制的有益补充,能够提高政府规制的能力。[42]
合作规制目前得到越多越多发达国家的提倡。从具体运作上来说,合作规制需要政府、国际组织等规制主体拟定行为规范、原则与政策,最终有赖于企业组织等自律的实施。[43]实际上,合作规制的重心和落脚点是自律,它的最终目标是促使企业等被规制对象高度自治,自觉维护公共利益。
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政府垂直监管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开始寻找替代性的规制方式,并且在理念上也出现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from Government to Governance)。[44]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合作规制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合作规制一开始主要应用于与经济民生相关的领域,比如食品安全、医疗、烟酒及保险等等。例如,澳大利亚消费者协会(Australian Consumers Association)和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ACCC)以合作监管的方式来制定了酒类广告守则。酒精生产商可以开展积极的自律,但其行为同时也要符合一些政府或其他行业外部制定的行为准则,澳大利亚政府和规范竞争的监管机构要参与制定行为准则,要与之协商,并且要和消费者代表组织协商。[45]而在互联网领域,由于网络所涉及范围的广泛性、内容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单纯由政府来进行规制是不符合实际的,而纯粹的自我规制又存在缺陷,因此合作规制就逐渐成为了许多国家的选择。
欧盟委员会是合作规制的主要倡导者。2000年,里斯本欧盟理事会峰会提出了改进规制的议题,峰会号召欧盟各机构和成员国采取简化与改进规制的措施。承接此提议,在2001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治理白皮书》。在这份白皮书中,欧盟提出必须革新其共同体的治理方法,应减少使用从上至下的(Top-down)管理方式,而采用非法律的手段以更有效地执行各项政策,也可以把法定规制与其他非强制性(Non-binding)手段结合起来。并且,白皮书也指出,由于规则的制定要考虑技术与市场变化,从而导致政策与立法也变得复杂、费时,成为一个缺乏灵活性与有效性的行为。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市场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难以预测的问题,需要各领域的专家一同参与到政策制定的过程中。所以,为了提高立法的质量、有效性和简化规制活动,可以将规制的实施引入合作规制的框架之中。[46]此白皮书成为了关于欧盟治理的重要文件。
1998年欧盟理事会发出了一份建议文件,对国家层面的传媒领域保护未成年人的自我规制提出了指导意见,此文件是欧盟第一份涵盖所有电子媒体(包括网络视听内容与信息服务)的法规。而对此建议的评估报告中,欧盟委员会称,合作规制意味着公共规制机构的适度介入,是公共规制机构与产业部门、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合作的规制形式,具有灵活性、适应性和效率高的特点,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合作规制常常是达成目标较好的约束机制。[47]
此外,在欧盟2007年颁布的《视听媒体服务指令》(Audiovisual Media Services Directive)中也特别规定,“成员国应该在各自法律所允许的前提下,鼓励在国家层级上使用行业自律与合作规制的方式贯彻本指令的要求。”此指令也是对媒介融合背景下欧盟视听内容传播的最全面的立法。[48]
在美国,虽然传统上对于互联网的规制以自我规制为主,但在涉及未成年人保护的一些高度敏感的问题上,也开始采用合作规制。首先,在刑事层面,1998年《保护儿童不受性侵犯法令》强制要求私营部门揭发违法行为。如果网络服务供应商发现了与儿童色情有关的内容,必须主动向执法机构报告。如果没有报告而被执法部门发现的话,可能会为网络服务提供商带来一笔高额的罚款,第一次是处以5万美元,之后为10万美元。[49]同样,2000年的《儿童互联网保护法》也有类似的要求。这部法案要求公共图书馆如果不能有效地限制人们在图书馆的电脑上浏览色情内容,他们的联邦基金有可能会被撤销。[50]
在人权保障方面,英国、爱尔兰、新西兰、欧盟委员会都在立法之前把该法案对于人权或公民权利的影响作为评估标准之一。爱尔兰要求评估实施主体应当考虑规制对于宪法和爱尔兰所加入的国际公约(如《世界人权宣言》及《欧洲人权公约》)所规定权利的影响,在保护个人自由和增加社会福利之间保持平衡。[51]欧盟委员会也列举了许多规制需要考虑的公民权利,具体包括:(1)平等权;(2)财产权;(3)获得正义的权利;(4)获得社会保障、健康及教育的权利;(5)隐私权;(6)知情权;(7)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受害人和目击证人的权利。[52]而英国对于人权的审查规定最为详细,要求评估实施主体根据1998年制定,2000年生效的《人权法》(Human Rights Act of 1998)的规定,对规制是否侵犯人权进行评价。这些权利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绝对权利(Absolute Right),即任何时候都绝对不能被国家限制或剥夺的,如免于酷刑或受到非人道或侮辱性对待及惩罚;二是受限制的权利(Limited Right),即在明确且限定的情形下可以被限制,如自由权;三是有限权利(Qualified Right),即需要在个人权利和广泛的国家或社会利益之间求得平衡,如个人隐私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宗教和信仰自由、表达权,结社与集会的自由,财产权和教育权等。[53]而评估时,应当遵循以下步骤:(1)判断该规制是否涉及公约权利;(2)判断该规制是否限制了这些权利;(3)判断被限制的权利的属性是否属于绝对权利、受限制的权利还是有限权利;(4)如果属于受限制或有限权利,需要判断这种限制是否在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内。最后,决定该规制合法还是违法。
四、国际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的网络人权保障体系不断完善。根据2016年我国发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实施评估报告》,截至2015年年底,互联网网民达到6.88亿,互联网人口普及率达到50.3%。网民通过各种互联网平台发表言论,对各级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对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对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保障也不断加强。互联网建设也为公民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2016年《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也强调要依法保障公民的互联网言论自由,继续完善为网民发表言论的服务,重视互联网反映的社情民意。
第一,网络立法层出不穷,但层级不高,且与上位法之间存在一定冲突。例如:自2014年,国务院授权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负责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以来,国家网信办发布了一系列互联网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互联网信息搜索服务管理规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对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义务作了细化和严格的规定.然而,这些规范性文件中的一些要求与上位法相违背:如《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第七条第三款中“视情采取警示、限制功能、暂停更新、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属于行政处罚,却缺乏明确的上位法依据,与《行政处罚法》第十四条中“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不得设定行政处罚”的要求相违背。而且,由于规范性文件位阶低,难以设定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导致其规制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网络监管力度的加强容易对网络表达权、监督权、知情权、隐私权等权利造成过度限制。随着网络违法的不断增加,我国网络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大,网络实名制的推进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于个人信息以及表达权保护的担忧。而对网络违法不良信息(淫秽色情、谣言等)的严厉打击,由于执法标准的不统一,也容易对公民正常的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等权利造成过度干涉。比如:2012年,重庆职工方洪因在微博上发表上批评性言论被劳动教养,法院认为,方洪在腾讯微博上发表的评论,虽然言辞不雅,但不属于散布谣言,也未造成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严重后果,更不具备“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这一基本要件;国家公务人员对公民基于其职务行为的批评,应当保持克制、包容、谦恭的态度。被告以原告方洪虚构事实扰乱社会治安秩序作出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判决此决定违法。在2013年最高法和最高检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司法解释出台后不久,甘肃省张家川县初三学生杨辉因发帖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当地警方援引该司法解释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引发社会各界对于该司法解释会导致警察滥用公权力的担忧。后杨被予以行政拘留后获释。
第三,网络监管以集中整治模式为主,常态化、日常化监管机制尚不健全。从国家网信办的监管实践来看,集中整治模式占了主导地位。从14年9月开始,国家网信办陆续开展了“整治网络弹窗”专项行动、扫黄打非净网行动、清理整治网络视频有害信息的专项行动、网络弹窗专项整治行动、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跟帖评论专项整治等专项行动,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处罚了一批企业,在短期内抑制了违法的势头。这种集中整治往往是集中执法力量在一段时间内从重从快打击违法行为,体现政府对某类违法行为严惩的决心,比较容易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也容易出现选择性执法、滥用裁量权、执法成本太高等问题,弱化了法律权威,有损政府的信用,治标不治本。[54]
笔者认为,国际对于网络人权的保障和限制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改进网络人权保障提供了有益参考,我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方面来改进网络人权保障:
网络人权是全球各国都重视和保护的基本人权,虽然国际公认的标准是,基于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他人合法权益的理由,可以对网络人权进行一定的限制,但是也要给限制设定边界。笔者认为,在我国对于网络人权的限制应当遵循以下两个基本原则:
1.依法行政原则
这一原则包括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两部分内容。所谓法律优先是指一切行政活动的法律依据,均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如:行政法规不能违反宪法和法律,部门规章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例如:上位法已经规定了对某一侵犯隐私权行为的处罚幅度,则下位法只能在此幅度范围内进行处罚,而不能超过该幅度进行,否则就构成违法。而法律保留是指特定的行政行为,必须有法律授权的依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的十类事项,但第9条又规定了,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换言之,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属于绝对法律保留的范畴,只能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如果某一行政法规规定了对侵犯网络人权的行为可以判处刑罚,则违背了这一原则。
因此,在保障网络人权时,需要考虑行政行为的依据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是否存在职权违法、程序违法等情形,该行为是否需要法律保留。
2.比例原则
产生于19世纪德国警察法上的比例原则被尊奉为行政法上的帝王条款。比例原涵盖了适当性、必要性及均衡性三个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的步骤,成为判断行政行为适法性的有效工具。这一原则要求行政权应当考虑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确保手段能够达到目的,且对相对人造成的侵害最小,成本与收益之间成比例。因此,在保护网络人权时,应当考虑是否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如果对某一侵犯网络隐私权的行为,只需通过罚款即可解决,而行政机关采取了行政拘留的手段,则属于不合比例的行为。
在我国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并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的背景下,我国互联网监管应当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1.从单中心监管到多主体治理的转变
监管(Regulation)和治理(Governance)具有不同的内涵。传统的互联网监管强调政府的控制和主导地位,监管工具主要是设定许可、限定禁止内容、设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各种义务等,以干预行政为主。而互联网治理内涵更丰富。根据2005年联合国互联网工作小组(WGIG)的定义,是指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55]因此治理强调多主体的协调、合作、互动,综合运用政府监管、合作监管、自我监管等多种机制。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创新性,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在互联网监管机关人力和技术水平都有限的情况下,仅靠行政机关的刚性监管,往往成本很高,而且效果不佳。在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简政放权的背景下,积极发挥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共同作用,通过合作监管、自我监管等方式能够降低监管成本,提升监管效果。其中政府应当扮演的角色包括:设定最低标准,召集多方协商机制,支持和鼓励各方主体参与协商,提升其参与协商的能力,以及进行最终的监督。政府和企业应该共同制定标准,共同执行,同时发挥行业协会自律、公民投诉举报等机制作用,才符合多主体治理的要求。
2.从刚性监管到刚柔并济的转变
互联网治理强调治理手段的刚柔相济,不仅包括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硬法机制,也包括行政指导、行政资助、行政奖励、行政调解等软法和非强制性监管手段,通过利益诱导机制引导行政相对人纠正违法行为,鼓励他们积极创新和提升守法意识。这些柔性监管手段具有平等协商性和自由选择性,从挖掘和满足行政相对人的需求入手,符合民主行政、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趋势,容易取得行政相对人的认同和配合。行政指导手段更加灵活,运用领域更加广泛,不仅是在行政相对人存在严重违法违规之前可以运用,在其存在轻微违法苗头时,或者为了促成行政相对人事业的发展壮大均可采用。当然,需要处理好刚性和柔性手段之间的关系,既不能以指导、奖励等柔性手段取代处罚等刚性手段,也不能单纯地一罚了之、以罚代管,而是刚柔相济,采用能够达到行政目标的最佳方式。
3.从集中整治到常态化监管的转变
实践证明,集中整治模式具有较多弊端,容易导致选择性执法,执法裁量权滥用等情形,因此监管机关应当转变观念,以常态化监管为主,从依赖突击和集中整治的粗放型监管模式向依靠多方参与、建立长效机制和加强技术手段的监管模式转变。同时,科学划分监管机关的权限,合理配置执法力量,推进综合执法;严格遵守执法程序,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对监管机关为追求政绩搞集中整治执法而忽略日常执法的行为的渎职和行政不作为加大问责力度;建立健全科学的公务员考评机制,将公务员的提升和奖惩与其日常执法绩效相结合。
4.从重实体、轻程序到树立程序正当理念的转变
程序正义是实现实体正义的前提和保障。互联网监管领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立法决策不够公开透明,监管程序不周全,与现代法治强调程序正当的理念不相契合。笔者认为,互联网监管的立法、决策、执法全过程都应当贯彻程序正当理念。互联网监管机关不仅应当在规范性文件中设计出能够有效保障行政相对人民主权、参与权、知情权、获得救济权的程序,更应当在出台法律法规和重大行政决策作出之前,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要求,公开征求意见,鼓励社会公众、利害关系人、专家、行业协会的广泛参与。同时,应当建立行政立法评估制度,对立法和决策的合法性、有效性等问题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引起人权影响评估,及时修改或者废止那些不合时宜的条款。同时,在行政执法中完善执法程序,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建立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完善行政执法公示和结果公开制度。
1. 完善相关立法
首先,我国还应该尽快出台互联网领域的基本法,或者修改《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互联网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义务、责任加以明确,细化网络信息的传播规范,网络监管的标准、程序、救济途径,避免出现上位法缺失,下位法任意扩权的问题。
其次,在全面推进网络实名制的同时,应当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我国已经在《网络安全法》中加入个人信息保护专章,明确界定了个人信息的范围,个人信息保护的基本原则,网络运营者的个人信息保护的义务,信息主体的删除权、更正权等。但这些规定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落实。
再次,在出台相关立法时以及立法实施后,我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对该立法对人权的影响进行评估,使得立法在人权保障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针对我国网络监管中重政府监管,轻合作监管和自我监管的情形,笔者认为,
首先,政府监管部门应当从行业资质、隐私保护、实名注册、备案审核、内容限制等方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指导和合作,合理界定平台责任,实现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并行。
其次,加强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网络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分工,推进综合执法,避免政出多门。
第三,在网络知情权,公共事务参与权方面,依据“互联网+政务”的精神,发挥微博、微信作为政务公开和舆论监督的平台作用,进一步推动“微博、微信问政”,通过平台发布政府信息,接收违规违纪、政府效能等方面的举报。完善从平台建设、信息推广、公众参与到对于举报的反馈、处理再到处理结果的公开等完整的制度链条,最大程度地便利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和舆论监督。
最后,监管部门应当大量采取行政指导、行政奖励、行政资助等柔性手段进行监管,例如对公民和企业发提示信息,指导其提高防范意识;对违法的个人或企业给予警告;对有功的企业和个人给予奖励等。
注释:
[1] 《信息社会高峰会议原则宣言》,http://www.itu.int/dms_pub/itu-s/md/03/wsis/doc/S03-WSIS-DOC-0004!!PDF-C.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2] Wolfgang Kleinw?chter,Human Rights and Internet Governance,http://dl.collaboratory.de/mind/mind_04berlin.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3] Resolution on the Promotion,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 http://ap.ohchr.org/documents/dpage_e.aspx?si=A/HRC/RES/20/8,2016年10月27日访问。
[4] Promotion,Protection and Enjoyment of Human Rights on the Internet,http://www.un.org/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A/HRC/32/L.20,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 David R. Johnson and David G. Post,“Law and Borders – The Rise of Law in Cyberspace”,Stanford Law Review(1996),vol. 48.
[6] T. Cochrane,“The Law of Nations in Cyberspace Fashioning a Cause of Ac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Human Rights Reports of the Internet.”,Michigan Telecommunications & Technology Law Review(1998),Vol. 4:157.
[7] Lawrence Lessig, 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New York: Basic Books,2000.
[8] S. Hick, E. F. Halpin, E. Hoskins,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et,New York:St. Martin"s Press,2000.
[9] Stuart Biegel, Beyond Our Control? Confronting the Limits of Our Legal Systems in the Age of Cyberspace, 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1.
[10] A.N Selian,ICT in Support of Human Rights,Democracy and Good Governa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2002.
[11] Balkin J.,Digital Speech and Democratic culture: a Theory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 79:1,available at http://www.yale.edu/lawweb/jbalkin/telecom/digitalspeechanddemocraticculture.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12] Michael L. Best,Can the Internet be a Human Right? 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2004,Vol.4.
[13] Molly Beutz Land,Protecting Rights Online (November 4,2008),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Forthcoming,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295448.,2016年10月27日访问。
[14] Joanna Kulesza,Freedom of Information in the Global Information Society: The Question of the Internet Bill of Rights,University of Warmia and Mazury in Olsztyn Law Review,2008,Vol. 1,pp. 81-95,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1446771.,2016年10月27日访问。
[15] Aleksey Ponomarev,Balancing Internet Regulation and Human Rights,Master Thesis,Stockholm University,2010.
[16] Richard Fontaine and Will Rogers,Internet Freedom:A Foreign Policy Imperative in the Digital Age,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ociety,June 2011.
[17] Luca Belli Matthijs van Bergen,Protecting Human Rights through Network Neutrality: Furthering Internet Users’ Interest,Modernising Human Rights and Safeguarding the Open Internet,Steering Committee on Media and Information Society(CDMSI)4th meeting Strasbourg 3-6,December 2013,CDMSI(2013)misc 19E.
[18] Human Rights and Internet Protocols: Comparing Processes and Principles,Council of Europe,Internet Governance,Council of Europe Strategy 2012-2015,CM(2011)175 final,March15,2012,paragraph I.8.e, available at https://wcd.coe.int/ViewDoc.jsp?id=1919461.,2016年10月27日访问。
[19] Belli L.,Council of Europe Multi-Stakeholder Dialogue on Network Neutrality and Human Rights,Outcome Paper,June 2013.
[20] Ian Brown and Christopher T. Marsden,Regulating Code: Good Governance and Better Regul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Cambridge:MIT Press,2013.
[21] Alec Ross,“Internet Freedom: Historic Roots and the Road Forward”,SAIS Review,2010,30(2): pp.3–15.
[22] 同注13
[23] Aleksey Ponomarev,Balancing Internet Regulation and Human Rights,Stockholm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Law Master Program in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9-2010Course B Thesis,available at:http://ssrn.com/abstract=1990182.,2016年10月27日访问。
[24]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 (February15,2011),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2016年10月27日访问。
[25] Alec Ross,Internet Freedom: Historic Roots and the Road Forward,SAIS Review,Volume 30,Number 2,Summer-Fall,2010,pp. 3-15 (Article).
[26] Hillary Rodham Clinton,“Internet Rights and Wrongs: Choices &Challenges in a Networked World”,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Washington (February15,2011),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2/156619.htm.,2016年10月27日访问。
[27] 同注17
[28] McCarthy D.R.,“Open Networks and the Open Doo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Narration of the Internet.” Foreign Policy Anal(2011),Foreign Policy Analysis 7(1): pp.89–111.
[29] 同注21
[30] Joseph S. Nye,“Get Smart: Combining Hard and Soft Power”,Foreign Affairs,2009,88(4): 160–63.
[31] Rebecca MacKinnon,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2012.
[32] Declaration of Principles,2003.
[33] Editorial Board of Pravoye Delo and Shtekel v. Ukraine (Application no. 33014/05).
[34] Network neutrality: Insights gained by juxtaposing the US and Korea,20th ITS Biennial Conference,Rio de Janeiro,Brazil,30 Nov. - 03 Dec. 2014: The Net and the Internet - Emerging Markets and Policies.
[35] Sunday Times v. The United Kingdom,App.no.6538/74( ECtHR,April 26,1979).
[36] Council of Europe(ed.),The exceptions to article 8 to11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1997,p.10.
[37] Jacobs,White & Ovey,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325-328.
[38] Bettina Lange,“Understanding Regulatory Law: Empirical versus Systems-Theoretical Approaches?”,Oxford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1998),pp. 449-450
[39] John T. Scholz,“Managing Regulatory Enforcement in the Unites States”,in Handbook of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Law (edited by David Rosenbloom & Richard D. Schwartz), 1994,p.431.
[40] Cary Coglianese and Evan Mendelson, Meta-Regulation and Self-Regulation, in Robert Baldwin,Martin Cave and Martin Lodge (eds.), Oxford Handbook on Regulation,2010,pp.146-153.
[41] [美]朱迪. 弗里曼:《合作监管与新行政法》,毕洪海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34-35页。
[42] Jacob Torfing,”Governance Networks”,in David Levi-Faur (Editor), Oxford Handbook of Governanc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103.
[43] 李继东:《复合规制:媒介融合时代的规制模式探微》,载《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7期。
[44] 张文峰:《西方国家传媒治理中的替代性规制》,载《新闻界》2015年第5期。
[45] Christopher T. Marsden, Internet co-regulation: European Law,Regulation Governance and Legitimacy in Cyberspace,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p.54.
[46] European Commission:“European Governance: A White Paper”,Brussels,COM(2001)428 final,July 25,2001.
[47] Second Evaluation Report from the Committee to the Council and the European Paliament on the Application of Council Recommendation of 24 September 1998 concerning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and human dignity,COM(2002)776 final.
[48] http://www.wipo.int/wipolex/en/text.jsp?file_id=199673.,2016年10月27日访问。
[49] Protection of Children From Sexual Predators Act of 1998, https://www.congress.gov/105/plaws/publ314/PLAW-105publ314.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0] Children"s Internet Protection Act of 2000,http://ifea.net/cipa.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1] RIA Guideline,How to conduct a Regulatory Impact Analysis,Published by Department of the Taoiseach,Publications_Archive/Publications_2011/Revised_RIA_Guidelines_June_2009.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2] Impact Assessment Guideline,http://ec.europa.eu/governance/impact/commission_guidelines/docs/iag_2009_en.pdf,,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3] 该法律将《欧洲人权公约》及议定书中的十六项权利规定为“公约权利”(Conventional right),包括:(1)生存权;(2)免于酷刑或受到非人道或侮辱性对待及惩罚;(3)免于奴役或强制性劳动;(4)自由和人身安全的权利;(5)公正审判的权利;(6)法无规定不受惩罚;(7)个人隐私和家庭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8)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9)表达自由;(10)结社与集会的自由;(11)结婚和组成家庭的权利;(12)不受歧视的权利,除非基于正当理由,不得因种族、宗教、性别、政治见解或其他个人地位而受到歧视;(13)财产权;受教育的权利;以及自由选举的权利;(14)教育权;(15)选举权;(16)废除死刑。Making sense of human rights: a short introduction, http://www.justice.gov.uk/docs/hr-handbook-introduction.pdf,P3.,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4] 严春银:《运动式行政执法现象评析》,http://fzb.nc.gov.cn/InfoDetails.aspx?InfoID=89,2016年10月27日访问。
[55]《信息社会突尼斯议程》,http://www.un.org/chinese/events/wsis/agenda.htm,2016年10月27日访问。
作者简介:郑宁,中国传媒大学文法学部法律系副教授,法学博士。
文章来源:《人权》2016年第5期